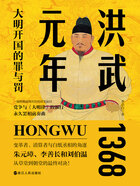
01 大案!姚广孝和盘托出明初最大案
碧蓝如洗的天空低垂下来,仿佛快要压到应天府大街那些行人们的头顶上。红彤彤的太阳就像一团巨大的火球,天上的云彩全都被它烤化,消失得无影无踪。
园子里的树荫下,一位身着青袍的清瘦老者和一位文官打扮的中年人,正默默坐在棋盘前对弈。灼热的阳光从他们头上密密层层的枝叶间透射下来,在地上印满了铜钱大小的块块光斑,晃得人有些睁不开眼。正在对弈之中的那位青袍老者也似乎感受到了这刺眼的阳光,不禁伸出衣袖在眼前轻轻隔挡了一下。
“咦?刘先生今天下棋好像有点儿心不在焉呀。”那中年文官微笑着将一枚黑子放上棋盘,顺势提走了青袍老者那边几枚被他阻断了“气”的白子,“杨某实在是有些不好意思,又吃掉了刘先生几个子儿!”
青袍老者深深一叹,忽然推枰而起。他眯着一双老眼仰望着如烈火般炙人的天穹,神情显得十分凝重。只见他缓缓说道:“唉!从二月二十三起到现在,已经干旱了五十多天了——江南十八郡的百姓可遭殃了!这五十多天来,大家一直没盼来雨水,纵是播了种、栽了秧,到地里也是个死,年底的收成自是好不起来了!”
“是啊!”中年文官也放下手中掂着的棋子,站起身来和他并肩而立,失声感慨不已,“李相国对这件事儿也焦虑得很,听说他要请应天府花雨寺的高僧来作法祈雨呢!”
青袍老者听了,眉头微动,然后又伸出手来,缓缓抚了抚胸前的须髯。但他神色则是不置可否。他心底暗想:这李善长也真有些可笑,平日里不知修渠筑库蓄水防旱,到了今年大旱才来“临时抱佛脚”,祈求苍天行云降雨。只是这般做法,却怕老天爷不“买账”啊!
原来,这青袍老者便是大明朝著名的开国功臣、现任御史中丞之职的刘基(刘基,字伯温,民间通称刘伯温)。那中年文官则是他朝中少有的几个挚友之一——中书省参知政事杨宪。今日刘基因身体不适未曾上朝,一直在府中休闲养神。杨宪是在散朝之后顺道过来看望他的。
刘基站了片刻,又在藤椅上坐了下来。他静静地看着杨宪问:“今日李相国和太子殿下在朝中议决了哪些事?拣紧要的给老夫说一说吧。”
“哦……杨某知悉,刘先生又在关心那部《大明律》(1)在全国颁布实施的事了。”杨宪像是早就揣摩到了刘基的心思一般微笑着答道,“李相国和太子殿下对这事儿也很重视,抓得很紧呀!据各大州府报上来的消息来看,大家对《大明律》在民间的宣讲和执行还是做得蛮不错的。荆州那里严格遵照《大明律》,对几个囤积居奇、大发横财的土豪劣绅进行了惩处,百姓对此纷纷拍手叫好呢!”
“嗯……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刘基认真听完杨宪的报告,不禁深深点了点头。他沉吟片刻,忽又问道:“今日李相国可曾谈到陛下北伐胡虏又取得了何等伟绩?”
“徐达大将军的东路大军已经打到通州,伪元帝早就弃了大都逃向漠北,胡元之灭指日可待。现在只有西路大军形势有些可虑……”杨宪蹙着双眉,回忆了好一会儿,才缓缓说道,“陛下六日之前已达开封府亲自指挥西路大军,正与李文忠、冯胜等将军谋划着一举歼灭盘踞在山西境内的贼酋王保保,目前尚无任何战报传来。”
刘基和杨宪口中所称的“陛下”,便是洪武大帝朱元璋。前不久,朱元璋因担忧北伐大业,不顾个人安危,亲率大军御驾征讨元朝第一名将王保保。但王保保这人一向深明韬略,智勇双全,又在山西拥兵近四十万,是元朝将军当中的顶尖人物,极难对付。在刘基看来,朱元璋是否真能如他自己所言将其一举歼之,把握并不太大。因此,在和丞相李善长作为一正一副两位监国大臣的身份留守应天府的这段日子里,他最为忧虑的就是朱元璋此番的御驾亲征顺利与否。
此刻听到杨宪声称前方尚无战报传来,刘基的眉头一下紧锁起来。等杨宪说完,他才轻轻叹了口气,慢慢说道:“其实,老夫倒并不怎么担忧陛下的龙体安危。陛下乃是命世之英、天纵奇才,定会逢凶化吉。老夫所忧之事是,倘若贼酋王保保坚壁清野,固守山西,使我大明雄师求战不得,求退不能——双方相持不下,再这样耗下去,唉,‘兵马交战,粮草为本’,我们就得千方百计为陛下多筹点儿粮草及时运送过去了。”
说到此处,他不禁抬头看了看天空中的炎炎烈日,满脸愁云地长叹一声:“你看这日头如此热辣,哪里有降雨泽民的迹象?唉,真是苦了黎民百姓了!”
杨宪听罢,也皱了皱眉头,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语:“是啊!前方打仗急需粮食,后方却又无雨灌溉农田——我们就是下去催逼百姓也于心不忍哪!”
“但愿苍天有眼,能及时降下甘霖化解这场旱灾吧!”刘基从藤椅上站起身来,在树荫下慢慢踱了几圈,仰面望向那蔚蓝的天空,表情显得十分复杂,“老夫是相信‘天人感应’之理的:陛下驱除胡虏、废除苛政、肃清四海,乃是天意民心所归,自会获得天佑人助。这一场北伐之战,必定是不疲师、不累民便可大功告成!”
杨宪听着,站在一侧默默点了点头。是啊,现在大家也只能作如此之盼了。
“对了,杨大人。”刘基静立片刻,忽又像想起了什么似地转过身来,一脸认真地看着杨宪说道,“从今天起,如果北伐大军那边有什么战况战报和战事图册送到中书省来,还要麻烦请你抄一份给老夫看看。唉,老夫若非如今身染沉疴,耐不得鞍马之劳,也上不得疆场,此番北伐必会追随陛下前赴开封府的。”
“刘中丞,陛下让您在后方好好养病,您就在家好好养病吧。”杨宪甚是关切地说道,“您这段日子里,实在是不宜操劳过度啊。”
“不妨!不妨!”刘基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老夫如今在府里养病闲着也是闲着,倒还不如抽些时间对那些战况战报和战事图册揣摩揣摩。没准儿能给陛下和冯将军、李将军他们想出几个点子送去,也算多少有些助益。料想早一日打下山西,朝野上下也可早一日松一口大气。”
“唉,刘中丞,您真是……好吧!杨某一有前方战况讯报和战事图簿便立刻给您送来就是。”杨宪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您啊!总是这么闲不住……”
正在这时,刘基府中的老仆刘德匆匆走进了园子,向刘基禀道:“老爷,府门外有一青年书生前来求见。”
刘基听了,斜眼向杨宪看了看,笑了一笑。杨宪也会意地一笑。他心想:一定又是哪个想贪图“捷径”一步登天的狂生来找刘先生“探门道”了!当他再转向刘基时,却发现刘基笑容早已收敛。只见他对刘德正色道:“一个青年书生?怕不是来找老夫说说文章、谈谈治学的吧?你回去告诉他:他若是自负才学出众,想来老夫这里毛遂自荐,可以自行前往中书省或者吏部投送名帖,接受他们的考核征召;他若是想来举报有关官吏贪赃枉法之事,可以前往御史台送交状纸,监察御史们自有公断。在这私人府第之中,任何陌生来客,老夫一概不予接见。”
刘德听罢,恭恭敬敬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杨宪却不多言,只是缓步走回树荫下的棋盘旁边。他看着那黑白纵横的棋局,微微笑道:“先生和杨某的棋弈还没结束呢!来,我们继续下。”
刘基头也不回,缓缓说道:“棋局已然如此,你还要下吗?老夫现在确是被你吃了四个子儿,但二十三招之后,你就要以输我十四个子儿而收官。”
杨宪一听,倒也不以为忤,只是笑道:“先生休要拿大言唬我!你且过来与我一战!”二人正说着,却见刘德再次折身回来,手里还拿着一张纸条。他向刘基禀道:“老爷,小的前去劝他不走,他还送了一张纸条给您。他说以中丞大人的谋国之忠、察事之明、执法之公,您一见他写的这张纸条,必然会接见他。”
杨宪一听,不禁“扑哧”一声笑了:“这青年书生也真是有趣,削尖了脑袋偏要找您刘老先生的‘门路’,可笑可笑!”
刘基微一沉吟,接过那张纸条,然后又向杨宪招了招手道:“你且过来,大家一起看一看他到底写的是何内容,为何他就那般肯定老夫一见他写的这纸条必定会接见他?”
杨宪淡淡地笑着,走了过来,和刘基一齐向那纸条上看去,却见那上面写着这样一番话:
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像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只可惜,昔日暴元之秽政,复又见于今日之大明圣朝,岂不令人扼腕痛心也?!
杨宪读罢感到又惊又怒,立时失声叱道:“这书生好大胆!竟敢出言不逊,亵渎我大明圣朝!快快让人把他拿下!”
却见刘基仍是低头静静地看着那纸条上的话,若有所思,半晌也没作声。那书生以刘基所著的文章《卖柑者言》反讽于他,确实令刘基心念一动。他忽然抬起头来,深深地向着府门方向望了片刻,方才摆了摆手,止住了杨宪的怒叱之声。杨宪一副怒气难平的样子,气呼呼地看着他说:“哎呀,刘先生,这书生的话尖刻得很,真亏了您还这么沉得住气。”
“杨大人暂且息怒。你还别说,他不写这段话倒也罢了,今天他写了这段话,老夫倒还真想见他一见了!”刘基静静地看着杨宪,淡淡说道,“古语说得好:‘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这书生敢出此非常之语,必是见了非常之事方才有感而发。刘德,且去请他进府来见,老夫倒要看看他究竟所为何事而来。”
说罢,他语气顿了一顿,又盯着杨宪愤愤不平的表情,慢慢说道:“若是查实了他确为信口雌黄、谤讪朝政,再议他的罪过也不迟。”
见状,杨宪也沉着脸点了个头。刘德见状,急忙应声而去。
隔了片刻,只听得足音笃笃,刘德一溜小跑在前引路,他身后跟着一位身着白衫的高瘦青年。只见此人生得玉面红唇、剑眉星目,举手投足恍若玉树临风,清逸不俗,正缓缓迈步潇洒而来。
这白衫青年走到刘基、杨宪面前,先是落落大方地微微一笑,然后躬身深深施了一礼道:“小生在此谒见刘先生和杨大人。”
刘基伸手轻轻抚着颌下长须,只是含笑不语。杨宪反倒是脸上微露嗔色,上前一步冷冷问道:“大胆狂生,你竟敢以暴元秽政比拟我大明圣朝——你可知罪?”
白衫青年听见他这般声色俱厉,却不慌不忙地微微笑道:“杨大人言重了,小生岂敢妄议朝政?小生今日前来,是想揭发大明圣朝开国以来第一大吏治弊案!此案不破,天下百姓对大明圣朝自有评说,悠悠众口,岂独小生一人?杨大人少安毋躁,且听小生细细道来。”
“吏治弊案?”杨宪一听立刻变了脸色,心头也跟着一阵剧震,“你这书生,今番前来要指证何人?有何证据?”
白衫青年并不立即作答,而是在树荫之下慢慢踱了几步,沉吟片刻,方才缓缓说道:“刚才刘先生对小生说:若是前来毛遂自荐,可到中书省或吏部报名应征;若是举报官吏不法之事,则可去御史台送呈状纸。可是这两个地方,小生都是碰壁而归啊!所以,小生迫不得已,只有来求见素以‘刚正清廉、公忠体国’之名远播天下的刘先生反映案情了!”
“你在中书省和御史台都碰壁而归?”刘基抚着长须,缓缓开口了,“他们为何会拒绝你?你且把事情经过详细讲来。”
“其实原因很简单。”白衫青年面容一肃,沉吟着说道,“首先,小生此番进京,本就是状告中书省和吏部,因怕遭人灭口,故而不敢自投罗网。其次,小生半个时辰前到御史台呈上诉状,不料当值的监察御史吴靖忠吴大人一听小生所告不法官吏之姓名,立刻便吓得面无人色,以‘草民告官,兹事体大’的理由推搪小生,死活也不肯接收小生的诉状。小生沉吟许久,本着‘一不做,二不休’的精神,便干脆来了刘先生府中登门告状。刘先生身为御史中丞,是我大明百姓头顶上的‘朗朗青天’,应该会受理小生举报的这个弊案的吧?”
他这一番话犹如竹筒倒豆子般噼里啪啦说将下来,杨宪已是听得脸色大变、瞠目结舌。他半晌方才反应过来,惊道:“本官也是中书省里的人——中书省岂是你口中所说的‘藏污纳垢’之所?你究竟要状告中书省里何等贪赃枉法之事?”
刘基却是面不改色,平平静静地看着白衫青年。只见他双眸正视,目光澄澈,心中估量他不似信口撒谎之人,便微微向外摆了摆手。刘德见状,立刻会过意来,急忙退下去,走得远远的。
待他走远之后,刘基才缓步走到那白衫青年面前,摆手止住了杨宪的催问。然后,他和颜悦色而又沉缓有力地对白衫青年说道:“公子为国仗义执言,不惧豪强,老夫十分敬佩。现在公子可以放心大胆地说了。老夫向你保证,你今日举报之事若是属实,御史台必定彻查到底,依律办理!无论此案牵涉到哪一级的高官权贵,御史台都绝不会姑息!”
白衫青年见刘基一字一句讲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不禁心念一动,脸色便也严肃凝重起来。只见他深深地点了点头:“宋濂宋老师常常对小生提起刘先生,说先生秉公持正、大公无私、执法如山,小生今日一见先生您的言谈气度,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你认识宋老夫子?”刘基和杨宪听了,表情都是愕然。白衫青年含笑不答,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刘基静思有顷,忽然淡淡笑了:“我知道公子是谁了。”说着,他慢慢抬起头望向万里无云的天空思索着说道:“前段日子宋老夫子曾给老夫说起他的家乡浙东长洲县里有一名青年儒生,学富五车,德才兼备,气宇清奇,胆识过人,实乃‘非常之器’‘超群之材’。他多次将此人举荐于老夫,要求朝廷以国士之礼聘之。然而老夫近来忙于公务,还未来得及推荐给陛下。不想你今日竟自己来了。”
白衫青年哈哈一笑,躬身深施一礼,语气于谦恭之中又带着一丝昂然的自负,说道:“小生今日之来,可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前程,而实为我大明圣朝的长治久安而来。”
刘基微微颔首,不再多言。不过,很快他便突然转身向杨宪双手拱了一揖道:“杨大人,你是中书省内之人,而这位公子又前来我处举报中书省不法之事。恐怕你滞留在此有些不便吧?”
“你……你……”杨宪一听,不禁瞪着刘基,“好你个刘先生,连杨某的为人也不相信吗?”
“老夫当然是素知杨大人的为人,可是《大明律》上也写着‘御史台查案之时,涉案部堂之官吏必须回避’的规定啊!杨大人,老夫询问这位公子之时,你应该回避。”刘基说到此处,又向着杨宪意味深长地一笑,“有些事情,恐怕杨大人还是主动回避、事先不知得好。”
杨宪怔了片刻,忽然明白了过来。他伸手拍了拍脑袋,“嗨”了一声,随即又一点头,立刻作礼告辞而去。
刘基目送他出府之后,方才转身向那白衫青年招呼了一声,请他在树荫下的藤椅上坐了下来,自己也坐在另一张藤椅上。他执壶在手,为白衫青年倒了一杯清茶递来,从容温和地说道:“现在你不会有什么顾忌了——可以说了吧?”
白衫青年见刘基如此礼敬于他,急忙垂手站起,谦恭地说道:“不敢当!不敢当!小生姚广孝(2),在此谢过先生美意了。”
“老夫早就料到是你姚公子了。”刘基淡淡笑道,“宋老夫子曾经送姚公子的一首诗给老夫看过,老夫记得很清楚。
‘独上绝顶俯沧海,万潮争啸云竞飞。昂首但见天压来,双臂高擎扬远威。’
公子的诗写得很好啊!你自喻为撑天柱地的栋梁之材,豪情可嘉啊!”
姚广孝有些腼腆地笑了一笑,急忙摆手道:“书生意气,虚浮之词,何足挂齿?况且我这首诗中的平仄也不那么贴切。先生取笑了!”
“不过,老夫感到奇怪的是:听说你不是已经在苏州府寒山寺出家为僧了吗?据说连法号都有了,叫什么‘道衍’?但看今天你的装束,怎么还是一身儒生打扮?”
“先生说得没有错。小生现在的确是寒山寺寄名的佛门俗家弟子。只因我年幼之时体弱多病,相士席应真前辈便建议我父母将我寄名于佛门之中以免灾咎,所以我从小就是寒山寺名下的带发修行弟子。而小生成年之后服膺儒学,和‘吴中诗杰’高启先生素有交游,也常在清流文苑之中来往。所以,我通常还是以姚广孝之名、姚斯道之字入世接物的。”
“原来如此!”刘基轻轻颔首。一眼就能看出,刘基像一位慈祥的长者微微含笑看着他。那神情、那气度,令人如沐春风。
姚广孝这时却静了下来,正了正脸色,肃然说道:“小生今日来见先生,确是有贪渎大案要举报。您在朝中,应该知道上个月底陛下奔赴开封府平贼之前,曾下了一道‘求贤令’,令上明文规定由中书省承办,面向全国各郡县征召贤能才智之士吧?”
刘基面色肃然,点了点头:“是有这么一件事……”
姚广孝双眼直盯着刘基的眼眸,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您也知道,小生乃是长洲县人氏,对长洲县之事必是关心。却说这道‘求贤令’发到我们长洲县时,县内的富豪韩复礼为了让自己的儿子韩通入仕当官,便拿钱买通了县令吴泽,向中书省送呈了韩通才艺过人、可以入仕的公函荐书。韩复礼竟然还拿着这份公函荐书,专程跑到应天府,走了中书省一个五品都事李彬的‘门路’,送了三千两白银给他。就这样,韩复礼把他那个大字不识一筐的傻儿子安排到了吏部当官,听说他还准备继续活动,在明年把这个傻儿子外放到哪个州郡去当知府呢!”
“确有此事?”刘基皱了皱眉,双目寒光一闪即逝,不过语气十分平静,“你可有证据?”
“小生岂敢在这等弊案上撒谎?他们这些贪赃枉法之事,后来是被小生的知交好友、长洲县的县衙主簿穆兴平知道后才告诉小生的。”姚广孝从衣袖中取出一卷状纸,向刘基递了过来,“这份状纸里附有穆兴平的证词,他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写得很详细。而且,韩复礼的儿子韩通根本就不通文墨,愚钝无比。先生如不信,可以将他招来一审便可辨清真伪虚实!”
刘基接过状纸,慢慢地看起来。过了半晌,他才重新卷好了状纸,轻轻搁在石桌棋枰之上,双目似闭非闭,状如老僧入定,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显然,刘基已处于两难境地。
一来,此案证人证词确凿,可见这姚广孝前来举报之事确系实情,那么长洲县县令吴泽、中书省都事李彬等就应该受到惩处!但是,听说这个李彬是丞相李善长的侄儿。而且,李善长所统领的中书省又一贯以“清廉务实,勤政绩优”之名为朝野上下所称道,皇上为嘉奖、表彰他们,还曾亲笔御书了一张“官清吏廉”的金字大匾悬于其堂门之上!如果让皇上知道李善长所辖的中书省在开基立国不及半年便出了这贪渎大案,必会对李善长及其中书省内官吏这一贯廉明勤政的作风有所质疑,也会对他们有所贬斥。这让素来极好颜面的李善长如何下得了台?况且,自己将要查处的又是他李善长的亲侄儿!这对他的刺激将会更加强烈!唉!这事儿可真难办呐……
但是,纵容李彬等贪官污吏徇私枉法,又岂是我大明社稷之福?上下贪墨、政以贿成,是危及国本的大害啊!刘基心中一念及此,便回忆起了自己当年出仕元朝时所遭遇的那些事。那是十五年前,自己曾任元朝浙东元帅府都事,参与了平定逆匪方国珍兄弟之乱。那时,方国珍兄弟拥兵数万,在台州一带烧杀掳掠,全无抚民安众之举,只有割据称雄之心。刘基见状极为愤慨,便极力主张不能姑息养奸,对方国珍兄弟“掠夺百姓,滥杀无辜”的暴行要追究到底,必须将他们绳之以法、捕而斩之。却不料方国珍见势不妙,派人从海路潜入大都,用重金贿赂收买了元朝当时的执政大臣。不久,一道诏令下来,朝廷对方国珍进行了“招安”,晋封他为一方大吏。同时,朝廷对刘基的正确建议横加指责,说他“伤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将他免职并羁管于绍兴。贿赂之后,竟使得朝中黑白颠倒,是非淆乱一至于此!也正是从那时起,刘基愤然生出弃官而去之心,走上与腐败不堪的元朝的决裂之路。
而今,李彬等人竟敢在大明朝开国之初,便以身试法,贪污受贿。要知此风一开,后患无穷!自己身为监察百官、纠劾不法的御史中丞,又怎能坐视大明朝重蹈当年元末秽政之覆辙?
想到这里,刘基霍然一下握起拳头,并在石桌棋枰上重重一捶。他暗暗一咬牙,硬声硬气地说道:“这个案子,我们御史台审定了!不管它涉及哪一位权贵,也不管将来查处它的阻力有多大,老夫都要一查到底、惩处到位,绝不手软!”
姚广孝静静地看着刘基那一脸坚毅果敢之色,不禁肃然起敬。他深深躬身行礼谢道:“既是如此,小生就代天下百姓谢过刘先生了!这天下百姓都盼着我大明圣朝在这个案子上给他们一个公道。”
刘基听罢,神色也很是感慨,抬起头来,瞧着姚广孝,缓缓说道:“这样吧,姚公子先暂且在老夫府中住下,这样更安全一些。老夫这就赶赴御史台去布置一下,把长洲县的吴泽、穆兴平以及韩复礼父子先招来讯问一下。”
姚广孝沉吟片刻,冷静地说道:“刘先生若是真要在此案上着力,那就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出击。如果稍有迟疑,李彬他们只要听到风声,便会抢先把一切罪迹掩盖起来,反而不妙!毕竟,《大明律》里规定了官员只要贪污六十两以上的白银便要判处‘斩立决’之刑,更何况他们贪的是数千两白银啊!”
刘基深有同感地抚须点了点头。他向外唤了一声,招了招手,让刘德过来。然后吩咐道:“你到后院去收拾几间干净的屋子,把这位姚公子好好安顿下来,不许怠慢。”
刘德听罢,应承一声,便往后院办理去了。
姚广孝却向刘基深深一笑:“小生谢过刘先生了。不怕刘先生见笑,小生倒不会和您客气什么。久闻刘先生学究天人、博古通今、神机妙算,小生也正想拜您为师,留在贵府向您多多请教,以求增才进德。”说着,便向刘基一头拜将下来。
刘基慌忙躬身来扶,急道:“使不得!使不得!姚公子快快请起!老夫岂堪为你之师?你只要不嫌敝府简陋,在此居住下来,和老夫切磋才学,老夫已是惊喜过望。拜师之事,还是日后再说罢!”
(1) 事实上,刘基等人编撰而成之律书名为《律令》,洪武六年方在此基础上详定《大明律》,次年修成。为便于理解挪用此名。
(2) 姚广孝本名天禧,字斯道。而“广孝”二字,为朱棣“靖难”后所赐,因其广为人知,为读者便于理解,故用于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