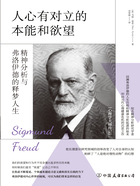

让我们从一个特别的历史时刻、一个特别的地方开始:1860年,4岁的西格斯蒙德·弗洛伊德(Sigismund Freud,他在青少年晚期才开始用“西格蒙德”这个名字)在他的妹妹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父亲雅各布·弗洛伊德(Jacob Freud,一名纺织品商人)和母亲阿玛莉亚·纳桑松(Amalia Nathansohn)的陪同下,来到了维也纳利奥波尔德施塔特的犹太区。尽管弗洛伊德是1939年9月23日在伦敦的汉普斯特德去世的,但他将永远与这个他几乎居住了一生的城市联系在一起。在这座城市里,精神分析的概念诞生于19世纪90年代,并在几年之后发展成了精神分析运动,正是这一运动让弗洛伊德拥有了全球性的声名和恶名。在1899年到1900年里,弗洛伊德最伟大的作品——《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发表了,这让人们很容易就将弗洛伊德置于19世纪末维也纳的背景下。这座城市现在经常被称为“梦之城”,它见证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艺术和知识的繁荣——新美学形式的诞生,音乐中的音调系统的重组,新的图画和装饰风格,以及建筑设计的试验。
但是想要理解弗洛伊德本人的文化形成,我们需要将他置于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中。当时的维也纳是哈布斯堡帝国的行政中心,经过了10年的新专制统治之后,正处于现代化和自由主义化进程的高峰。在19世纪的中欧,犹太人的命运取决于政治自由主义是否处于支配地位,而在奥地利及其相关省份,即使在1848年革命之后,政治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与法国或英国相比仍然很弱。奥地利在1866年奥普战争中的失败造成了奥匈帝国的双重君主制,自由党能够控制某些领域的政策,进一步推进世俗化,放任经济自由发展并返还了对某些地区的管控——至少对更富裕的中产阶级来说是这样的。这一充满活力的改革在帝国首都为犹太人创造了机会,到1867年,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边缘化、迫害,以及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限制,他们终于在法律层面上实现了平等。不出意料,19世纪60年代后期,向首都迁移的人数达到了高峰,尤其是来自东部省份的移民。世纪之交,许多犹太人成了维也纳文化精英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社会民主工人党创始人)和散文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他们是犹太商人或实业家的儿子,来自帝国王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现在都属捷克共和国)或西里西亚(在18世纪被普鲁士占领)。

1 米克莱勒广场,维也纳,1850—1888年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家族是这次向西移民的重要成员。他的父母都来自更东的加利西亚——哈布斯堡王朝在18世纪末分割波兰时得到的一个省,现在在乌克兰西部。雅各布·弗洛伊德和他的第一任妻子萨莉·坎纳(Sally Kanner)养育了两个儿子——西格蒙德同父异母的兄弟伊曼纽尔(Emanuel,出生于1833年)和菲利普(Philipp,出生于1836年)。当时,雅各布与萨莉的祖父建立了贸易伙伴关系,从此在摩拉维亚的一个小镇弗莱堡(现在的皮埃尔),两个家族开始建立了联系。萨莉去世后(约1852年),雅各布在这里认识了阿玛莉亚·纳桑松,并于1855年结婚[她实际上是雅各布的第三任妻子,但我们对他的第二任妻子瑞贝卡(Rebecca)知之甚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出生于1856年5月6日。一年半之后,弗洛伊德的弟弟朱利叶斯(Julius)出生,但是他在八个月大的时候就夭折了。弗洛伊德关于这个时期的记忆很少,其中最生动的记忆埋藏在一篇描述匿名患者的文章《屏幕记忆》(1899)里:一片陡峭的草地上点缀着些许蒲公英,他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伊曼纽尔的孩子约翰(John)和波林(Pauline)在草地上玩耍,一位捷克农妇和一名保姆在旁边看着。之后我们将看到,约翰在弗洛伊德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当时,在地区经济危机的刺激下,这个家庭分成了两个部分。1858年,伊曼纽尔和菲利普移民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在那里他们一起从德国和法国进口货物做生意,而雅各布和其他家人则短暂地搬到了莱比锡,之后又搬去了帝国首都维也纳。
维也纳吸引人的地方不只在于经济方面,还在于自由主义精神世俗化的暂时胜利,这也为犹太人从被控制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前提。正如犹太法学博士和政治活动家约瑟夫·S.布洛赫(Joseph S.Bloch)在1885年观察到的:“对犹太人来说,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教义、舒适的原则和当时的流行观点——这是他的精神庇护……在经历了一种难以形容的严厉和羞耻的奴役之后,他获得了自由的权利。”2从1861年开始,自由文化体现在了一系列宏伟的建筑中:议会、镇议会、大学、歌剧院,也体现在中世纪城市内部的防御工事被夷为平地,创建了一圈宽阔的林荫大道(类似于奥斯曼男爵在20世纪中期对巴黎的改造)上。这些改变代表贵族——联邦和天主教的神职权力被上升的资产阶级所取代。弗洛伊德回忆道,1867年的自由政府格外自信,他的父亲将一些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肖像带回家来装饰房子:“从此以后,每个勤奋的犹太学生书包里都带着一个内阁部长的文件夹。”3与自由主义政治相结合的是一套启蒙价值观,它是“普遍的”和“人文主义的”,强调理性、世界主义、个人权利和对伦理意志自治的信仰,而非宗教。这些都与德国启蒙运动的传统(而非奥地利当地的传统)有关——哥特霍尔德·以法莲·莱辛(GottholdEphraim Lessing)、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弗洛伊德的亲英性,以及他对亚当·史密(Adam Smith)、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J.S.穆勒(J.S.Mill)作品的狂热阅读,经常被世人注意到,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席勒、海因里希·海因(Heinrich Heine)和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是贯穿始终的文化参考点。正如犹太学者格尔肖姆·斯科勒姆(Gershom Scholem)打趣的那样:“对许多犹太人来说,与弗里德里希·席勒的相遇比与真正的德国人相遇更真实。”4弗洛伊德反复提到席勒,来证实他认为饥饿和爱是人类心理的两个基本动力的观点。1930年,当席勒在法兰克福被授予歌德奖时,他承认这个晚期的认可给了他一种特别的快乐。

2 弗莱堡,摩拉维亚,约1845年
德语在18世纪晚期成了帝国的官方行政语言,并在日益多语言的社会中变成了统治精英的象征。而哈布斯堡王朝的犹太人向自由主义的转变,让他们变得越来越想融入德国文化中。这让我们想起,1871年俾斯麦获胜之前,德国还是一个尚未统一的帝国,它更像是一种语言和文化理想,而不是一个已确立的政治实体。这种同化的代价往往是对犹太文化和宗教的抛弃: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维克多·阿德勒和精神分析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都皈依了基督教(尤其是新教,而不是奥地利天主教)。但许多以某种形式保留了犹太身份的人仍然认为,自己在文化层面是德国人(就弗洛伊德而言,他声称父亲让他在对犹太文化完全无知的情况中长大,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言过其实,因为他接受了希伯来语的私人教育,在后来的生活中,他也越来越强烈地认同自己“内心”的犹太人身份)。

3 弗洛伊德和他的母亲阿玛莉亚,以及妹妹罗莎(Rosa)和多尔菲[Dolfi,或阿多尔芬(Adolphine)],约在1864年
中产阶级犹太人的儿子主要通过进入高级中学融入德国化的高雅文化。这是标准的精英中学,类似于文法学校,致力于启蒙人文主义文化的发展,这对犹太家庭来说尤其有吸引力,因为传统上他们就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很高(1880年左右,维也纳高级中学的学生大约三分之一是犹太人)5。正如社会历史学家玛莎·罗森布利特(Marsha Rozenblit)所指出的那样,“在那里接受训练的年轻人对贺拉斯(Horace)、西塞罗(Cicero)和《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的了解肯定比《塔木德》(Talmud)和《托拉》(Torah)更多。”6弗洛伊德最初在家里接受父亲的教育,但他在1865年进入了位于利奥波尔德施塔特的文实中学,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一年了(1989年重命名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高级中学)。大家都说,弗洛伊德在这里的表现非常好,在班上名列前茅。他的妹妹安娜回忆,弗洛伊德在青少年时期沉迷于学习,他会独自在房间里吃饭,以免分散学习的注意力[家里并不富裕,有七个孩子——五个妹妹和他的弟弟亚历山大(Alexander),西格蒙德是唯一一个拥有自己卧室的人]7。在此期间,他打下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古典文明的坚实基础,这反映在他后来对考古学的迷恋上,他对“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的命名深入人心。
1873年的秋天,弗洛伊德作为一名医科学生进入了维也纳大学——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医学研究中心之一。他的专业在哲学学院开设了广泛的科学课程,包括解剖学、生理学和生物学,也包括了达尔文主义、磁学、电学、化学和数学,弗洛伊德额外选修了天主教哲学家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授课的哲学和逻辑学课程。大学所授的医学并不一定能让人成为医生,维也纳大学同样开设了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这是由于19世纪70年代的维也纳,受到了埃米尔·杜·波依斯-雷蒙德(Emil du Bois-Reymond)和恩斯特·冯·布鲁克(Ernst von Brücke)19世纪40年代在柏林的实证主义、机械主义研究取向的影响。这两位好友在1845年与赫尔曼·冯·赫姆霍尔兹(Hermann von Helmholtz)一起立下了著名的誓言:“除了物理和化学中共同的力量,没有任何力量在生物体中起作用。”8埃米尔·杜·波依斯·雷蒙德1848年的关键研究探索出了动物肌肉组织和电之间的关系,同年赫姆霍尔兹发表了关于能量守恒定律的著名论文,并开始继续研究知觉(perception)生理学。1849年,布鲁克搬到了维也纳,他是首个被任命为实现学院现代化的外国人,他还成立了一个生理学调查研究机构,带来了实证主义项目。
弗洛伊德似乎在自然科学和医学之间摇摆不定——1875年他从学校写信给他的密友爱德华·西尔伯斯坦(Eduard Silberstein),信中提到他决定攻读哲学和动物学博士学位,但一次到曼彻斯特对同父异母兄弟的拜访,让他对当代医学的进步印象深刻——很明显,对他来说,医学主要意味着进行自然科学研究。因此,他计划在1874年冬天去柏林参加杜·波依斯-雷蒙德和赫姆霍尔兹的讲座,但或许是缺乏资金,他的计划没有实施。1876年春天,弗洛伊德开始了他的研究生涯,同时仍然继续他的本科学习,并加入了动物学家卡尔·克劳斯的新海洋生物学研究所(当时是哈布斯堡帝国亚得里亚海财产的一部分)。研究所项目的内容是解剖并寻找鳗鱼的性器官,“6月30日晚上,我的手上沾染着白色和红色的海洋动物血液,细胞碎屑漂浮在眼前,这甚至进入了我的梦境,我的脑海中除了与导管、睾丸和卵巢有关的问题,什么都没有”9,弗洛伊德开玩笑地写给西尔伯斯坦。同年,弗洛伊德加入了布鲁克的研究所,在那里进一步研究,直到1882年(1881年他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

4 弗洛伊德家族肖像画,维也纳,1878年。后排,从左到右:宝拉(Paula)、安娜、西格蒙德、伊曼纽尔(同父异母的兄弟)、罗莎、玛丽(Marie)、西蒙·内桑森(Simon Nathanson)。前排:多尔菲(不确定),阿玛莉亚,亚历山大(不确定)和雅各布
除了被先进的科学发现所吸引,弗洛伊德还被实证主义方法本身所吸引,这也与崇尚自由主义、进步和现代性的德国文化联系在一起。克劳斯和布鲁克都是德国人[就像弗洛伊德学习过程中的其他关键人物一样,比如大学精神病学主席西奥多·迈纳特(Theodor Meynert),医学人道主义教授赫尔曼·诺斯纳格尔(Hermann Nothnagel)]。克劳斯是欧洲大陆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关键传递者,而布鲁克以反教会而闻名。这一时期,弗洛伊德的信件中充满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激进唯物主义哲学,他在1875年向西尔伯斯坦描述自己是一个“不信神的医生和经验主义者”10。
弗洛伊德研究兴趣的核心是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领域。通过在基本的物理或机械力基础上的构思,并在解剖、显微镜和电设备的帮助下进行追踪,他研究了有关神经真实功能的问题。这将他论文中那些乍一看令人奇怪的主题联系了起来,从他的首篇解剖学论文研究了鱼的脊髓神经根(Petromyzon planeri,1877)和淡水螯虾的神经纤维(1822),到关于染色神经束的新组织学程序(为显微镜研究做准备)的文章,以及他关于可卡因的作用和医学用途的系列论文(1884)。虽然弗洛伊德被认为“几乎”发现了可卡因的麻醉特性[他在一篇论文中提及后,最终由眼科医生卡尔·科勒(Carl Koller)发现了],在后来的论文中,他更多地关注生物碱对情绪和肌肉力量的生理效应。他所在研究所的老同事的工作也反映了类似的对生物物理学功能的关注,他们是西格蒙德·埃克斯纳(Sigmund Exner)、恩斯特·弗莱希尔·冯·马克斯(Ernst Fleischl von Marxow)和约瑟夫·布鲁尔(Josef Breuer),后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冯·马克斯发表了关于神经兴奋定律的文章,埃克斯纳试图对精神现象进行生理学解释(就像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弗洛伊德一样)。布鲁尔则转向了神经疾病的研究,后来他和弗洛伊德合作撰写了《歇斯底里症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1895),这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但他之前的论文主题涉及的是诸如呼吸调节和耳石功能等方面[与维也纳哲学家和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合作]。正是在这种活跃的研究环境中,弗洛伊德度过了他最快乐的大学时光。

5 弗洛伊德在1878年绘制的七鳃鳗(即泼氏七鳃鳗)
伴随着这些研究项目的进行,弗洛伊德花了8年的时间才拿到了他的医学学位——后来他将这一事实归咎于年轻时的拖延。但显然,弗洛伊德并没有游手好闲,在生理学研究所度过的漫长时光与他在研究领域寻找最佳机会的努力同样重要:接近自然科学研究,满足他的智识爱好的同时,又足够实用,足以在经济上支撑他。一个关键因素是1882年6月,弗洛伊德与玛莎·伯纳斯(Martha Bernays)订婚了,玛莎是汉堡亚麻商人的女儿、伊莱·伯纳斯(Eli Bernays)的妹妹,同一时期,伊莱在追求弗洛伊德的妹妹安娜[他们后来移民到美国,在那里,他们的儿子爱德华·伯纳斯(Edward Bernays)对公共关系领域的创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弗洛伊德和玛莎第一次见面是在1882年4月,仅仅两个月后,他们就私下订婚了,并约定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结婚。弗洛伊德立即辞去了他在实验室的职位——部分是因为布鲁克的建议,考虑到他现在还没有机会在该研究所立刻得到一个助理职位。弗洛伊德想要短时间内在维也纳总医院获得尽可能多的临床经验,这种经验是开办私人诊所必需的。在外科待了短暂的时间后,他在赫尔曼·诺斯纳格尔手下作了临床助理(内科最低的职位),六个月后在西奥多·迈纳特的精神病诊所担任二级医师(初级医生),随后是皮肤科和眼科,并于1885年获得了神经病理学专业的讲师称号。虽然没有薪水,但原则上,这个讲师头衔能够让他在大学里讲课,从而建立声誉,来吸引收入更高的病人。

6 玛莎·伯纳斯,1880年
临床上,弗洛伊德关注的仍然是研究而不是治疗上的成就,这反映了维也纳医学院的精神——与“治疗虚无主义”的联系而闻名。其目的与其说是治愈疾病,不如说是把病理解剖学变成一种诊断工具,将活体中可见的疾病症状与解剖台上的发现联系起来,这是著名病理学家卡尔·罗基坦斯基(Carl Rokitansky)在19世纪30年代末开创的一种方法。这种看似对人类生命漠不关心的态度也解释了医学院(包括迈纳特,他为弗洛伊德提供了继续在大脑解剖研究所进行神经学研究的机会)对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有关人类意志的悲观哲学的接受度。有一个关于弗洛伊德的小故事,描述了他在1884年专心照顾一位和他的未婚妻玛莎·伯纳斯有关的病人的情形,实际上这促成了他的第一本临床出版物——《脑出血病例》(A Case of Cerebral Haemorrhage)。弗洛伊德发现了许多症状,并据此推断病人的出血部位,他坐在病人身边观察到“病情不断发展,七点钟出现了对称性瘫痪,直到晚上8点病人死亡,没有任何现象逃脱我的注意”11。公布该病例是“必要的”,尤其是尸检能对诊断做出令人满意的确认结果。弗洛伊德在床边的态度很难给病人带来多少安慰。
还有一个因素影响着弗洛伊德从学术生活转向医疗实践——维也纳不断变化的政治氛围。19世纪70年代后期,维也纳已经开始反对自由主义和犹太人。尽管在学生弗洛伊德看来,1867年的自由派似乎是在为理性和进步的永恒之声辩护,但在他的学生时代,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版图正在被重新绘制,这将给日耳曼化的犹太人和他们同化所依赖的自由政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哈布斯堡在普奥战争中被俾斯麦的军队击败,这在短期内巩固了自由派的地位,也导致了一个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奥地利被排除在外。这使得那些哈布斯堡帝国的德意志臣民离开了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认同的国家。弗洛伊德的妹妹安娜回忆说,看到伤员抵达维也纳北站时,西格蒙德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敦促家人制作“绒布”,一种外科包扎用亚麻线。
与此同时,由王室和省份组成的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笨拙庞大的王国结构因其他新生民族运动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同样的失败导致了匈牙利的地方自治,捷克民族主义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在上升。正是鉴于这一初期的瓦解,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1878年从匈牙利佩斯特来到维也纳的犹太移民)最终发展起了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愿景,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在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的一段时间内,年轻一代的维也纳犹太人,如赫茨尔、维克多·阿德勒、古斯塔夫·马勒、作家亚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甚至弗洛伊德本人都将卷入德国文化民族主义(19世纪70年代中期,弗洛伊德在大学期间曾短暂地成为德国学生阅读俱乐部的成员)。讽刺的是,1885年,泛德运动的奥地利活动家乔治·舍内尔(Georg Schönerer)在其宣言中加入了一项条款,呼吁“从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消除犹太人的影响”12。
弗洛伊德最早在他的自传中分享有关反犹主义的回忆是在1867年左右,内容是他和父亲出去散步时的一次谈话(尽管相关事件发生在1851年雅各布结婚之前)。雅各布热衷于强调新兴自由主义时期的情况有多好,他回忆道:
稍后我们将看到,这次谈话和他父亲无法对抗压迫者的事实,对弗洛伊德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当弗洛伊德在1873年进入维也纳大学时(当时维也纳证券交易所的股市崩盘引发了一波反犹主义的仇恨)他发现自己也“被认为是低等的,因为我是犹太人”14。19世纪80年代初也在这所大学学医的施尼茨勒回忆道:“对公众视野中的犹太人来说,要忽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是不可能的,而其他人则不是……犹太人只能被认为是麻木不仁、咄咄逼人、傲慢自大的,或者极度敏感、害羞和偏执的。”15
1883年,弗洛伊德记录了他更直接的对反犹情绪的感觉:在穿越萨克森的火车上,他打开了窗户,这让他的同行者们感到不安。“从背后传来一声呼喊:‘他是个肮脏的犹太人!’”,当时几乎就要打起来了,但弗洛伊德最终似乎通过设法坚持自己的立场取得了胜利。然而,这一事件仍然为我们描绘了弗洛伊德每天都必须面临的不安全感和潜在的威胁。自由主义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一个关键因素是1882年选举权的扩大,推动了更多民粹主义政治的兴起,以及基督教社会党及其反犹领袖卡尔·路格(Karl Lueger)在1895年的最终胜利。事实上,正是自由主义对犹太人的认同加速了犹太种族的瓦解。
弗洛伊德19世纪80年代早期的书信中充满了“为生存而斗争”的思考。通过他与玛莎·伯纳斯几乎每天的往来书信,我们对他在这一时期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1883年6月,玛莎陪母亲住在汉堡郊外的旺兹贝克,尽管玛莎敦促弗洛伊德不要为了她放弃学术上的目标,但弗洛伊德敏锐地意识到,将他的生命致力于科学研究的想法可能会“破坏我们共同生活的机会”“我已经努力了足够长的时间,却一无所有”16。从1881年到1885年,弗洛伊德的经济和情感状况都很曲折。作为曾经的神经生理学家,他担心继续坚持过去所有的选择会危及自己的心理健康,但他设法获得了同事的支持,如布鲁尔和约瑟夫·帕内斯(Josef Paneth,他接替了弗洛伊德在布鲁克实验室的工作),两人借给他钱时说道:“我们都很穷,但会尽可能地互相帮助。”17

7 1873年5月18日,维也纳股市崩盘后不久,反犹漫画出版
乍一看,这场“生存斗争”与经济竞争和稀缺的大学教职有关。维也纳大学的晋升原则上取决于临床论文的发表,这需要通过大学的临床部门获得一系列有用的病例。然而,讽刺的是,布鲁尔作为私人诊所广受欢迎的医生,他的良好声誉阻断了弗洛伊德的晋升之路。诺斯纳格尔建议弗洛伊德先在一个小镇开始工作,等布鲁尔退休后再回到维也纳。不过,影响弗洛伊德做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仍然是对犹太人的偏见——即使后来,从经济安全和国际认可的角度看,他认为这成就了他的思维强度,“对于不被社会所接受这个事情,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被迫熟悉成为对立面的命运”为“一定程度上的独立判断”奠定了基础。18然而,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分析的一些梦是关于同事之间的竞争,他们都在充满希望地相互竞争,而由于“宗派”因素,晋升永远不会到来。1894年,布鲁尔在给阿道夫·埃克斯纳(Adolf Exner)的一封信中一反常态地抱怨道:“你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因素对我们这样的人有多么不好的影响。”同年,在该大学任教的53名犹太人中,只有2名达到了最高职位。19
因此,影响弗洛伊德逐渐脱离大学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他的信中充满了辛酸的失落、沮丧和焦虑。然而,与此同时,他对玛莎的承诺促使了他在经济上的独立,这给了他一个特定的目标,一个情感和生存的停泊地。通过长期的书信交流,他们逐渐取得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弗洛伊德也获得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立足点。他从未完全放弃对科研的向往,而是逐渐将其作为医生工作实践的一个分支。1884年底,弗洛伊德开始变得自信。到那时为止,他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的科学论文,包括他第一次发表的关于神经病理学的临床文章;他发表了关于可卡因生理效应系列论文的首篇;他马上就要获得学位(1月提交,1885年9月获得批准);他获得了直接的临床经验,在医院从事有偿的工作,并准备建立自己的门诊。他变得非常自信,可能很快就能与玛莎结婚,他在1884年11月给她的信中写道:“这意味着靠他人养活的生活结束了,‘山谷’(Dalles,意第绪语,意味着‘贫困’)也结束了。”20虽然10年之后,弗洛伊德才在科学领域取得了突破,并奠定了精神分析的基础,但28岁的他似乎已经完成了在智识和专业方面的积累,即将成为一名执业的神经病学家。
另一种生活:不同的历史
这段简短的历史遗漏了什么?从弗洛伊德最终成名的结果来看:几乎所有都被遗漏了。弗洛伊德成熟的作品揭示了自我的历史是如何被彻底改变的,记忆如何与外部经验联系,是什么将生活联系在一起。例如,他最重要的发现(以现在的时间节点来看,仍在未来)将涉及个人生活中最基本的双重本质。从表面上看,就像本章前半部分概述的那样,我们会有意识地回忆起关于自己的记忆、事实和描述。但也有另一种历史,由潜意识的记忆和幻想组成,我们最多可以在梦中或者非理性的担忧和焦虑中瞥见它,这些非理性的担忧和焦虑折磨着我们,让我们无法对自己和周围的环境有平静、稳定的认知。对弗洛伊德早期生活的叙述(让他的生活变得“有意义”并按时间顺序排列),不考虑这些引人注目的替代维度(即上文中的潜意识),这意味着什么?
举个例子,弗洛伊德在公开的自传体声明中对他所经历的反犹主义历史的评价往往是简洁、蔑视、没有感情波动的。但后来,在他对自己梦的自由联想中(在《梦的解析》中公开),他揭示了一系列更为复杂、充满情感的反应。在一个关于罗马城的梦中,他被迫带着孩子们逃离这个城市,他发现自己坐在喷泉的边缘,感到“非常沮丧,几乎哭了”21。会做这个梦的部分原因是弗洛伊德看了西奥多·赫茨尔的戏剧《新犹太人区》(The New Ghetto,1898),这部剧讲述了“犹太人的问题”和“对孩子未来的担忧,他们不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22就在做那个梦之前不久,他听说一个犹太人“被迫辞掉辛苦得来的在国家精神病院的工作”23。另一个有关罗马的梦促使弗洛伊德回忆上学时他对迦太基人而非罗马人的同情,这是他“第一次理解属于外来种族意味着什么”24。正是这个梦,让他认识到了那次与父亲谈论遭受街头反犹主义袭击的对话带来的长期影响,之后弗洛伊德(在他看来)对比了他的父亲与汉尼拔(Hannibal)父亲的不同反应,汉尼拔的父亲让儿子发誓报复罗马:“从那以后,汉尼拔就一直在我的幻想中占有一席之地。”25
类似的事件,还出现在弗洛伊德对他梦境的记录中,以一种跨越历史的共鸣,让过去与现在、真实与虚幻、个人经历与他人经历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它们让讲述生活的任务复杂化。工作中的失望、反犹偏见、弗洛伊德的古典教育和他的孩子们的教育,都在潜意识层面将弗洛伊德的精神生活与犹太人的流亡历史交织在一起(弗洛伊德在梦中喷泉旁的悲伤让人想起《圣经》中的诗篇《在巴比伦河边》)。弗洛伊德的梦也经常表现出想要跨越不同身份和不同语言之间象征性界限的愿望。在与汉尼拔有关的梦中,弗洛伊德惊讶地发现了许多德语海报。而一天前,他和一个来自柏林的朋友讨论见面的地点时,他曾提醒说布拉格可能不太适合德国人,并暗自希望他们能在罗马见面;在弗洛伊德逃离罗马的梦里,他的儿子念了一个神秘的词,一个希伯来新词——安格塞尔斯(Ungeseres),格塞雷斯(Geseres)的反义词,或意为“强加的厄运”。在梦里,经验变得模棱两可、语焉不详,就像罗马本身的形象一样:它是古典文化的宝地,深受歌德的喜爱,但它也是罗马天主教和犹太教冲突的根源,在古代,它是汉尼拔在意大利战役中放弃的城市,导致了随后对迦太基的报复和破坏。
尽管考虑这些深层次的个人材料需要跳出时间顺序,并借鉴19世纪90年代后期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和在研究梦时产生的关联,但现在把一些细节考虑进来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些细节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弗洛伊德的青年和学生时代。同样有帮助的还有《梦的解析》中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生活是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或描绘它。可以看到,弗洛伊德对精神生活的研究方法,在很多方面都是“历史性的”。精神生活是一段历史,它的叙述,就像刚才给出的关于罗马的例子一样,会根据不同的原则(心理甚至躯体的原则),与传统的叙述相结合。精神生活没有考虑记忆的表面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揭示了一些关于记忆可以解除我们对现实控制的方面,它揭示了另一种更隐秘、更令人不安的生活,以此来扰乱我们在现实中相对平稳的生活。
乍一看,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及相关作品中揭示的早期记忆似乎很平庸,甚至微不足道。有个场景我们之前提到过,弗洛伊德在弗莱堡的草地上和他的侄女、侄子玩耍,当时他大概三岁。另一个场景是他在维也纳的早期记忆之一,他撕毁了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中描绘了他和妹妹安娜穿越波斯的旅程。第三个场景是他在父母的卧室前“服从自然的召唤”而被父亲斥责。也许后面两个场景里发生的事可以被认为是孩子气的轻率之举,为许多此类自传增添了色彩——例如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被他的保姆殴打,或者歌德最早把家里的陶器扔出窗外的记忆。
然而,关键不在于记忆中的场景本身,而在于它们与潜意识思维过程的联系:我们精神生活的薄弱环节。弗洛伊德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我们的“意识”生活背后必须有“潜意识”维度的人。我们能够回忆和表达的思想和想法,其实是由潜在的神经系统、记忆系统和躯体系统触发的更广泛、隐蔽和自动化的最终结果。精神潜意识的概念仍然有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对那些科学家、道德家、哲学家和神学家来说,出于许多不同的原因,他们试图坚持将意识作为一个自主逻辑或心理实体的范式。正如弗朗茨·布伦塔诺在1874年发表的《从经验的角度看心理学》(Psychology from an Empirical Standpoint)中观察到的那样,大约在弗洛伊德参加他的演讲的时候,“假设一种潜意识”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是荒谬的,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认为这是一个“直接矛盾”。26尽管如此,那些致力于以后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的方式解释人类现象的人,理所当然地开始尝试建立关于更加晦暗不清的躯体及情感腹地之间关系的理论。布伦塔诺还在该书中引用了英国医生亨利·莫兹利(Henry Maudsley)试图将潜意识建立在生理学基础上的描述,实验心理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认为大脑可以做出潜意识推论的想法,以及哲学家和心理物理学家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的观点,即思想和感觉在被意识到之前需要达到一定强度的阈值。27
让弗洛伊德的立场脱颖而出[虽然类似于叔本华和尼采(Nietzsche)的观点]的是他声称潜意识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获得意识的途径,它绝不按照我们想象中那样,像一面理性的镜子反映我们的肖像、描述这个世界,以及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例如,弗洛伊德在他的回忆叙述中引入了“伪造”这一不稳定因素。回顾他最早的记忆,他确信至少有一些回忆是基于父母反复地向他描述。28其他的记忆,例如弗莱堡明亮的草地——弗洛伊德对他出生地唯一的“伪”印象,让人怀疑是合成的,其中本来经历的元素被后来的印象所取代,或嫁接在一起形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屏蔽记忆”。“屏蔽”或“覆盖”,指的是一种用令人更愉快的印象来掩饰或取代令人不愉快的印象的倾向。弗洛伊德认为,不仅是记忆中场景的呈现,而且它的选择(看似平淡的场景,而不是更具戏剧性的场景)可能都与历史的准确性无关。事实上,人们可能会质疑,“我们是否真的拥有任何童年时期的记忆”29。其实,我们所拥有的是讲述童年的记忆,它既是为了掩盖过去,也是为了揭示过去。
讽刺的是,另一个挑战我们对所熟悉的生活叙述的因素(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是记忆本身的“超记忆”特质。我们的潜意识大脑能够保留过去的那些微小的、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这远远超过了我们习惯中留下的少数印象。在19世纪90年代,弗洛伊德梦见了他童年早期的一个独眼医生:“我已经38年没有看过医生了,据我所知,我在醒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他。”30他在其他人的梦中也举了类似的例子——一个年轻人梦见过一只狮子,后来他认为狮子其实是瓷器,曾经是他“童年时最喜欢的玩具”31。比利时心理学家约瑟夫·德尔博夫(Joseph Delboeuf)在1862年做了一个关于一排蜥蜴的梦;在1877年,他在一本旧期刊中重新发现了这个来自过去的插图,这一定是当时梦中形象的起源。32德尔博夫说:“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印象也会留下不变的痕迹,而这种痕迹会无限期地重现。”33
然而,如果过去能够无限期地重现,那么它难道不会失去作为过去的意义吗?例如,弗洛伊德的侄子约翰在弗莱堡可能被“篡改”的草地上和他玩耍,他是他最早的玩伴形象:“直到我三岁之前,我们一直形影不离。我们彼此相爱,互相争斗。”34约翰从未完全超越弗洛伊德心中的那些印象。当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从英国来访问时,这像是早期关系的“回归者”。更重要的是,约翰“对我后来与同代人的所有关系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35。所以弗洛伊德渐渐明白了,他所有的朋友都是第一个人物的重新化身,就像地狱里的鬼魂,用弗洛伊德最喜欢的荷马的《奥德赛》(Odyssey)当中的比喻来形容则是“一尝到血就苏醒到新生命”36。
到目前为止,我们感到如此不可思议;一方面,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我们的实际回忆可能是伪造的;另一方面,我们拥有的大量印象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我们有意识获得的,而且,隐藏的过去还有能力无限地重复。但弗洛伊德对记忆的描述还有转折。首先,来自过去的力量影响着当下的体验,又重塑着我们的过去——孩童时期。这一点在晚上尤其明显,因为我们对思维的有意识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正如弗洛伊德在19世纪90年代末评论的那样:“让我们惊讶的是,我们发现孩童和孩童时的冲动仍然存在于梦中。”37至少,这让我们对传记形成的理解变得更加复杂。在弗洛伊德的生活中,人们显然将孩童抛在了脑后。
不仅如此,孩子的精神世界也与成人不同:“孩子完全是利己主义者,他们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需要,并努力满足,尤其和竞争对手、其他孩子,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相比。”38弗洛伊德开始对孩子感兴趣,他们可能成长为最有道德的生物,但同时又对撕裂甲虫和蝴蝶的翅膀并不感到内疚,孩子可以自由地释放本能的冲动。更强烈的是,他相信那些爱自己的兄弟姐妹,并在他们去世后感到悲痛的成年人,可能同时“在潜意识中怀有可以追溯到早期的邪恶愿望”39。“我希望约瑟芬死了。”一个孩子对她父亲说道。“为什么是死了?”她的父亲镇定地问,“不可以说她离开了吗?”“不,”孩子回答说,“那她还会回来的。”40弗洛伊德认为他是带着“敌对的愿望和真诚又幼稚的嫉妒”迎接他的小弟弟朱利叶斯的死亡的。41因此,我们不仅失去了对记忆的信任,隐藏在记忆背后的思想的各个方面在道德上也是不值得信任的,因为它们是幼稚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危险的孩子就在阴影里陪着我们。
弗洛伊德认为,在潜意识的回忆中,我们后天获得的道德和理性被一个更幼稚、由本能驱动的过去以躯体的形式所颠覆了。梦通常可以反映出明显的身体冲动,比如想要小便或喝酒。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详细叙述了探险家芒戈·帕克(Mungo Park)的故事,“当他在一次非洲旅行中几乎渴死时,他不断地梦见家乡水源充足的山谷和草地”42。当然,弗洛伊德因他对性的重视而闻名,他认为我们思想的各个方面都被情欲和冲动所支配。但在某些时候,弗洛伊德通过生理学方法中的训练,将思维本身视为一个分层的系统,来释放或抑制兴奋。我们知道,一个笑话不仅能让人愉悦,还能引起神经放松,让人笑得全身发抖。但是,如果所有的认知行为,不仅包括开玩笑、做梦,还有记忆,都能在身体的要求下发挥功能性作用,在需要的时候充当安全阀,保护我们免受令人不安的感觉和紧张的刺激,那我们创造的故事就都是我们的思想和身体能够接受的。因此,弗洛伊德发表了这一章开头的声明:“传记中并不存在真相,即使存在,我们也不能使用它。”
在这里,我想提前介绍一下,来自弗洛伊德19世纪90年代的作品——他的“压抑”和审查(censorship)理论。潜意识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储存着我们不朽的记忆和本能愿望,但每个人都有着“不愿向别人透露,甚至自己也不想承认的愿望”43。因此,在潜意识和意识之间存在着一个系统,用来抑制我们不想承认的想法和愿望的出现,它允许任何东西不经修改地通过,尤其是可能引发内部冲突、焦虑或不快的事物。在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中,弗洛伊德将那些被篡改的场景比作“降临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的和平,激烈斗争的痕迹已荡然无存”44。就像弗莱堡的草地,“绿色而茂密……我们正在摘黄色的花朵”,据弗洛伊德的家人说,他童年时与侄子玩耍的主要活动就是频繁的攻击行为。
这里列举了弗洛伊德在他的成熟作品中重新思考记忆和意识的功能的几种方式,这不仅是对未来章节的预告,还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更精神分析的角度考虑弗洛伊德早期发展的前奏。然而,单独而言,我们所概述的精神生活的任何特征,都不能完全抓住我试图唤起的“隐藏生活”的本质,在这种生活中,自由主体的模式对历史进步的信念,以及对真理、自我意识和理性动机原则的服从,都有可能被推翻。在本章前半部分的叙述中,我们曾提到过,年轻的弗洛伊德受到了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和科学理想的驱动。在弗洛伊德要发展的反叙事主义中,人的生活史有着不同的中心:大量潜意识的思想从某些被压抑或遗忘的童年经历中隐秘地向外辐射,让我们无法真实地知道我们是谁和我们采取行动的原因。在潜意识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完全的“所有精神价值的转换”45(弗洛伊德借用了尼采的这个词)。为了明白这在事件中意味着什么,我将介绍弗洛伊德的梦,这里不是解释他的梦是如何形成的,而是用例子简单地说明他对自己早期生活的印象,以及他的过去,这样的角度在许多叙述中被“低估”了。它们揭示了一种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类型的传记,甚至是不同的时间感。这个梦被称为弗洛伊德的“图恩伯爵(Count Thun)”之梦。
弗洛伊德很可能是在1898年8月凌晨的某个时候做了这个梦,当时他在去奥地利斯蒂里亚州的巴德奥西度假的途中,独自待在没有厕所的火车车厢里。他还增加了一些做梦前一天晚上的有用细节。在维也纳的韦斯特巴霍夫火车站等候时,弗洛伊德看到波希米亚前州长、现任内政部长图恩伯爵“用手轻快地”傲慢地推开了一名检票员,不禁大吃一惊。在剩余的时间内,弗洛伊德站在车站站台上,睁大眼睛,以免有人滥用职权占用车厢。他支付了头等座的全部车费,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打算“大声抗议,也就是说,要求平等权利”46,然后,他讲述了自己的梦(《梦的解析》中时间最长的梦),我将展示部分原文,以理解弗洛伊德传达的看似随机、无关紧要的内容:

8 威廉·沃勒(Wilhelm Wörnle),在齐格蒙德·拉勒曼德(Siegmund L’Allemand)之后,弗朗茨·安东·冯·图恩伯爵(Count Franz Anton von Thun)和霍亨斯坦(Hohenstein)的版画,1893年
至少,这是关于梦的表面报告,弗洛伊德将其称之为“明显的”内容。接下来还有大约12页的描述,但我只能在这里粗略地总结一下,试图梳理出那天贯穿他脑海的无数思想线索,根据他的理论,梦是浓缩的产物。弗洛伊德用于恢复梦中更广泛的心理环境的方法是自由联想——将每一个细节分开,看看它唤起的是什么链接或回忆,以便尽可能自发地将这些片段和场景重新精确地带入同一个梦境。通过分析大量的声音、人物和情节的爆发揭示出来的“潜在内容”,为弗洛伊德的生活和成长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见解——本质上,就是解释了“成为”弗洛伊德是什么感觉。
上述弗洛伊德对梦的重现被压缩了,但也展现了梦的混乱和迷人(完整的描述可以在《梦的解析》中找到)。弗洛伊德通过6种不同的语言寻找他的精神联系——德语、意大利语(他记得自己在站台上哼唱《费加罗的咏叹调》)、法语、英语(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的场景)、西班牙语和拉丁语。随着这张更广泛的心理地图的展开,它涵盖了几个省份和国家(卡斯蒂利亚、摩拉维亚、萨克森、英格兰),并涉及了弗洛伊德数十年生活的不同历史层次。包括1898年的紧急情况(包括即将到来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帝的金禧庆典),以及在梦结束时离开那位生病的绅士,与两年前他父亲生病和死亡的最后阶段的联系。
其他线索与弗洛伊德青年时期更为“公开”的过去中已经涉及的大量事件和主题有关:例如,与花有关的一系列联想最后变成了红白康乃馨,前者是社会民主党的象征,后者是反犹主义基督教社会党的象征。梦开始时的学生会议让弗洛伊德回忆起,他在大学早期通过激进的德国学生阅读俱乐部参与德国民族主义的事,也让他想起了他曾在高级中学领导的一场针对一位不受欢迎的研究生的密谋。
最终,对梦的分析让弗洛伊德回忆起了他七八岁时在父母的卧室里小便的情景,他的父亲因此责备道:“这个男孩将一事无成。”弗洛伊德还听闻,在这之前,他两岁的时候尿湿了床,但他还安慰他的父亲,承诺会给他买一张新的床。除了其他各种历史标记(参考1848年的革命和金雀花王朝),梦的联想还提供了弗洛伊德阶级等级观念的一个有趣缩影,他编织了一个卡夫卡式(另一个哈布斯堡王朝的德国犹太作家)的世界,里面有铁路官员、政府议员、专横的贵族、潜伏的管家、马车夫和妓女。
这显然是弗洛伊德的生活,但它是根据一种与之前叙述的历史非常不同且不光彩的逻辑来排序和相互联系的。通过这种浓缩成一个夜晚的梦的另类自传模式,关于弗洛伊德我们了解到了什么?它是如何重塑我们对弗洛伊德成长的感知的?首先,这里没有成长的感知。尽管梦中充满了现实事件,但这些事件在历史上是没有联系的:它们不是根据时间的流逝的感觉排序的。相反,它们通常会通过一个相当不寻常的元素,一个特定的声音或单词联系在一起。举个例子,那朵花,款冬(Huflattich),据说是德国人的最爱,伯爵在梦开始时轻蔑地提到它,让弗洛伊德想起了法语的蒲公英(pisse-en-lit,但字面意思是“在床上尿”),这又让他想起了童年的尿床事件。法语还让他想起了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的《大地》(La Terre,1887),在《大地》中有一场放屁(flatus,联系回flattich)比赛,弗洛伊德随后将其与为纪念英国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铸造的奖牌上的铭文联系在一起——Flavit et Disside sunt(他将他们吹散开来)。47考虑到弗洛伊德试图重建梦背后的想法和冲动时产生的多重联想,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为什么解析比梦本身要庞大得多,甚至更疯狂。
这些关联映射的不是历史或地理关系,而是一种神经上的亲属关系。在弗洛伊德看来,它们是心理上的联系,甚至可能在神经纤维和神经元的层面产生联系。无论是哪种,这肯定是一条“联想链”。对过去和现在的记忆,虽然在时间上是分离的,但在梦里,它们在精神上是连续的,它们共同存在并被压缩成一个超现实的、没有国界边缘的叙事逻辑,在这种叙事逻辑中,一系列的人物和场景不恰当地、荒谬地相互叠加。因此,很难将一个梦简化为一个信息,或一个单纯的结果。弗洛伊德鼓励我们不要按顺序阅读梦中的场景,而是寻找意义的集中点,即许多不同层次的相交点。
弗洛伊德这个梦的两个明显诱因是,首先,他对图恩伯爵的傲慢感到被冒犯(也许也很着迷);其次,小便的欲望最终唤醒了他。那么这两者之间又有一个隐藏的节点,那就是他在父母房间小便时幼稚的快乐,以及父亲对他的指责。压抑羞辱所产生的愤怒,也许是令人难忘的身体上的解脱和兴奋,在这个夜晚,似乎在精神联想的各个层次中产生了共鸣:开往萨克森的火车上的反犹对抗、学生时代的争吵,甚至玫瑰战争。这意味着,就像弗洛伊德的侄子约翰成为“回归者”一样,童年的撒尿事件也永远不会消失,在弗洛伊德的梦中,会对这一场景重复提及,并且这种梦“总是与列举我的成就联系在一起”,似乎是为了反驳他的父亲关于他将一事无成的判断。48如果梦有任何逻辑,那么就弗洛伊德而言,它就是一个渴望推翻所有羞辱的梦,最终,梦通过逆转父亲在童年场景中的角色,进行了报复,“这位老人(显然是我父亲,因为他一只眼睛失明是因为我父亲患有单侧青光眼)现在在我面前撒尿,就像我曾经在他面前一样”49。
这个梦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尤其是传记作家们想在其中找到一些弗洛伊德与政治相关的线索。文化历史学家卡尔·E.肖尔斯克(Carl E.Schorske)将其解读为弗洛伊德把来自外部世界的职业、社交的挫折感(他缺乏经济来源,他的边缘化和反犹偏见)变成了内心世界的冲突。在这里,图恩伯爵和其他无数官员以及竞争对手,可以象征性在内心的斗争中被征服,在这种斗争中,弗洛伊德更容易成为胜利者。“政治”问题在站台上的最后一个场景中解决了,梦境用垂死的父亲代替了活着的伯爵。这是对参与政治的逃离(尽管是为了科学成就),这说明了弗洛伊德对心理学研究的成熟转变。50
毫无疑问,这种解读的各个方面都是正确的。弗洛伊德自己也认识到,梦完全是自我主义的,它通过防御性地重新组织真相来弥补现实生活中的缺憾,这永远是做梦者的功劳。然而,要推断这可能也适用于弗洛伊德梦项目本身的框架(用一种逃避现实的感觉来玷污它)似乎是错误的。只有当弗洛伊德在他的潜意识联想理论中实现的一切(从记忆的保存时间和它充满情感的特质到幼儿生活的形成本质)都是不真实的、是一种幻觉时,这种批评才会站得住脚。但这无异于把身体、非理性、潜意识本身都扔掉。
如果梦可以是任何事物,那么在弗洛伊德手中,它就是记录物质生活中被压抑的思想的文件夹。这一切都在道德上不受束缚——但精神上并没有因此脱离束缚。相反,将梦的元素连接在一起的唯一原则是精神上的,在社会上需要的谨慎和道德关注的一切都消失了。引人注目的是梦的极端本质,它是内心暴力抗议的回响,也是宏大想象的逆转。在弗洛伊德的许多其他梦中,有一种对辩护和伟大的愤怒,他将其描述为幼稚的“自大狂(megalomania)”。关于在许多不同梦境中出现的厕所主题,他认为在梦中产生尿液是种伟大的幻想,他还以格列佛消灭掉利力浦特的大火为例,还有加纳图亚——拉伯莱“超人”,他“以同样的方式向巴黎人复仇,跨坐在圣母院,尿向城市”。51
在关于图恩伯爵的梦里,弗洛伊德的父亲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半盲、年老、摇摇欲坠,在站台上需要帮助来排尿,即使参考了垂死之人尿失禁的实际情况,这似乎也荒谬得过分了。它变得更加无礼了!弗洛伊德将这一幕与奥斯卡·帕尼扎(Oskar Panizza)的颠覆性淫秽戏剧《爱情委员会》(Das Liebeskonzil,1895)联系在一起。在剧中,失明、无能、有梅毒的上帝必须克制自己,以免他愤怒的愿望意外地毁掉人类,而博尔吉亚教皇则在复活节期间被衣着暴露的妓女款待。弗洛伊德回忆左拉的文字与其他梦的细节有关,包括各种弑父和谋杀的场景。《大地》中的父亲窒息,被活活烧死,在《萌芽》(Germinal)中有一个阉割的场景。所有这些都是用特定躯体的形式所想象的。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那样,关于伯爵的梦和梦中的思想唤起了身体的每一种主要功能,而它的各种愿望(胜利或复仇)都以生动的、发自内心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关键并不在于这是弗洛伊德有意识地想法或期望。他当然经历了对针对他父亲的这种敌意的羞耻、焦虑和抵制,我们将看到,这种敌意是通过漫长的内省和对自我分析技术的研究才被发现的。这反映在他潜意识的世界,或被他的潜意识所转移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由主要的情感和愿望驱动,追求内在的享乐。弗洛伊德(每个人)思想的“其他”方面吸收了他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细节,他的全部过往,并根据其自身不容忽视的、独特的逻辑进行了重新部署。潜意识的愿望没有屈服于外部权威(除了那些它已经内化的权威),尤其是弗洛伊德本人。它是永恒的,有多种意义的,孩子般有破坏性的。传统的社会身份和目标在其中消解。关于图恩伯爵的梦捕捉到了弗洛伊德最令人震惊、超现实和颠覆性的一面,但它也呈现了弗洛伊德对现代性的智识挑战的核心内容:有意识的头脑,以其有序的历史和理性,永远不会完全控制或重建这些在人的内心运作的奇怪且陌生的原则。

9 朱尔斯·加尼尔(Jules Garnier),加纳图亚在巴黎小便的插图,摘自《拉伯莱等作品》,第二卷(1897-9)
本章的后一部分概述了前面提到的一些领域。接下来我将介绍弗洛伊德对神经疾病以及神经症或歇斯底里病人的研究。1883年,他们只是弗洛伊德职业生活中的人物,但这种情况很快就改变了。1884年1月16日,他写信给玛莎说:“看到每个人都直奔尚未开发的神经疾病,我很生气。”52但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器质性神经系统疾病患者,我们往往束手无策,但是大量的神经症患者可以为一个开始私人行医的贫穷医生提供一条生机。两天后,弗洛伊德宣布:“今天我终于开始研究神经疾病了。”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