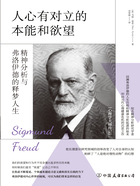
前言 弗洛伊德的余韵
1907年9月,一位热情的粉丝向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信,向他索要一张在最近卫生展览会上拍摄的照片。这位粉丝就是精神分析运动(Psychoanalytic movement)的新成员——瑞士精神病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弗洛伊德同意了,但他含糊其词地回复道:“请不要将我看得太重了,我只是一个凡人,不值得你如此上心。”1事实上,弗洛伊德十分厌恶这张照片,他更喜欢寄一些他儿子拍摄得不那么做作的照片。在这之后的许多年里,弗洛伊德的肖像被用多种方式记录了下来,包括照片、油画、卡通、蚀刻版画和雕像等。照片通常由他的摄影师女婿马克思·哈尔伯施塔(Max Halberstadt)拍摄,有的展现了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凝视,有的更像是随意的家庭快照。他的面孔为著名的《时代》(Time)杂志所钟爱,登上了1924年、1939年以及1993年的封面。弗洛伊德认为他的肖像被世人理想化了。在一辆摇晃的火车上,透过浴室柜上的镜子。他看到了自己的肖像,一幅由赫尔曼·斯特鲁克(Hermann Struck)1914年所作的蚀刻版画,而他将这幅肖像误认成了闯入包厢的不速之客(“我现在还可以回忆起,当时我非常不喜欢那幅肖像的表情”2)。然而在生命的最后16年,弗洛伊德患上了口腔癌。癌症手术切除了他的右侧上颌和大部分的上颚,面部不得不植入被他称为“恶魔”的假体,这让他感到非常痛苦,“恶魔”还影响到了他的听力和言语。
弗洛伊德的面孔还意味着什么?历史学家约翰·弗雷斯特(John Forrester)在2015年去世前尚未完成的书中提到,20世纪的核心就是“弗洛伊德世纪”。在这个世纪,全世界的人都在使用弗洛伊德所创的术语,梦到弗洛伊德所提的梦境,产生弗洛伊德口误(Freudian slips)、患神经症(Neurosis)、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e),无休止地重新审视自己的父母;在这个世纪,人们学着去爱自己的病症、创伤、愿望和潜意识(Unconscious),去大量地开弗洛伊德式的玩笑(Freudian jokes);在这个世纪,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被当作是科幻小说和哲学革命的科学分支3。自恋(Narcissism)、投射(Projection)、升华(Sublimation)、压抑(Repression)、矛盾心理(Ambivalence)等术语并非全部都由弗洛伊德首创,但精神分析将它们引入了20世纪的心理学,并将它们应用于临床治疗,同时在主流文化中进行了传播。而对于大量弗洛伊德的反对者来说,弗洛伊德无疑是个骗子,他的作品是专门为那些容易轻信和庸俗的人所设计的,是“精神手淫”“精神性感染”抑或是“大脑神话中地狱般的幽灵”4。
在众多的反对声中,纳粹对精神分析的打击无疑是最致命的。大量的犹太精神分析学家从中欧逃往美洲、英国(弗洛伊德本人逃往了英国)、巴勒斯坦和其他地区。他们成了难民,财产被夺走,家人被谋杀,文化被摧毁,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研究及医疗机构,不得不在陌生的环境中努力恢复原来的精神分析项目。自此,精神分析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精神病学的霸主地位被药理学和神经生物学所取代。在20世纪80年代,一场名为“弗洛伊德战争”(“Freud Wars”)的学术纠纷指控弗洛伊德用他的“幻想”取代了儿童被虐待的证据。精神分析经受了女权主义和反精神病学运动的攻击,不仅如此,它还从医疗机构纷纷撤资,转而支持其他更加经济的治疗方法,在危机中存活了下来。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精神分析已远远超出了其他源地和时间,成为许多不同文化和倡议的一部分,无论是在治疗、社会、政治还是在智识方面。有人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孟加拉地区和30年代的东京是弗洛伊德式的;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现代诗人是弗洛伊德式的;南非的种族隔离是弗洛伊德式的;在多年独裁统治下的巴西社会是弗洛伊德式的;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和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是弗洛伊德式的;犹太复国运动和1968年意大利的学生运动是弗洛伊德式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自恋文化”是弗洛伊德式的;20世纪50年代的伊拉克社会学是弗洛伊德式的;千禧年之后的中国是弗洛伊德式的。弗洛伊德的思想反复出现在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的马克思主义和反法西斯的著作中;在唐纳德·温妮科特(Donald Winnicott)战时关于英国母亲、社会关怀,以及19世纪40年代哈莱姆区反种族主义活动的广播中;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和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文化人类学中;在20世纪70年代西德同性恋的辩论中;在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文学与英国文化研究中;在德里丁(Derridean)的解构主义和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理论中;在20世纪90年代的创伤理论中;在今天的非洲悲观主义神经精神分析、酷儿理论和生态学中;当然也在当代心理治疗、社会工作、咨询、护理和早期教育学中有所体现。
精神分析常把自己当作过去的一门学科——精神考古学。毫无疑问,弗洛伊德的生活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20世纪早期历史上的许多戏剧性主题交织在一起,包括维也纳的性别文化、女性的歇斯底里(Hysteric)和现代心理学的诞生、现代性行为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文化理想的影响、中欧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兴起,这些都将在本书中讨论。但是精神分析本身并不是过去的事。我们仍能感受到弗洛伊德思想的余韵,我们在一个由弗洛伊德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的宇宙中生活和呼吸。现如今,随着心理健康焦虑日益蔓延,以及社会身份结构开始转变,人们呼吁解释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持续地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质,这些现象或许比以往都要多。弗洛伊德和后弗洛伊德(Post-Freudian)观点不仅在谈话疗法(Talking therapies)中反复出现,还进一步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发展紧密结合,重新创造出了适合21世纪危机的生活范式。
所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回看弗洛伊德,去讲述他的故事和精神分析的起源。弗洛伊德的故事尚没有定论,我们仍在决定如何看待他。但是我并不想像《时代》杂志封面那样,用一副年代久远的白人男性科学家的肖像来简单地概括当代世界的复杂性。这将精神分析看得太变幻莫测、太统一化了。在这本书中,我将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探寻我认为可以证明精神分析在当代仍然有存在必要的特征。这意味着本书不仅会涉及一直以来,人们普遍感兴趣的梦和神话的意义、性的本质、潜意识想法以及愿望的力量,还会涉及现代生活中的焦虑和神经疾病的体验。这尤其意味着,就像原子、历史和社会一样,我们的“我”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我们声称的自我、意识和身份都不是只有单一、简单的一面。我们的现实、我们和他人所感受到的主观现实,从来都不由我们随心所欲地处置。这其实是成功隐藏我们自己的一种解释、一种转换和一种机制。别的科学不会产生这么多弗洛伊德式的方法,如此敏锐地审视我们的精神生活,并且带动全球的专业机构去探究这样的问题:个人和群体是如何在功能上(或潜意识)隐藏真实的自我的,尤其是当触及最亲密、最富有情感的体验和最充满激情的依恋(Attachment)时。
谨以此书献给诸多的当代学者:肖尔·巴-海姆(Shaul Bar-Haim)、达格玛·赫尔佐格(Dagmar Herzog)、卡罗琳·劳本德(Carolyn Laubender)、乔治·马卡里(George Makari)、大卫·马里奥特(David Marriott)、安德烈亚斯·梅耶(Andreas Mayer)、斯蒂芬尼亚·潘多夫(Stefania Pandolfo)、丹尼尔·皮克(Daniel Pick)、卡米尔·罗西斯(Camille Robcis)、乔安娜·瑞安(Joanna Ryan)、拉卢卡·索雷努(Raluca Soreanu)、伊莱·扎雷茨基(Eli Zaretsky),以及所有我不认识的人。他们致力于在21世纪重现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创造出一种超越父权制、殖民主义、异性恋和性别不平等,以及特权的弗洛伊德学派。这并不是理想主义,这是至关重要的。许多他们的作品被作为本书的推荐阅读,其中有一些尚未出版。本书大量引用了最近的学术研究,希望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弗洛伊德对当代世界是如何产生影响的。然而现在,我们必须从过去开始——19世纪60年代早期,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