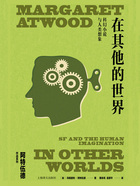
在其他的世界:
科幻小说与人类想象
飞翔的兔子:遥远空间的外来居民
这孩子已升到半空了,凭借翅膀浮着。尽管他没有像鸟儿一样来回拍打翅膀,但这翅膀悬在他的头顶上方,好似已稳稳地把他吊起,而不用耗费他自身半点气力。
——爱德华·鲍沃尔·利顿《即临之族》(1)
我已经讲过萨满和民间故事中的英雄,也讲过“负性质”——它能变化成“轻盈”并且使任何愿望在“飞行”中神奇地得到满足。
——伊塔洛·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
那些未被我们带入意识的,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投射为命运。(2)
——卡尔·荣格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便闯入了那个早年间被大众贴上“科幻小说”标签的现代神奇故事的世界。我的年少时光大多在加拿大北部的林区度过,和家人一起于林中守着年复一年的春去夏归,秋尽冬回。那段时间里,我接触文化机构以及艺术品的机会真是少之又少,因为当时不但没有日用电器、暖气炉、抽水马桶、学校、杂货店,甚至连电视也没有。收音机里只有一个俄罗斯的短波电台。没有影院,没有剧院,更没有公共图书馆。不过,书却很多,从科学教材到侦探小说,林林总总。尽管当中有些书可能并不适合儿童,倒也从未有人告诫我这本不许读,那本不能看。
因为没人有时间专门为我朗读,我很早就学会独立阅读了,因此小小年纪便能看懂连环漫画。报纸上刊载的连环漫画又叫滑稽人物故事。其中相当一部分虽然颇为夸张,却一点也不滑稽。比如《特里与海盗》(Terry and the Pirates)中有一名唤作“龙夫人”的蛇蝎美人,使一根极长的烟斗。还有一部分超现实得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比如《小孤女安妮》(Little Orphan Anniè)——她的眼睛在哪里呢?这些连环漫画在我那幼小的头脑里种下许多疑问,好些至今未能解答。魔术师曼德拉(3)在催眠状态下手舞足蹈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雪花公主(4)走动时要在耳朵上挂花椰菜?如果不是花椰菜,又该是什么?
我不仅仅阅读漫画故事,也早早提笔创作了,并且还画了不少画:绘画和阅读是山林孩子的主要娱乐方式,尤其在雨天。当然,彼时我的所作所画和自然主义一点边也沾不上。我想这一点我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因为一个不满八岁的孩子只对会说话的动物、恐龙、巨人,以及这种或那种会飞的人形生物——仙女、天使或者外星人之类的话题兴趣浓厚,可以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但是对于探讨什么温馨的室内设计或者乡村风景实在没有兴趣。“画花”是学校惯常教授的内容,不外乎郁金香、黄水仙之类。而我们真正想画的却更接近维纳斯捕蝇草,当然尺寸要大上许多,还有被吞了一半的耷拉在外面的胳膊和腿。
近来,我再次翻阅了一遍我的少儿时代的作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保留至今的那个年龄阶段的部分作品。与此期间,亦重温了自己早年非自然主义的写作癖好。当然,我所说的“少儿时代的作品”不是指威廉·布莱克或约翰·济慈在少年时期创作的老气横秋的诗歌,而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我尚在髫龄时做的写作尝试。(5)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我的超级英雄——会飞的兔子。它们的名字是“蓝邦尼”“白邦尼”,以现实生活中名字很普通的玩具兔为原型。这些玩具兔凭借古老的动力技术——“人工抛升”——时不时在空中飞一下。时隔不久,这对柔弱的英雄兔转变成两名硬汉,一个改叫“钢铁邦尼”,另一个改叫“疯狂邦尼”,以更加传统的超级英雄的方式飞行——借助斗篷。他们的不同之处是,钢铁邦尼的斗篷上的图案是条纹,而疯狂邦尼的斗篷图案是圆点,就此而言,十分清晰。
事实上,我的超级英雄兔的形象是基于对哥哥的天才想象的苍白模仿。是哥哥先于我发明了会飞的兔子——来自外星球的飞翔的兔子。他的兔子拥有各式的交通工具,配备许多先进技术设备——例如,宇宙飞船、太空飞机、武器库等等,应有尽有。它们不但与邪恶的天敌狐狸做斗争,并且与机器人、吃人的植物及凶残的野兽交战。那些兔子居住的星球的名字叫“邦尼之国”,而我的兔子则居住在一个更加神秘的地方——“恶作剧之国”。究竟是什么促使我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在“恶作剧之国”居住的兔子生活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乘着热气球四处飘游——这在二战期间实在可梦不可得。所以我对它们十分着迷。并且,我恰好又读过《绿野仙踪》,书中的巫师乘坐一个由巨型热气球拉动的大篮子,眨眼工夫就升入半空,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因此,我不仅让我的兔子们,也让兔子的宠物猫们能够依样升上天空。这是因为家中不许养猫,偏我又十分想要一只猫,所以假想我的兔子们养了许多的宠物猫。这些兔子只吃蛋卷冰激凌——战时及战后物资匮乏的年月里,十分珍贵又吸引人的食物。它们还会各种花样的技巧,特别是能凭借斗篷在空中旋出种种姿势。尽管这些兔子偶尔会邪气地笑着扣动手枪扳机,一时对射击热情万丈,一时又对追逐罪犯兴味十足,再不然就是忙于拯救世界,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似乎只想开心,捉弄人类。
而我和哥哥不过两个小屁孩,是从何处知道会飞的斗篷、超能力和外星球等概念?一部分乃因为当时朴素的超人连环漫画,比如从当年最红的闪电侠连环漫画中,我们知道了太空行走和机器人,从超人和神奇队长连环漫画中,知道了额外的力量和超能力,以及利用斗篷飞行。蝙蝠侠,虽是凡夫俗子,也没有神奇斗篷(大概因为斗篷会妨碍他攀爬建筑物),却与神奇队长和超人一样,有个弱小的、虚幻的第二身份作为掩护。(神奇队长其实就是比利·巴特森,乳臭未干的报道新闻的青年;超人的掩护身份是个戴眼镜的记者;蝙蝠侠就是布鲁斯·韦恩,有钱的花花公子,整日叼着香烟四处游荡。)
它们与《绿野仙踪》、希腊神话以及我们手头的关于太阳系的一本小册子一道构成了我们的核心创意的源泉。尽管有关太阳系的书本身还是十分严肃的,但有一点得说明,那时候人们对太阳系各大行星的认识依旧有限,人们仍旧认为太阳系有可能住着外星生命。在我们的书里,通常就是长着独眼和三指掌,不怀好意的人形外来生物;或者长着剃刀般锋利牙齿的,有各种阴暗卑鄙习性、好开膛破肚的动物;或者也可以是能对人放电或用毒气毒死人的鱼;又或者是长着毒刺或毒花瓣、有鞭子一样的触须的、消化能力极快的植物。因为父亲是昆虫学家、多才多艺的自然主义者,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获得丰足的科学图像,比如:显微镜下的池塘生物的图片。也许正是这些图片激发了我们对火星人、金星人、海王星人以及土星人的相貌的各种想象。
对于掩护身份,我注意到我的兔子们几乎都不需要:因为当时我们本就人小年幼,自己就能扮作比利·巴特森。而且我想,对那时的我们而言,将自己那孩童的自我意识投射在会飞的兔子上,足称得上是双重人格。
但是,滑稽故事连载主创关于超级英雄的奇思妙想又从哪里冒出来的呢?现在,我也十分好奇了。既然不能无中生有(6),那么究竟谁才是超级英雄的始祖?事实上,还真的存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基因库,比如:超人来自氪星,在某种程度上,三十年代的那本从头到尾都是K、Z、Y、X、Q之类古怪字母的科幻小说中的那个小孩也是来自外星球。
神奇队长口中那个充满魔力的咒语“SHAZAM”是由众多古老神灵和一个经典形象的名字的首字母缩写而成,他们是:所罗门、赫拉克勒斯、阿特拉斯、宙斯、阿喀琉斯和墨丘利。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神奇队长是顺着希腊神话的源流来到我们身边的。我们知道,神奇队长的导师、巫师肖扎姆(Shazamo)曾是喀耳刻(《奥德赛》中能够把人变成猪的魔女)的朋友。因此,我想神奇队长的创作者小时候读的书和我小时候读的应该相差无几。(神奇女侠的创作方法应该与其同出一辙,不过她与女神狄安娜(7)——那位身背银弓、正派典雅的女猎手渊源颇深。狄安娜女神手中的银弓弦肯定化作了神奇女侠手中的霸气索套。在神奇女侠的早年生活中,也即四十年代的连环漫画中,神奇女侠的另一个自我,狄安娜·普林斯,只要被她心爱的人史蒂夫·特雷沃亲吻就会开始颤抖,能量丧失殆尽,因为贞洁是原始女神的属性之一。)
另一方面,蝙蝠侠依赖技术横空出世。可惜其本质,乃一介凡人,生命终究有限,不无遗憾。但是他有许多机械装置和小零碎,可以助他对战邪恶。因此,当代杂志中和蝙蝠侠联系最紧密的并非《诡丽幻谭》(Weird Tales),而是《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从风格与装饰的角度讲,蝙蝠侠还是最具未来主义气质的英雄:哥谭市第一次出现在书中时,便一展其大气的风格,明艳的装饰艺术的感染力。
神话传说、关于外星球的科幻小说、现代技术,三者珠联璧合。尽管初见之下,神话故事成于远古,似与超现代格格不入,但是我们在神奇女侠、神奇队长故事中读到的内容却丝毫不令人感到突兀。
事实上,几乎所有早期连环漫画中那些耀眼的英雄,连同我那些除了耳朵和尾巴之外与超级英雄血脉相连的飞兔都根源于文学与文化史,甚至根源于人类心灵本身。
其他的世界
那么其他的世界和外来生物又源自哪里?为什么小孩子总对床下心怀畏惧,认为除了拖鞋之外,床下还有令他们恐惧的东西?这个床下怪物的原型是从史前一直遗留至今的吗?史前时代的人类是穴居老虎或者其他动物捕食的猎物。为什么孩子们会相信无生命的东西如勺子、石头,更别提那毛茸茸的泰迪熊玩具了——都与人一样有思想,对自己心怀善念或歹意?这三个问题相互联系吗?
孩子们从另一种存在角度看问题的能力最近引起了生物学家的广泛注意。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法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的《移情年代》(The Age of Empathy)(8)。人们过去常常以为只有人类能从另一个生物的角度想象生活。但事情并非如此,大象可以做到,黑猩猩(不是猴子)也能做到。我们推测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都有这一能力。一种验证的方法就是“照镜子”。动物看着镜子中的映象能意识到那就是自己吗?人们为大象安排了一次精妙的实验——在大象的面前摆一面镜子,大小同大象的身材相当。而后,先在象头的一侧涂上可见的标识,另一侧涂上不可见的标识以排除触觉因素。倘若大象看见反射成像上的标记后用鼻子触碰头上的真实标识,则表明大象一定清楚镜子里的这个“象”就是自己了。当然,在意识到这个映象就是自己之前,大象常常会先往镜子后面张望,就像人类的小孩子一样。
如果能在脑中勾勒或想象自己的模样,你就能同样在头脑中勾勒或想象一个非自身的存在物的模样。同理,你还能想象这样一个非自我的存在物如何观察世界,一个将你也包括在其中的世界,而你正可以置身此世界之外观察自身。在这个存在物看来,你也许是一位备受他人珍视爱护的人,又或是一位日后可以交往的朋友,甚至还有可能只是一顿可口的晚餐,一个势不两立的敌人。孩子们在想象床下情景时,其实就是在想象床下那个看不见的生物所意识到的世界——猎物的世界。告诉小孩子们他们看上去很美味可口,肯定不是什么好主意。小猫无论怎样活泼可爱,没有移情能力,对这样的描述自然置之不理,可是小查理们没准会吓疯了。
H.G.威尔斯的《星球大战》更为精彩的创新便是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微不足道的人类在智力远超人类的神一样的外星生物眼中的样子。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听着这样的故事,如莎士比亚所描述的,虽然他所思考的神明距离人类比火星人近些:“我们之于神明,如同苍蝇之于顽童。他们毁灭我们只为消遣。”(9)
* * *
住着怪物的其他非人类世界在人类的各种文学作品和神话故事中不胜枚举。我曾推测,包括孩子构想出的从未见诸出版的梦幻园在内,这世上想象出的地方比真实存在的地方要多得多。不论是我们死后要去的地方(好也罢,坏也罢),还是诸神与邪恶力量之家,抑或是已经消失的文明、远在一个星系之外的诸星球,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不在此时,不在此处。天涯海角之外,鸿蒙初开之前,渺茫不明的幽秘境界——“未来”才是它们的处所,甚至还有可能就在我们栖身的时空之中,掩藏着另一个它们可以存在的维度。依照惯例,其他的生物可以从某个地方倏然闯进,造访我们的起居室,但是他们也不能将他们所由从出的世界完完整整地一路拽进我们的世界。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可以穿越橱柜或虫洞,最终到达他们的王国。可见,一切和外来生物相遇发生的故事无一例外地需要“旅行”,非“进”即“出”。不是某些“人”或“动物”从“那儿”来到“这儿”,就是我们从“这儿”到“那儿”。大门、门道、关口和机车——仔细想想——如同远古神话中描绘的一样,处处是洞穴入口和燃着熊熊火焰的马车。
我们于幼年就具备构思“想象之地”的能力了,尽管它们不似晚餐桌上的猪排那么实在。首先,我们很小的时候,事物只要脱离我们的视线,就会脱离我们的脑海:我们没有看到的就是消失了,然后,忽然又出现了。等到一段时间过后,我们才醒悟滚落在窗帘后的橡皮鸭依旧在某个地方,而不是从此消失。
一旦我们认定东西是去了另一个地方而不是就此湮灭,这观念便再难以动摇。“发现东西本来好好地在这儿,却突然不见”的经历也许就是“来世”“心灵传动”等诸多概念的发端。斯科蒂(《星际迷航》)用光束将人传送上飞船的本领是受到我们小时候玩的藏东西、躲猫猫的游戏中一直没有消失的橡皮鸭的启发吧?过世的爷爷真的在幽灵世界里飘浮,想要联系我们吗?而等到有一天,我们也会像爷爷一样飘来飘去吧,因为我们实在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逝去的人一定是去了某个地方,而不是待在坟墓里。他们一定去过埃及,给自己的灵魂称重;或者穿过种满常春花的草地,或者升上天化为星星;再或者进入一个叫作天堂的实实在在的地方。如今,他们也许还能前往氪星或者所有外星人去过的地方。种满常春花的草地、氪星,(10)会是同一处地方吗?
进入其他的世界的一个方法是沿着文学的传承轨迹蹁跹前行,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狱一路走到埃及的来世,从冥王星之王国、基督教的天堂地狱、托马斯·摩尔笔下的乌托邦到慧骃国诸岛、莫洛博士的人魔岛,最终到达X星球、格森星和凯龙星。“其他的世界”在许多文化中都存在过,它们可以回溯到许多彼此独立的文学、文化谱系中。人类创造出种种其他的世界的癖好之本质属性会是人类的想象力吗,这种想象力会通过大脑边缘系统和新皮质,像移情能力一样发挥作用吗?
服装道具
从前,超能人类都像天使一样披着斗篷,或者像恶魔一样一丝不挂。但是在二十世纪,超能人类的服饰有了更相近的初始样板:紧身上衣和泳装,华丽的腰带,及膝高筒靴。这套装束极可能取自古香古色的二十世纪初马戏团的服装,尤其是马戏团表演走钢丝者或大力士的戏服。(正因为这个有趣的循环,国际摔跤联盟的巨星们今时今日的着装与连环漫画中的角色颇有几分相似。这些连环漫画中的英雄的衣服件件鲜亮,可以显出六块腹肌,使人联想起更早期的肌肉发达的杂耍艺人。)
斗篷这一装扮,也许来自形象设计者理应比较熟稔的前拉斐尔派艺术突出的骑士形象,当然也可能更直接一些,出自舞台魔术师的形象,甚至还有可能径向黑白电影《德古拉》中扮演吸血鬼德古拉的贝拉·卢戈西(Bela Lugosi)借取造型。尽管那时的吸血鬼还是邪恶的、浑身散发着难闻的气味,而不是今时经过演变后的模样——在太阳光下闪闪发光(11),是爱的年轻梦想。在古老的民间传说中还有一种隐形衣,它在威尔斯的小说《隐形人》(Invisible Man)中以现代科学发现的形式出现,在《哈利·波特》系列中仍以原始的魔法的形式重现,在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中摇身一变成为一种伪装保护材料。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超级英雄连环漫画中,没有一位拥有隐身斗篷(12)。这也许是因为隐形人实在太难画了。(我们最接近隐形的可能是神奇女侠的透明直升机,用虚线表现。)
面具不是超级英雄的必需品。不论是超人还是神奇队长都不需要这样的身份掩饰物,因为他们每一位都已有个完整的躯壳得以藏身。比如:克拉克·肯特,能在电话间卸去记者的行头之后,立即像被扔进水里的干凝胶圣诞老人一样,眨眼间膨胀成一个大块头的肌肉男。只不过,作者对这一项能力从未详细解说。蝙蝠侠的面具大概来源于假面喜剧的服装传统,或者像艾凡赫一样隐姓埋名的骑士的装束;甚至可能来自更加罪恶的源头,例如歌剧魅影,或者说方托马斯(Fantómas)——一位诞生于世纪之交的戴着面具的法兰西天才魔鬼;当然也可能只是来自连环漫画中的标准面具强盗。而蝙蝠侠乃一介凡胎,无法变身,因此他显然需要面具。
服装道具——或曰特别的衣服和徽章——历史悠久。在我们熟悉的各种典礼上,例如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你就需要戴着软兜帽或檐边帽,手上再捧着一个卷轴出席,有了这两样,你就改头换面,成为另外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你。在教皇的就职典礼上,新教皇将被套上“渔夫戒指”,在信众的眼中,这枚新饰物会赋予新教皇“强大只属于佩戴这个象征物之一人”的精神力量(几千年以来,戒指中蕴藏了种种殊异的力量,看看《一千零一夜》中的魔戒,以及理查德·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系列和J.R.R.托尔金笔下与前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魔戒》,它们都汲取了更久远的文化传统)。在加冕典礼上,有魔力的物品就是王冠和权杖——它们代表着王权,就像国王一度被当作王国的象征。时代越往前推,所佩戴的或所持有的物件的意义就越重大。在神主时代,例如古埃及、古苏美尔,无论男女,他们与服装、徽章融为一体:你即角色,这个角色是外观,是装饰,人住在角色里,而不只是裹在衣服下。
想想我们所了解的最古老的诗歌——《美索不达米亚的轮回》吧,它又称作《伊南娜下冥界》(Inanna's Journey to Hell)。生命女神伊南娜下到冥界去找姐姐死亡女神厄里斯奇格。在下到冥界的途中,为了自我保护,伊南娜身上戴着、手中拿着数量多得惊人的护身符和法宝:特殊的便鞋、七枚徽章、沙漠皇冠、女王的假发、枝条、珠宝、两只胸针、金戒指、面妆用品还有一件象征主权的披风。但是根据冥界的法律,伊南娜必须放弃所有的东西,因为法典规定任何人都不允许携带任何东西。当所有用来保护她的法器被剥除得干干净净,伊南娜立时赤条条得无遮无挡,死在冥界,被挂在钉子上。每个阿喀琉斯都有一个脚踝,一个易受攻击的软肋;每个超人都会遭遇一块氪石,一种能对抗特殊能力的力量。
美索不达米亚传说的结局皆大欢喜。伊南娜是生育和繁衍之神,让她永留死亡国度也是一种灾难。可是没有一个凡人能够被送入冥界,为伊南娜带去生命之水,让她复活。因为凡人入冥必死无疑。为此,水神和智慧神恩基(Enkil)用自己的甲垢捏出两个不受肉体凡胎之困的泥物,并将它们送下冥界。可以这么说,这两个泥人赋予了我们灵感,让我们想象出石魔的原型——那座会变活的雕像,并最终制造出了机器人。尽管这首诗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伊南娜在回到人间的途中是否将自己的法器悉数收回,但其实这根本毋庸置疑,因为在诗的后半段,伊南娜又戴上了那顶象征权威的皇冠。
然而,专用服饰、护身符和高高在上的权力,三者间的纽带究竟比美索不达米亚的传说还要古老多少?答案是要古老得多。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中极罕见的人物画中就有一部分实际上只能算半人半兽像:人们认为他们这些萨满通过披毛戴角,能够使自己成为半人半兽——能同野兽思想相通,确定野兽的行踪,甚至要求它们将自身献给饥肠辘辘的族人。
正是这些服装道具连同与之紧密相关的仪式使萨满神秘的力量具象为一种实在。狩猎人萨满与族人住在一起,而不是住在宫殿或寺庙,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过着平常的生活。一旦情势需要,他们就把自己变成充满魔力的另一个自我,服务全族。有一部描写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电影《十只独木船》(Ten Canoes),以原初形态的原住民文化为背景,其中就有类似的情节。当人们需要萨满施行法术,他便走到树丛的后面,等到他再次现身时,已然全身覆彩,准备施法。萨满是个有双重身份的人:普通的自己和另外一个拥有各种非凡能力的、能在有形的和无形的世界间游走的人。那些专门的装饰就像神奇队长的衣物,在观众的眼中标志着他进入了一个转换后的状态。
双重身份
超级英雄们之双重身份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但是最近的先祖大概出现在连环漫画问世前不久。
在十九世纪的小说中,替身的数量和他们在歌剧与芭蕾舞剧中的数目一样多得数不清。《天鹅湖》中的黑白天鹅公主,史蒂文森笔下的杰基尔医生和他那个矮小、年轻、毛发浓密的替身——下贱的海德先生,王尔德笔下的道林·格雷和他那幅病恹恹的、堕落的画像,爱伦·坡笔下的威廉·威尔逊和他那整天奚落别人的双胞胎兄弟,他们都是文学中最著名的替身典范。有人推断,这样的善恶共生至少在真实的人类生活中多少是有根可寻的。比如:乔纳森·威尔德(13)除了当捕贼队队长,还过着另一种不为人知的生活——罪行的幕后策划者。再比如爱丁堡执事布罗迪,一名受人尊重的绅士,人们相信正是他的夜半罪行给予史蒂文森以创作灵感。
但这些都是邪恶的替身。至于作为强大、正直的英雄的外表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替身——那些以柔弱、轻佻的“他我”——更确切地说,如同克拉克·肯特是超人的替身——让我们觉得自己更像在注视着“红花侠”(14)——白天是优柔寡断的花花公子,晚上则是意志如钢铁般的拯救者。甚至在大仲马笔下的基督山伯爵也有几个化名,包括扮作古怪的英国贵族,赏善惩恶。夏洛克·福尔摩斯,聪明绝顶的线索追踪者和罪犯猎人,同时也是伪装的泰斗,常常假扮成与自己相去甚远的角色:虚弱、慈祥、年迈的牧师,没有客人的马车夫等等。
除了假扮成“正常”的其他人之外,这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超级英雄也被安排了一两位强大的敌手。卡尔·荣格坦承,他的“心灵地图”多是以文学、艺术为基础。他的“阴影”理论,即人的阴暗面理论与《霍夫曼的故事》(15)以及我之前提到过的任一“双重身份”故事有许多共通之处。生活分裂、不停卷入神魔之战的连环漫画人物很可能表现出荣格心理特征。事实上,蝙蝠侠就是这样一个可供研究的几近完美的典型。
蝙蝠侠有三大劲敌,在荣格学说的拥趸眼中,俱是布鲁斯·韦恩的心理投射。韦恩必须接受并与他们妥协。(用布莱克的术语,这两个男性敌人被解释为萦绕在他心头的恐惧,而女性劲敌则是布鲁斯的内在精神的“外在表现”[Emanation]。)对于布鲁斯而言,女性元素是与他本人相悖的——坚定的独身主义者的生命里不需要路易斯·莱恩这样多愁善感的好姑娘。但是和他冲突不断的妖柔而魅惑的猫女定是布鲁斯的荣格的“暗黑灵魂”(dark anima)的形象投射:连小孩子都看得出布鲁斯和猫女的感情纠缠不清。
以险恶的扑克牌中的小丑形象示人的、残酷成性的“小丑”是蝙蝠侠的荣格阴影——他对衣着打扮及笑话的爱好越发透着邪气。还有另外一个阴影恶棍——企鹅人——穿一身能让人想起从前穿鞋罩、叼烟斗、戴高帽的资本家的卡通形象的衣服。他的普通身份的化名甚至可分成三个响亮的组成部分,属于凭空捏造出的、相当自命不凡的、阔老爷似的英文名字:奥斯瓦德·切斯特菲尔德·科波特。这企鹅便是花花公子布鲁斯·韦恩那“富豪”的一面变得让人讨厌时的样子。
神奇男孩罗宾(Robin)是布鲁斯的护卫。布鲁斯是同性恋吗?这一点无须怀疑。依我们神话学思想家的观点看,罗宾就是自然元素精灵,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帕克和爱丽尔。注意,罗宾本是鸟儿的名字,而这个名字又将他与天空联系在了一起。故事中罗宾的作用就是帮助仁慈的魔术大师——蝙蝠侠完成他的计划。然而,在荣格学说的信徒眼中,罗宾只不过是像小飞侠彼得·潘一样永远长不大的,代表着生活在布鲁斯·韦恩心中倍感压抑的孩子。我们应该记得布鲁斯的亲生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遇害身故了,这段经历阻碍了布鲁斯感情的健康成长。
一旦认真研究,你会发现连环漫画中的超级英雄们终究是些“稻草人”,至多稍改头换面而已。透过霍夫曼派的神奇眼睛观察,这些超级英雄与荣格本人都可以被视作同一部神话故事的一部分。
但在小孩子的眼中(小孩子是这类书的主要读者),罗宾就是我们自己——倘若我们也有面具和斗篷,我们也会穿上,然后隐在谁也辨不出的假身之内到处撒欢。当然如果晚上能推迟睡觉,并因此获得首肯,得允参与我们天真地以为只属于成人世界的事情就更美妙了。
飞翔
蝙蝠侠不能真正飞翔,这多少影响到我们对蝙蝠侠的好感。因为有图为证,飞翔是我——当时的小小超人卡通迷——最痴爱的超人特质。在我自己创作的“恶作剧之国”中,几乎一切都是借风而动。我究竟为什么如此痴迷飞来飞去的生活呢?细细琢磨,为什么超级英雄创作者们同样痴迷于此呢?
对飞翔的钟爱似乎十分普遍。我最近认识了一位“超级英雄”——尽管个头矮小——名叫“肾脏男孩”(Kidney Boy)。我是在“推特”上发现他的,受他的名字的启发,我提出要为他设计一套装备,包括特殊能量和魔法咒语。在现实生活中,“肾脏男孩”有些书呆子气,是一位肾脏专家或者说肾科医生。他告诉我,很希望自己会魔法,如此可以为肾透析患者“度身定变”出完美的、全新的肾脏。但是倘若无法拥有这样的魔力,他说,他是否可以“至少拥有能够飞行的魔法”?
因此最后,我专为他设计了他想要的一切:携带紫色肾脏形头盔的外套,永远精准的魔法手术刀,以及咒语——“肾脏——变——哦!——”,不但可以随心变成需要的肾脏,而且可以将新肾脏轻松无创地滑入患者体内,当然最美妙的部分还是“随心飞行器”。
个体发生重复着种系发生——难道“肾脏男孩”和我都继承了对飞行的爱好?是因为它已经刻在我们自身的基因或是模因(memes)里的结果?又或者如理查德·道金斯推广的理论产生的效应——主题、思想、意念代代相传,并在此过程中不停自我复制,自我突变,并同时与其他的文化基因竞争。
然而,无论是什么原因,有一点毋庸置疑:不论是否借助翅膀、飞行鞋、飞行斗篷、天马、飞毯、热气球、空气动力肾脏,飞行的能力历史悠久。
飞行能力,无论超人的还是神的,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在此讨论的飞行器既不是民用飞机也不是直升机,无关更迅速、更高效、更现实的交通工具。它只与翅膀相关联,或真实可见的或含蓄引申的,既能飞升至地球上空也能轻而易举地从一个地方滑至另一个地方。它冲破身体的局限,摆脱这副终将湮入尘土的臭皮囊的羁绊。古代僧侣总会低声吟唱“假若我有天使的翅膀,我要飞越监狱般的高墙……”我们没有翅膀,但对它的渴望从未停止。
尽管,最初,你可能会认为拥有翅膀有百益而无一害。但事实上,那些非人存在拥有翅膀的例子对此予以了警示。
例如,伊南娜,上文提到过的美索不达米亚的生命与性的女神,就有一双翅膀。但是你绝不会想与她扯上半点瓜葛。因为伊南娜和她的化身伊丝塔——《吉尔迦美什史诗》中的女神——都是生冥两界的旅者,擅长引诱倒霉的男子。当伊丝塔要求吉尔迦美什做自己的丈夫时,他列举了一长串被伊丝塔杀害、折磨或者变成狼或侏儒的前任情人的名字。
在希腊文化中,有两名神的使者:伊丽斯,始终在道义上保持中立的金翅神;赫尔墨斯——掌控沟通交流之神。(无怪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贝尔电话簿上会印有赫尔墨斯头戴金翅帽、脚蹬插翼罗马靴的鬈发、帅气的画像,此外还赋予了一点现代气息——大量粗壮的电话线温柔地缠绕在他的腰际。)赫尔墨斯也是行路者的保护神,引导死者的灵魂去往冥界,因此和他一道旅行真的未必是一件幸事。还有尼姬(Nike)(16),被认为是胜利女神,更确切地说是宣布最终胜出方的女神,是另一位信使。她也有一双翅膀。然而我们很清楚一方胜利必然意味着另一方失败。
在犹太基督教的传统观念中,从神域来的信使被称作“天使”(angels),而angel一词在希腊语中即为“信使”的意思。在希伯来语中也是同样的意思。《圣经》中,天使也并不总是被描绘成有翅膀的,在更多的情况下,皆以人的面目出现。尽管《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六翼天使有六只翅膀,《新约》也明白无误地记载着一些天使能够飞翔并即时传送信息。在后来的艺术作品中,长着翅膀的天使的形象很可能是借鉴自尼姬、伊丽斯,而年轻的小天使的形象则可能取自爱神厄洛斯展开双翅的形象。但无论是有翅还是无翅,天使绝对拥有令人不安的本质。倘若你被告知自己的家乡将毁于地狱之火,或者一位未婚女子将身怀六甲,这种消息能有多愉悦呢?文艺复兴时期,圣母马利亚的种种表情便常常表现出恐惧,而非欢乐。伊丽斯、赫尔墨斯或者任何一位犹太基督神使的造访,带来的可能是好消息,但更有可能是坏消息。
事实就是如此,我们不一定要因为他们是会飞的神祇便笃信不疑。圣人的预言、信使的消息常常极其地含混不清。
变形的诡计
赫尔墨斯,插上了翅膀的信使,不但是交流之神,还是小偷、骗子和说笑话的人的保护神。许多飞来飞去的非人类都有这一有趣的特点——古怪的幽默感。他们喜欢误导众生,捉弄众生,并乐此不疲。在莎士比亚的多部戏剧中,如我之前提过的,有两位值得注意的会飞的非人类:《仲夏夜之梦》中的帕克和《暴风雨》中的爱丽尔。二者都是信使、仆人。各自负责执行奥伯龙和普洛斯彼罗的计划,传布奥伯龙和普洛斯彼罗的法令。二者又都是伪装艺术家、恶作剧者。他们的形象不都是取自生翼的厄洛斯(又称作丘比特)——臭名昭著的、爱开玩笑的爱的小男神,女神维纳斯的信使吗?如今,丘比特可能会带上许多巧克力,而从前,他会将伤人的情欲之箭射进人心。中箭者因爱欲、痴恋和欲求不得而癫狂迷乱之时却是丘比特开怀大笑之际。《一千零一夜》中的灯神亦与信使和仆人相当。《绿野仙踪》里的翼猴同样无出其类:行止飘忽,能量滔天,除了用魔法之外很难控制。英国民间传说里那些在道义上无信可言的仙女同样表现出这一族群相似性:掩饰真面目、愚弄人类是她们最引以为傲的本领。帕克就强烈地表现出这一血统的特征:让他感到莫大乐趣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张凳子,等到有人想要坐上去,又倏然掠开。捉弄本来就不聪明的凡人正是帕克的一大消遣。
仔细想想,早年的连环漫画中的超级英雄无一例外地有此嗜好。虽然一般说来他们不是天生的愚人者,但是他们的变形无一例外带有欺骗性质——没有人知道克拉克·肯特就是超人,或者意识到超人就是克拉克·肯特。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桥段不是解救妙龄少女,也不是哥谭市最终幸免于毁灭,甚至也不是又打、又捶、又挠的空手肉搏战。孩子们喜爱的桥段只是在一个个变身的时刻。上一刻还是一位戴着眼镜、羸弱、腿脚不便并常遭奚落的报童,下一刻褪去所有伪装,立时长成强壮结实的赳赳武夫,好像费多的滑稽剧(Feydeau farce)(17)中从柜子里弹出来的一个伟丈夫——多么让人惊喜!——坏人闻风丧胆,恃强凌弱之徒再也不敢在沙滩上把沙子踢到你的脸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喜爱的“愚弄”——在成人堆(连环漫画中走在街上的成人)里自由穿梭却丝毫不引起怀疑。清楚自己身上有大人不了解的东西:拥有并隐藏的能量足以让他们目瞪口呆。
从这一方面来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超级英雄塑料超人(Plastic Man)可谓冠绝群雄。他的超能力是伸缩自如。因为他是塑料制品,在一大罐混合化学剂令人不愉快的作用下诞生,近似于生而为神子,或者说类似阿喀琉斯在冥河中浸泡过——他可以将自己变成日常可见的各异的形状,比如油灯、烟灰缸;偷听骗子和暴徒的密谋,之后一跃而起,亮明身份,像一根长长的橡皮带紧紧缠绕住作恶者的身体。塑料超人大概是所有超人中最狡猾、最机智、最不暴力的一位,与其说像奥伯龙,不如说更像帕克,颇似滑稽的派对小玩具的味道。
伪装的魅力几可溯及远古。诸神常常幻化成各种凡物,以便于在人间行走时不被发觉。(这一习惯后来沿袭下来。民间故事中的苏丹、国王甚至圣人都爱乔装改扮,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圣彼得。)而文学作品中,第一位自觉乔装的人物,或者说第一位非神的乔装者,据我所知,应该是《奥德赛》中经年漂泊离家的奥德修斯。他返回宫殿时,把自己假扮成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发现一大群粗野的年轻人正在肆意享用宫中饲养的禽畜,凌辱侍女,甚至还想娶自己的妻子。可以想见,当他拉满那张巨弓——一张充满魔法、除他之外无人能开的神弓——他又变回国王了,他把他们全部射杀了。奥德修斯特别青睐的有两位神,一位是雅典娜,知识与智慧女神;另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赫尔墨斯,善谋划、喜恶作剧的骗子的守护神。
一切都引领我们回到我六七岁时画过、并为之写过故事的飞兔。现在我们了解了为什么它们的居所会被我命名为“恶作剧之国”,尽管回想当年,连我自己也并不十分明白为什么非要起这么一个名字。像许多艺术家一样,我这么命名只因当时认为舍此无他。热气球、飞行、超能力、恶作剧,它们缺一不可。当然,我的飞兔也许是绝无仅有的长耳朵、白绒尾巴的超人。
(1) 鲍沃尔·利顿《即临之族》(The Coming Race,1871)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人类的超级种群:居于深穴之内,利用一种内部带电的生物体“维利”(vril)获取能量。(“维利”还被用来为一种牛肉汁命名,即“保维利”牛肉汁。)这种人依靠“维利之翅”四处飞行,并表现出超常智力。他们的女人比男人更健壮、高大,因此,男人不得不善待女人,以免女人飞跑了。
(2) 荣格的话摘自《遇见阴影:人类天性中黑暗面的隐藏力量》(艾布拉姆斯和茨威格,1991)。
(3) 据说魔术师曼德拉是史上第一位连环漫画超级英雄。但他的催眠手势却来自卡利加里博士和马布斯博士。(他们俩是讲述邪恶催眠术的两部同名电影里的恶棍。)
(4) 雪花公主是连环漫画《坎画》(Steve Canyon)中的人物。
(5) 这本少年读物现被收藏于多伦多大学费舍尔(Fisher)图书馆。
(6) 原文为拉丁语:Ex nihilo nihil fit。——编注
(7) 狄安娜: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贞洁、善射,与飞禽走兽关系亲密。
(8) 法兰斯·德·瓦尔,《移情年代:大自然给更好的社会的一课》(2010)。
(9) 莎士比亚的话摘自《李尔王》第四幕第一场,32—34。
(10) “种满常春花的草地”在希腊神话中的阴间,氪星是超人的故乡。
(11) 闪闪发光的吸血鬼在斯蒂芬妮·梅尔的《暮光之城》系列中可以找到。
(12) 隐身斗篷是民间故事中的特色物件,参见《格林童话》。
(13) 我第一次读到乔纳森·威尔德的双重身份是在哈里森·安斯沃思的小说《杰克·雪柏德》(Jack Sheppard,1840)之中。
(14) “红花侠”是奥希兹女男爵(Baroness Orczy)1903年创作的戏剧和据此改编的小说中的英雄。
(15) 《霍夫曼的故事》是奥芬巴赫创作的歌剧(1881)中的人物。其中,所有的恶棍都由同一位歌者扮演。
(16) 尼姬:这个飞得极快的女神决定胜负,抑或仅仅对胜出者予以奖励?说法不一。然而,无论怎样,对于跑鞋来说,这是个好名字。
(17) 乔治·费多创作过许多滑稽戏。这些戏剧都以精确的出入场时机为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