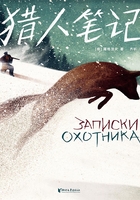
我的邻居拉季洛夫
秋天里,山鹬经常栖息在古老的椴树园中。在我们奥廖尔省,这样的园子可有不少。我们的祖辈在选择栖息地时,总要辟出一块作为果园,铺上小径,小径旁则必然密密种满椴树。五十年或者是七十年之后,这类“贵族之巢”渐渐都消失了,其间的房屋早已朽坏或者被拆了卖掉,石质的各类配套建筑成了废墟;苹果树枯死了,被砍了当柴烧,栅栏和篱笆也都被消灭了。只有椴树,依旧苍劲挺拔。如今,它们立在曾被耕种过的田野间,向我们这轻浮的一代讲述“祖父辈的故事”。这有年头的椴树可真是不得了的树木……就连手握砍斧的俄罗斯汉子也对它颇为怜惜。椴树的叶子细小,枝丫却粗壮舒展,往往伸向四面八方,形成永恒的树荫。
有一天,跟叶尔莫莱一起在野外捕山鹑的时候,我发现一处废弃的园子,便走上前去。刚靠近园子边,便有一只山鹬从树丛里“笃”地蹦了出来。我立即举枪射击。就在那一刹那,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传来一阵叫声。一个年轻女子惊恐的脸从树丛后闪出来,瞬间消失了。叶尔莫莱跑到我跟前说:“您咋在这儿开枪呢?这里住着个地主呢。”
还没等我回答,我的猎犬也还没来得及带着一脸傲娇郑重地把打中的鸟儿叼过来,就听见急切的脚步声传来。一个留小胡子的高个子从林子里钻了出来,一脸不满地站到了我面前。我好是一番道歉,报了自己的姓名,还要把在他府地上打的鸟儿给他。
“好吧,”他微笑道,“我收下这只鸟儿。不过,条件是您得在我这儿吃顿便饭。”
说实话吧,我并不大乐意接受这个提议,但又没有办法拒绝。
“我是这儿的地主、您的邻居拉季洛夫。您大概听说过我吧?”我的新相识接着说道,“今儿是星期天,我家的午饭应该还挺像样的,否则我也就不邀请您了。”
我说了几句例行的客套话,便跟着他往府里走去。一条不久前刚清理过的小道很快把我们带出了椴树林,我们进了菜园。在一株株老苹果树和长得极为繁盛的醋栗之间,蹲着一棵棵鲜绿的圆白菜;葎草弯曲盘绕在高高的竿子上;菜畦上挂满了深褐色的树藤,被豌豆苗所缠绕;平扁的大南瓜大咧咧地四散躺在地里;黄瓜从棱角分明、落满灰尘的叶子下面探出来;荨麻沿着篱笆长得老高;有那么几处地方集中长着忍冬、接骨花和野蔷薇,貌似是以前的“花坛”。一个充满泛红的浓稠水体的鱼池边上,开了一口井,井边围着几摊水洼。鸭子们在水洼里扑腾着;一只狗儿正皱着眉、浑身用力地在一块空地上啃骨头;花斑奶牛懒洋洋嚼着草,不时用尾巴扫扫瘦骨嶙峋的背。小道向一边拐去。茂密的爆竹柳和白桦的掩映之下,是一座灰色的、带歪斜前廊的木顶老屋。拉季洛夫停了下来。
“其实呢,”他憨厚而直爽地看着我的脸道,“我改主意了。您可能压根儿不想上我家来。这样的话……”
我没等他说完,便坚持说,正相反,我很乐意来他家吃顿午饭。
“那么,请便吧。”
我们进了屋子。一个身着蓝色厚呢长褂的年轻仆从在前廊迎接了我们。拉季洛夫立即请他给叶尔莫莱端来伏特加,我的猎人伙伴对着大方的拉季洛夫的背影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们经过挂满花花绿绿各色图画、蒙着纱窗的前厅,进了一间小屋。这是拉季洛夫的书房。我脱下猎装,把猎枪靠在墙角。一位身着长襟衫的仆从赶忙替我掸掉身上的灰尘。
“那么,现在我们去客厅吧,”拉季洛夫友善地说,“我把您介绍给我母亲。”
我跟了过去。客厅里,一张中等大小的沙发上,坐着一位身形娇小的老太太。她穿着咖啡色长裙,戴着白色居家便帽,脸瘦削而慈祥,目光温存而忧伤。
“妈,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邻居×××。”
老太太起身给我行了个礼,干瘦的手里一直攥着一只口袋状的毛线手包。
“您来我们这儿很久了吗?”她眨了眨眼,轻声细语地问道。
“不久。”
“在这儿打算待多久?”
“估计待到冬天吧。”
老太太沉默了。
“这位嘛,则是,”拉季洛夫突然想起来,指着一个进客厅时我并未发现的瘦高的人道,“这位是费奥多尔·米赫伊奇……我说,费佳注13,把你的本事亮给客人瞧瞧。你怎么躲到角落里去了?”
费奥多尔·米赫伊奇立刻从椅子上站起身,从床边拿来一把破破烂烂的小提琴,握着琴弓中央,而不是底部,把琴抵在胸前,闭上眼,载歌载舞起来,把那琴弦拉得吱吱响。他看上去有七十来岁了,长长的粗布外套耷拉在他瘦削嶙峋的肩上。他跳着,一会儿大胆地摆来摆去,一会儿又仿佛要停住,仰着不大的谢顶的头,伸着布满青筋的脖子,在原地跺着;一会儿又明显困难地弯膝蹦着。他那没了牙的嘴里发出嘶哑的声音。拉季洛夫大约从我的表情看出,费佳的“本领”并没给我带来多大享受。
“好吧,老兄,够啦,”他说道,“你可以去犒赏自个儿了。”
费奥多尔·米赫伊奇立刻把提琴收到了窗后,对着我、老太太和拉季洛夫都分别鞠了躬,便走了出去。
“他也曾经是个地主,”我的新朋友说道,“很富有,后来破产了,现在住在我这儿……年轻的时候可是全省闻名的浪荡汉子,先后拐跑过两个人的老婆。他养过一群歌手,自己也是能歌善舞……您要不要来点伏特加?饭菜都已上桌了。”
我在园子里见过一眼的那位年轻女子走了进来。
“这是奥尔佳!”拉季洛夫略微转过头,介绍说,“请您多关照……我们去用餐吧。”
我们进了餐厅,坐了下来。我们从客厅走过来的时候,遇见已经“犒赏”过自己的费奥多尔·米赫伊奇,他眼珠子发亮,鼻头通红,正在哼唱《胜利的欢雷,请奏响!》。大家给他在角落里单独摆了一小桌,没铺桌布。可怜的老头吃相不太文明,因此大家用餐时总是离他远着点儿。他在胸前画了十字,叹了口气,像鲨鱼一般吃了起来。午餐的确不错,作为周日的正餐,还配有鲜嫩的果冻和西班牙式甜饼。
饭桌上,曾经当过十年步兵,还征战到过土耳其的拉季洛夫讲起了他的经历。我仔细听着他的讲述,顺便偷偷观察着奥尔佳。她不算多美,不过她那坚定而安详的表情、宽阔雪白的额头、浓密的头发,特别是不大,却极聪慧、明亮、生动的眼睛会让任何一个像我一样观察着她的人感到惊喜。她仿佛一字一句听着拉季洛夫的讲述,满脸热忱的关注。按年岁来算,拉季洛夫可以当她的父亲了,对她却以“你”相称。不过,我立马察觉,她不是他的女儿。聊天中,拉季洛夫提到了他已故的妻子。“她姐姐,”拉季洛夫指着奥尔佳补充道。她即刻红了脸,垂下双眼。拉季洛夫停了停,转了话题。老太太整个用餐期间没有发一言,几乎没吃什么,也没特别招呼我。她的轮廓带着某种胆怯无望的期待,某种年老体衰的忧伤,足以令各位读者揪心。
饭快吃完的时候,费奥多尔·米赫伊奇原本要“赞颂”主客的。拉季洛夫看了我一眼,叫他不要出声。老头儿用手抚了抚嘴,眨眨眼,鞠了躬,坐到了椅子最边上。午饭后,我和拉季洛夫进了他的书房。
在那些一直被一种想法或者爱好所占据的人身上,往往有些共同的地方,在待人接物上或者其他方面。不过,他们的品质、能力、社会地位和教养,还是不尽相同的。越是观察拉季洛夫,我便越确信,他就是此类人。讲起自己的产业、收成、割草、战争、县里的流言蜚语和即将到来的选举,他表情随意,甚至带着参与感,不过,时不时地叹气,坐进椅子里,像一个被繁重劳作所折磨的人一般,用手抚着脸。他那善良温软的心被一种情感所浸透。
我感到震惊,因为我无法从他身上察觉到对食物、美酒、打猎、库尔斯克夜莺、患了癫痫病的鸽子、俄罗斯文学、溜蹄马、匈牙利人、打牌或桌球、舞会、游览省里的城市或其他大都市、造纸厂、炼糖厂、粉刷得五颜六色的亭子、茶点、骄纵的拉边套的马儿,对胖得腰带系到胳肢窝下的车夫,那些尽心尽责的、拉车时候脖子每动一下眼睛便要往外翻斜的车夫等等的任何兴趣。
“这算哪门子地主呀!”我暗自想。同时,他又完全不是一个阴沉而对生活不满的人。正相反,他浑身上下散发着盲目的热情与诚恳,乐意与任何一个遇到的人接近。不过,结识之后,您也会感觉到,真正与他接近是不可能的,并非因为他不需要任何人,而是他的整个生活暂时变得内敛了。观察着拉季洛夫,我感觉不到他现在或是什么时候曾经快乐过。他不算是美男子,但在他的目光、微笑,他的整个存在当中,隐藏着某种极为吸引人的东西,—藏得深深的,似乎叫人特别想更了解、喜欢此人。当然,他也会偶尔流露出地主和草原居民的习气,但仍旧是个极可爱的人。
我们正想聊聊县里新的头头们,忽然传来奥尔佳的声音:“茶点备好了。”我们走进客厅。费奥多尔·米赫伊奇像之前一样坐在窗与门之间的角落里,缩着脚。拉季洛夫的母亲织着长袜。秋天的清新与苹果的清香从窗外漫进来。奥尔佳殷勤地倒上茶,我更加仔细地看了看她。像其他县城女子一样,她话很少。不同的是,她并没有非要说些聪明话的愿望,并不给人空洞无力的印象。她不叹息,就好像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不翻眼睛,不勉强无谓地微笑。她看人直率而无意,就像一个经历过大喜大忧的人一般。她的步伐动作坚毅自由。我非常喜欢她。
我和拉季洛夫又聊了开来。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说到那句名言的了,就是说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那些微不足道的事。
“是呀,”拉季洛夫说道,“这点我切身感受到了。您知道,我结过婚。婚姻维持并不久……三年。我妻子生产时死去了。我当时想,我也活不下去了。我难过极了,彻底垮了,却哭不出来,只是着了魔一般踱来踱去。家人给妻子换上衣服,放在了桌上,就在这间屋子里。神父和辅祭们来了,开始祷告、点香炉。我行着叩地大礼,却还是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我的心和脑仿佛都僵住了,整个人也沉重起来。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您信不,夜里我居然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来到妻子旁边。那时是夏天。阳光把她从头到脚整个照得透亮。突然,我发现……(拉季洛夫不禁哆嗦了一下。)您猜怎么着,她有只眼睛没有完全闭上,苍蝇正在上面爬着……我瘫倒下去,就像是最终反应过来一样,嚎啕大哭,怎么也停不住……”
拉季洛夫沉默了。我看看他,又看看奥尔佳……一辈子我也忘不掉她的脸。老太太将长袜放到膝上,从手袋里取出绢子,悄悄擦着眼泪。费奥多尔·米赫伊奇起身抓过小提琴,扯着嘶哑粗野的喉咙唱了起来。他大概是想宽慰我们,可他一开唱,我们便打了个哆嗦,拉季洛夫赶紧叫他停下。
“不过,”拉季洛夫继续说道,“这都已经过去了,无法再挽回。最终……一切都是为了此生能更好吧。这好像是伏尔泰说的。”他迅速补充道。
“是的,”我说,“当然!何况任何的不幸都是能够挺过来的。没有走不出的困境。”
“您也这么认为?”拉季洛夫道,“您说的估计没错。我在土耳其时曾经伤得很重,半死地躺在医院里,伤口感染,高烧不退。医院条件可真差。当然,打仗嘛,这就不错了!还不断有病人被送进来。把他们往哪儿安顿呢?医生跑前跑后也腾不出地方。他走到我跟前,问助理:‘还活着吗?’那家伙回道:‘早上还活着。’医生弯下腰,听见我还在呼吸,忍住不叫道:‘这可真是蠢货!明明是要死了,肯定会死的,却死撑着,不肯给别人腾地方。’‘你呀,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还真是不咋地……’我暗自想。这不,您看,我活了下来,还一直活到了今天。想必您说得对。”
“无论怎样我都没说错,”我答道,“就算您死去了,您还是从困境中走出来了呀。”
“当然,当然,”他说道,忽然用手重重捶了一下桌子,“必须要有决心……困境究竟算什么?为什么要磨磨蹭蹭呢……”
奥尔佳迅速站起身,走到园子里去了。
“费佳,给咱跳上一段吧!”拉季洛夫叫道。费佳起身,在屋里迈开那特别的、雄赳赳的舞步,就像装扮成母羊、牵着熊的杂耍小厮一般唱道:“就在咱家的门边哟……”注14
门外传来赛马车的响声,不一会儿,一个高个子、宽肩、粗壮结实的老头进屋来。这便是独院地主奥夫西亚尼科夫。奥夫西亚尼科夫是如此独特的一个人物,读者允许的话,我们将另辟章节来讲讲他。现在呢,我再补充告诉各位,第二天,我和叶尔莫莱天一亮便去打猎了,打完猎就回了家。一周之后,我又顺路去看望拉季洛夫。他和奥尔佳都不在。两周后,我才知道,他突然抛下老母消失了,跟妻妹去了什么地方。全省因此沸腾。大家都在聊着此事。至此,我才明白拉季洛夫讲述时,奥尔佳的表情。那不仅仅是痛苦,更是嫉妒。
离开村子时,我去拜访了拉季洛夫的老母。她正在客厅与费奥多尔·米赫伊奇玩“傻瓜”扑克。
“您有儿子的消息吗?”我问她。
老太太哭了起来。我便没有再问有关拉季洛夫的任何事。
注13 费奥多尔的指小表爱形式。
注14 俄罗斯十八世纪起开始流行的一种杂耍形式,年轻的杂耍艺人扮作母羊,领着被驯化的熊又唱又跳。上至皇家,下至民间,一度风行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