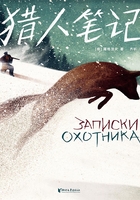
小县医生
某个秋日,我从很远的原野归来,途中着凉病倒了。幸运的是,我是到了一个县城、住进宾馆后才发起烧来的。于是,我派人去叫了医生。半小时后,医生来了,个子不高,是位黑发的瘦子。他给我开了普通的退烧药,嘱咐我贴上退热贴。我付了他五卢布。他一边把钱熟练地塞进袖口,一边望着别处干咳着。本来他已经要走了,结果不知怎么就留下聊开来了。发热使我萎靡。不过,想到难以入眠的漫漫长夜,我倒是挺愿意跟个善良的人聊聊的。我叫人上了茶点。医生便打开了话匣子。他虽然算不上什么人物,但挺聪明的,说话也非常有趣。
人在这世上呀,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跟有些走得很近、关系亲密的人吧,却往往说不了什么掏心窝的事;有的人呢,你刚认识,就像跟神父忏悔一般把什么都跟他倒出来了。不知道是什么叫这位新朋友对我如此信任,总之他“一上来”就跟我讲了一个极有趣的经历。我现在就把这件事跟各位耐心的读者来说说。我尽量模仿他的口气。
“您认不认识,”他的声音微微颤抖着(抽别列佐夫烟太多的缘故),“您不认识我县法官梅洛夫,巴维尔·卢基奇吗?……不认识……不要紧。(他咳了一下,用手拭了拭眼睛。)我不想跟您撒谎,不过呢,事情是这样的。大斋戒注12期间,天气正开始暖和的时候,我有次跟法官一起打朴列费兰斯牌。法官人不错,很爱打牌。忽然(医生特别喜欢用“忽然”一词),有人跟我说:‘你们那儿有人找你。’我回道:‘找我啥事?’说是有人送了张纸条给我,应该是病人写的……好吧!您理解的,这是我的饭碗哪……
“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女地主,寡妇,写信给我说,女儿快不行了,请我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赶紧去瞧瞧。马车也给我派来了。这倒是没啥……不过,她住在二十俄里开外的地方,大半夜的,路也不好走,简直了!她家境并不咋地,能给两卢布已经不错了,兴许就给点麻布或者小东西搪塞过去了。不过,行医是天职呀!病人快不行了。我把手里的牌转给每次必来参加牌局的卡里奥平,匆匆赶回家去了。
“一架小破车停在我家门口,拉车的是干农活的马,耷拉着大肚皮,皮毛粗糙得像毡子。车夫呢,就像是对我致敬一般,连个帽子也没有戴。我暗自想,兄弟,看出来咯,你家主子日子不宽裕……您看,您觉得好笑。我跟您说吧,我们这些穷人哪,啥都看得明白着呢。要是车夫威武地坐着,帽子戴得好好的,还时不时从胡须下面露出点嘲笑,那就可以大胆地要双倍出诊费啦!这次呀,可没这好事。不过,我还是想,得尽当医生的义务。我抓起必备的药品,便出发了。这一路可把我折腾坏啦:水洼水坑、积雪泥泞,半路还遇上个决了堤的小水坝,真是够呛!不过,总算到了地方。
“那家的房子不大,屋顶铺着秸秆。窗边亮着灯,应该是在等我。我进了屋。迎面走来一个颇有仪态的老太太,戴着便帽。
“‘您快救救她吧,人快不行啦。’她说。
“我问:‘请别着急……病人在哪儿?’
“‘请往这边来。’
“我一看,房间干干净净,屋角里挂着油灯,床上躺着一位二十岁上下的女子,已经昏迷。她浑身冒火,呼吸困难,发着高烧。旁边还有两个姑娘,应该是她姐妹,吓坏了,泪流满面,说道:
“‘她昨天还好好的,吃饭也很香,今天一早起来说头疼,到了晚上就发展成这个样子了……’
“我说:‘请别着急,这是我医生的职责。’然后便开始诊断了。我给她放了血,叫人贴上了退热贴,开了些糖浆。我看着,不禁想到,天哪,还真没见过这么俊俏的脸儿……一句话,是个大美人儿!我真是动了怜悯之心。她的轮廓可真美,眼睛也漂亮……终于,她开始退烧了,出了一身汗,仿佛清醒过来,看了看四周,微笑了一眼,用手抚了抚脸……姐妹们弯腰问道:
“‘你怎么样?’
“‘还可以。’她说完便转过头去。我一看,是睡过去了。我吩咐不要打扰病人。大家便都踮着脚尖出了房间,只有贴身丫头留了下来。客厅里,主人已经架起茶炉,还上了一瓶牙买加酒。干我们这行没了这个可不行。主人招待我用了茶点,请我留下过夜……我同意了。这大半夜的还能往哪儿去!老太太还是有些担心。
“‘您别愁啦,’我说,‘姑娘没事,您自己也歇歇吧,这都半夜一点多了。’
“‘要是有啥情况,你可得叫醒我哟!’
“‘肯定叫醒您。’
“老太太回自己房间了,姑娘们也都回房了。他们为我在客厅里铺好了床铺。我躺下身,却怎么也睡不着,真是奇了怪了!明明折腾到大半夜。这女病号总是在我脑海里盘旋。我没忍住,起了身,决定去瞧瞧病人怎么样了。她的卧房就在客厅隔壁。我轻轻地推开门,心怦怦跳。贴身丫头睡意正酣,见鬼了,还张着嘴打鼾呢。病人脸对着我躺着,双手张开。可怜见的!我走上前去……她忽然睁开眼睛盯住我:
“‘这是谁?谁?’
“我一阵发窘,道:‘小姐,您别怕,是我,医生。我来看看您咋样了。’
“‘您是医生?’
“‘医生……您母亲把我从城里叫来的。我们给您放了血,小姐,您该好好歇息一下啦。再过个两天,老天保佑,我们就叫您好起来。’
“‘啊,医生呀,请别叫我死去呀,我求求您啦。’
“‘您这是胡说什么哪!’我暗自想,她不会又发起烧来了吧。摸了摸脉,可不!她看了看我,突然抓起我的手说:
“‘我跟您说说,为啥我不愿死。我跟您解释……现在就我们俩人,您可千万别告诉别人。您听着……’我弯下腰去。她把嘴唇贴在我的耳朵上,头发拂过我的脸颊,低声讲起来。我得承认,我一阵眩晕。我听不懂她要讲些啥……满嘴胡话……她急促地讲啊讲,就好像说的不是俄语。讲完后,抽搐了一下,头歪倒在枕边,用手指指着我威胁道:
“‘您可记住了,医生,对谁都不能说……’我好歹把她安抚住了,喂她喝了水,叫醒了女仆,便走出房去。”
说到此,医生狠狠地吸了吸鼻咽,待了一小会儿。
“不过,”他继续道,“让人没想到,第二天病人并没有好转。我想了又想,突然决定留下。其实我还有别的病人呢……这种情况是不能忽视的,会影响医生的声誉。首先,病人的情况的确不妙。其次,得承认,我对她产生了好感。这一家子人都挺叫人喜欢的。虽然她们过得并不富裕,但教养却是少见的……他们家的男主人是个学者,擅长做学问的,死的时候没留下什么财产。不过,孩子们他都调教得很好,还留下不少书籍。不知是为此,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我对这女病人照料有加。这家人也把我当作亲人看待……与此同时,交通确实越来越成问题了,几乎完全中断了,以至于进城买药都成了大麻烦。病人却仍未见好转……这么一天又一天……一直这么着……(医生顿了顿。)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了……(他又吸了口鼻烟,出了口气,喝了点茶。)我就老实跟您说了吧,我这女病人哪,像是喜欢上我了还是怎么着……不过,其实吧,这也……(医生红了脸,垂下头去。)”
“不对,”他继续激动地说道,“什么喜欢上!我也得有点自知之明了。那姑娘受过良好教育,读过不少书,聪明伶俐。我呢,连拉丁文都几乎全部忘光了。我这身材(医生微笑着自我打量了一番)也没啥出众的。但老天也没叫我成个傻瓜,基本常识我是有的,也有自己的脑瓜。比如,我很明白,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她叫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对我产生的不是爱意,而是友情或者尊敬之类的。尽管她自己可能也没大明白自己的感受。您想想,她病成那样……不过,”医生补充道,之前的那一大通话他几乎是一口气说完的,像是着了魔一般,“我好像是胡扯了一通……估计您啥也没听明白……我现在给您清楚地讲讲。”
他把茶喝完,平静地继续讲道:
“是这样,病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您不是医务工作者,所以,先生哪,您也就没法明白,医生心里是个啥滋味,当他开始猜到自己已无力回天时。自信心受到打击!人一下子就胆小得难以形容了。你突然觉得,自己学的东西全部忘记了,病人对你也不再信任。人们都觉得你不再称职,不再对你老老实实报告病情,另眼瞧你,背后嚼舌头……真是糟透了!你依旧想,应该是有能治好这病的良药呀!只要能找到就行!你试一种药,是不是这个?不是!都不给时间让药效发挥……一会儿试这个,一会儿试那个。有时候拿起药典想,就是这个了吧,就这么盲目地以为,找到了良药……病人却正死去,别的哪个医生估计本来能把他治好的。你嘟囔着,得会诊了,我没法负责了。可会诊时你简直就是个傻瓜!慢慢地,你就忍受下来了。人死了,并非你的过失,你是按规矩给他治的。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痛苦:你看到病人对你盲目的信任,而自己明白,其实没法帮助他们。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一家对我所报以的正是这样一种信任,仿佛忘记了女儿严重的病情。我呢,也是对她们百般安慰,告诉她们没啥事,而自己的心却沉到了谷底。使情况变得更糟糕的便是几乎中断了的交通,车夫进城买药往往要耗费一天的时间。我也守在女病人的房间里不出来,给她讲讲笑话,陪她打打牌,整夜整夜陪着。老太太眼含热泪感谢我,而我想,我不值得你感谢。我就跟您彻底坦白了吧,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遮掩的,—我爱上了这女病人。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对我也亲近起来,有时候除了我谁也不让进屋。跟我聊天时,她问好些问题,我在哪儿上的学,过得怎么样,常去看望的亲人有哪些。我明白,她该好好休息,却没法严格禁止她说话。我时不时地拷问自个儿:‘你个强盗!你究竟在做什么?……’
“有时候,她会忽然抓起我的手握着,久久望着我,然后转过身去叹气:‘您可真善良!’她的手滚烫,双眼又大又深。‘是呀,’她说,‘您可真是善良,跟我们的邻居可不一样……您跟他们不是一类,不是……我怎么才认识您呢!’
“‘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安静一下吧,’我说道,‘我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赢得了您的信任……您千万不要激动,求您了,不要激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您会好起来的。’”
“其实吧,我跟您说,”医生向前弓着身子,扬起眉毛说道,“她们家跟邻居其实并不怎么打交道。出身卑微的吧,配不上她们。那些富贵的呢,她们又清高不肯攀附。我不是跟您说吗,这是非常有教养的一家子。跟她们在一起我感到特别荣幸。女病人只肯叫我喂药给她吃,可怜见的,我帮她支起身子,她吃了药就盯着我看……我这心里呀,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她的病情越来越重了。就快死了,我想。她老母亲和姐妹就这么巴巴地看着我,我恨不得自己进棺材去……对我的信任也渐渐没了。
“‘您看怎么样了?’
“‘没事儿,放心!’简直疯了吗!放哪门子心?
“这不,有天夜里,我还是一个人守在病人床边。贴身丫头也坐在一旁,鼾声雷动……也没法说这丫头什么不是,她也是累坏了。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一夜没睡好,高烧不退。闹腾到了半夜,终于像是睡着了,反正是不闹腾了,静静躺在那里。角落里的圣像前,油灯在幽幽燃着。我坐得迟钝了,也打起瞌睡来。突然,仿佛谁从侧面推了我一下,我一转身……我的老天爷!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睁着大眼望着我,嘴大张,双颊火烫。
“‘您怎么啦?’
“‘医生,我要死了,对吧?’
“‘胡扯些啥!’
“‘不,医生,请别再说我会活下去……别再说了……您要知道……请不要再对我隐瞒了,’她就这么急促地呼吸着,‘我是要死了……我全都跟您说,全说!’
“‘行行好吧,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
“‘我其实没有睡着,我一直看着您……求您了……我信任您,您是个好人,诚实的人,您得拿世上最珍视的东西跟我保证,您要说实话!这对我太重要了……医生,求您了!我病得很危险?’
“‘我能跟您说什么呢,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饶了我吧!’
“‘求求您了!’
“‘我不能隐瞒,是的,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的确病得很重,但上帝是仁慈的……’
“‘我要死了,要死了……’她仿佛高兴起来,满脸欢快,把我吓坏了。
“‘您不要害怕,别怕。我不怕死的。’她突然用手肘撑着坐起身来,‘现在……现在我可以跟您承认了,我衷心感激您。您是个大好人。我爱您……’
“我像是看着一个神志不清的人,感到恐惧……
“‘您听到了没,我爱您……’
“‘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配不上您的爱意!’
“‘不,不,您没明白……您不明白……’突然,她伸出手,将我的头抱住,吻了吻……我差点大叫起来……我跪在床边,把头埋进枕头。她默然痛哭着,我感觉得到她的手指在我的头发里颤抖着游走。我开始宽慰她……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您会把丫头吵醒的,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感激您……请相信我,静一静吧。’
“‘行了,够了,’她说道,‘上帝与大家同在,管他谁被吵醒、谁进屋来呢—我反正要死了……你又怕什么呢,有什么可怕的?抬起头……还是说,您不爱我……我弄错了……若是这样,请原谅我吧。’
“‘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说些什么哪?……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
“她直望着我的眼睛,将手松开。
“‘那你抱抱我吧……’
“跟您坦白吧,我那夜差点就疯了。我感到,我这女病人就快把自己给毁了,她根本失去了理智。我也明白,要是她不认为自己就要死了,也不会想到我吧。您想呀,二十五岁就死去是多么可怕呀!还没来得及爱过谁!她正是被这想法折磨着,才在绝望中抓到了我,您现在明白了吧?她就是对我不放手。
“‘您饶了我吧,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也放过自己吧。’
“‘有什么好可怜的呢,’她说,‘我这都快要死了……’这句话她一直重复着。‘如果我要是能活下去,重新当个体面的小姐,那我一定会感到羞愧的……可现在又能怎样?’
“‘谁说过您要死了呢?’
“‘够啦!你骗不了我的。你看看自个儿,你不会骗人。’
“‘您会活下去的,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会把您治好的。到时候我们向您母亲祈求祝福……我们就结合在一起,我们会幸福的。’
“‘不,您不是都说了吗,我会死的,你都承诺了……你说的……’我心里真是五味杂陈,难受得要命。您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事呀。似乎没啥,其实叫人很痛苦。
“她突然想起问我的名字,不是姓,而是名字。不巧的是,我名叫特里丰。对,对,我叫特里丰·伊万内奇。家里人都叫我医生。没办法呀,我答:‘小姐,我叫特里丰。’她眯起眼睛,摇了摇头,说了几句法语。叫人不快的是,然后还笑了起来。我就这样在她跟前坐了一夜。
“凌晨,当我从她屋里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失魂落魄的。白天的时候,吃完茶点,我又去屋里探望她了。上帝呀!简直没法认出她来,面如死灰。我跟您保证,我都没法明白,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我的女病人烧了三天三夜……都是些什么夜晚呀!她跟我说的那些话……最后一夜,当我再次坐在她身边时,我不断求着上帝,快把她收去了吧,顺便把我也带去……
“突然,她的老母亲走了进来。前一天我已经通知她了,没什么希望了,该叫个神父来了。女病人一看见母亲便说:‘来得正好……你看我们,我们深爱对方,已经都许诺好了。’
“‘她这说的是啥,医生,是啥?’我脸色铁青。
“‘发烧说胡话呢。’我说。
“她继续道:‘够了,好了!你刚还跟我说的别的呢,还从我这里接了婚戒……装什么装呢?我老母亲可善良了,她会原谅我们的。她知道我要死了,我不会说谎,快把你的手给我……’我跳起来冲出屋去。老太太自然是猜到了。
“我不想再继续打扰您了,自己再回想这些也是种折磨。第二天,我的女病人就去世了。愿她在天之灵安息(医生快语补了这句,叹了口气)!临死前,她叫亲人们都走出去,只留下我一个人。
“‘请您原谅我吧,’她说,‘我应该是非常对不住您了……这病……请相信我,我爱您胜过任何人……请您不要忘记我……请保管好我的戒指……’”
医生说完转过身去。我赶紧抓住他的手。
“唉!”他说,“让我们聊点别的吧,要不咱们打会儿牌?我们这些医生一般可没精力玩儿这个呢,我们想的就是怎么不让孩子吵闹、不叫妻子叫骂。不过呢,其实我也已经结婚啦……我娶了个商人的女儿,得了她家七千卢布嫁妆。她叫阿库琳娜,跟特里丰正相配。这婆娘脾气不好,不过呢,倒是爱睡觉……打一轮朴列费兰斯牌如何?”
我们打起了一轮一戈比的朴列费兰斯。特里丰·伊万内奇从我这儿赢了两个半卢布,离开得挺晚,对自己赢的钱颇为满意。
注12 东正教一年之中最大的斋戒,于每年复活节前结束,持续时间长达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