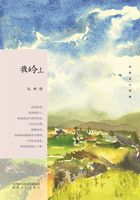
第10章 故乡的路
盛夏,与妻回县城看父亲。已在半路上,打父亲手机,父亲说他在老家。便邀了妹子、妹夫,直奔老家。交通方便了,每年总要回老家两三次。车驶入了一条新路,我问妹夫:“咱这是走三官庙吗?”妹夫说:“不是,仍走环山路。”过去走环山路,要从老312国道绕上去,现在新开通了一条路,宽阔笔直,与环山路贯通。晴空上飘几朵白云,南山逼真而逼近,环山路穿行在南山与灞河之间,车如同在一幅画中畅行,眼睛因为享受而喜出望外。
故乡在横岭上,沟、坡、梁构成了地貌,中华民国时代有一条土路翻岭越沟,通向许庙街道,土路叫官道,可行马车。故乡人要进县上省(西安市),如果坐马车,许庙是绕不过去的。上世纪70年代,官道改道,仿佛一个圆规取了直径的两点,故乡与312国道骤然缩短,前程是入口的一个接点。仍为土路,铺了些沙石,可容汽车通过。沙石很快被雨水冲刷净尽,遇雨路便泥泞,不能行车,行人赤脚比穿雨靴还要轻便。1984年暑假,我的一伙大学同学去我故乡,一路烟雨,一路泥水,都光了脚,说舒服。晴日路面干结,留有人脚窝、牛蹄窝、羊蹄窝,夹杂着独木轮、架子车、手扶拖拉机的车轱辘印辙,不是洼坑,就是疙瘩,行车其上,一路颠簸。道路失修,沟地滑坡,外地的司机驾车经过,多半提心吊胆。截至上世纪末,故乡人对过往车辆多半喜欢高看两眼,孩子还尾追到梁上,望着车绝尘而远。省城在一百里外,去一次比进戏园子看戏还难,去的必是能行人,故乡人当然也高看。我上大学后,就被故乡人高看:“大学生呀!”只这人前背后的一句半截话,足令我挺起胸膛,走路有了底气。我回一次故乡,故乡人见了都稀罕:“还能住惯么?”被高看的人可以改乡音,可以吃不惯故乡的饭,睡不惯故乡的炕。每次车进村,一村人都知道我回家了。一根烟,就换来一声啧啧:“你把世事弄成了!”
2004年秋,一伙朋友去我的故乡,妹妹告诉了我一条新路,说是好走,直通故乡。我牢记了路线,便带着朋友们上路了。车从县城附近的312国道边的岔路口向北踅上一条公路,我不知道叫蓝金路,却知道这条路通金山,过三官庙。柏油路,多弯而奔高,盘旋而平展。费秉勋开玩笑:“孔明,你不会认不得故乡路吧?”我笑得一脸灿烂:“哈哈,费老师,你放心,回故乡嘛,怎么可能认不得路?”按照妹妹叮嘱的路线,遇见一个丁字口,我发话:“右拐!”车一溜烟儿飞奔,越往前越生疏,故乡的路有这么宽吗?嘀咕着让车停下,三个乡党正在路边施工,我问杏树凹,其中一个乡党说:“你不会是强民他兄弟吧?”强民是我大哥。我赶快拱手,那人嬉笑,揶揄道:“真是阔别了,连你村子的路都不认得了!”一个“阔”字咬得极重,却指说:“退回去,看见一个水塔再拐弯,沙路,只管走,就到了。”一车的人都在笑我,说费老师算定了我要出此洋相。
2005年初夏,又一伙朋友去我的故乡,其中有贾平凹、京夫、晓雷等。我领着几辆车,决定重温上一次回故乡的路。车上,贾老师听说我上一次回故乡闹了笑话,说:“孔明这一次还要走弯路!”我笑得比上次更灿烂:“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我是真认为不可能,因为我胸有成竹呀!我记住了那个水塔,还能走错吗?看见水塔,我让司机拐弯,贾老师说:“你看好,别犯低级错误呀!”我大笑:“勇往直前,绝对正确!”车奔驰,闪过一个村,又进了一个村,我是真不自信了:“不对呀!不可能呀!怎么会这样了呢?”车只能退回去,问一过路行者,说是再过一个村子就是杏树凹。大家起哄嘲笑我。去年一条路,今年又开出了一条新路,我是犯经验主义错误了。
2005年冬天,我的母亲长行,一些朋友闻讯前往我的故乡,多半人走了弯路。大家一见面就怪我,我也“委屈”:“只能怪通向我故乡的路太多了。”我生怕朋友们走冤枉路,便将故乡的路线图形成具体的文字,发到朋友们的手机里。一些朋友顺利到达了,一些朋友不断地打手机问路,结果还是绕了一大圈。我的同事开了三辆车,一路走,一路问,结果问到了厚子镇,再前行就是渭南地界了。路人告诉他们,走厚三路就到了。所谓厚三路,就是厚子镇通向三官庙的乡级公路。我第一次走错路,走的就是这条路,只不过反向而已。天下了雪,一面坡上结冰了,他们知难而退了。事后我才知道他们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幸而他们知难而退,否则没有人领路,不知道他们要奔向何方。
2008年冬天,母亲逝世三周年祭,参加纪念活动的朋友仍有走弯路的。其时村村通公路,路路通顺,无论指路多么“正确”,仍有“误入歧途”的。我的一对老朋友夫妇籍贯商洛,老312国道走了不知多少个来回,还知道他们的故乡与我的故乡在前程“分道扬镳”。他们沿着老312国道东行,越走越觉得不对劲,问街上人:“这是前程吗?”答:“这是许庙!”问杏树凹,当地人指了一条捷径,他们事后说好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已经和我握手了,朋友的妻子仍捂着胸口说:“怕死了!怕死了!”他们走的恰是中华民国时代那条“马路”,只不过拓宽了,柏油了。这条路就像一个“U”字,下坡,上坡,上、下都悬乎,怪不得朋友夫妇“怕死了”。
这一次回故乡是2013年8月3日。妹子说:“条条道路通故乡。”这话一点儿也不言过其实。车下了环山路,过公王桥(灞河桥),轻车熟路进去,一辆车挡道,没有避让的意思。我们的车就退出去,前行,看见路口又拐进去,东折北踅地上了宽阔大道,妹夫说是陕沪高速的辅道,可以穿越。虽然绕了些路,视野却豁然开朗,踅上坡后扑眼而来的都是风景,妻子掏出iPad拍照,我则惊讶故乡咋会有这么好看!居高临下,南山,灞河,村庄,高架桥,白云静浮如祥云缭绕,绿地起伏如海涛翻滚,立体大写真,山水好图画,这是老天爷的大手笔嘛!
故乡从古到今都应该这样,如同这天的蓝、云的白、山的俊秀、水的清幽。“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未识,不等于不存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譬如我,对故乡的美,昔年不能说视而不见,也不能说了如指掌。走眼,花眼,不顺眼,看不真切,都是有可能的。有如今日不走此道,不回头,不展望,不驻足观赏,不在这样的季节,身临这样的地方,如何能拥有这样的眼界?高一丈,不一样,是真的!而这一切,都依赖了路。没有路,就只能想象了。但无论怎样想象,眼前这如诗如画的故乡都曾在想象之外。
忽然有点惆怅,却不知道为何。唉,故乡的路要把故乡带向何方?故乡有梦,继续想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