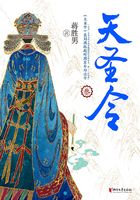
第6章 咸平新政
赵恒登上宫城的城墙,负手遥看远方,已经很久了。
刘娥站在他的身后,看着他的身影一动不动,似在遥望远方的田野,又似在看天边那一抹云彩,却一直一言不发。
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赵恒御驾回京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一次北巡边关,似乎给他带来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不论在朝堂还是在后宫,都不曾表现出来,他只是增添了一个习惯——每日退朝之后就走上城楼,遥望远方许久。
而每当这个时候,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去打扰他。唯有刘娥,可以默默地站在他的身后,却也从不开口打扰。
刚开始,刘娥只觉得心中不安,却又不敢说什么,唯一能做的,也只有在他转身的那一刻让他看到自己站在那里。那时候,赵恒的眼中就会掠过一丝温暖的笑意,却什么话也不会说。
后来渐渐习惯了每天这个时候站在这里,刘娥有时候也会好奇地上前一步,顺着赵恒的眼睛看向远方。看着那远山、那云彩、那遥不可知的天际深处;或者低下头来,看着城墙之下的开封城,看着城墙之下的田野,看着皇城之下的众生;或者转头之间,再看着大内深宫,看着重重宫阙,看着平时已经看惯了的一草一木,竟似换了一种见识。
第一次沉浸于这种思绪奔逸的状态中,她忽然明白了赵恒为什么每天要站在这里看着远方——站在这里,能让心平静,能让烦恼远去,更能让头脑摆脱固定的思绪,打开另一扇门。
到后来,她甚至不再把每日登上城楼当成是陪伴,而是也开始享受这片刻的安宁。
她甚至没有感觉到,赵恒已经转过身来看着她。
刘娥回过神来,看着赵恒嫣然一笑:“官家在看什么?”
赵恒微笑:“在看你。”
刘娥脸微微一红:“我看得出神,竟忘形了!”
赵恒伸出手来,刘娥上前一步,两人并肩站在一起。赵恒轻叹一声:“却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领略到这忘形的感觉。”
刘娥遥望远方,轻叹一声:“官家还在为傅潜之事耿耿于怀?”
皇帝此番北上,颇提升了几名作战勇猛的将领,又用高琼替换了退缩不前的傅潜,军务整顿的动作很大。众臣以为皇帝回京之后必会有一系列动作,可是一个多月过去,对傅潜的处置却还没有下来。
赵恒叹息一声:“是因为傅潜,也不仅仅是因为傅潜。自大宋开国以来,太祖、太宗都有北伐之举。但先帝晚年不喜兵事,不愿与辽国发生争势,因此众将也就顺势罢兵,不愿承担戍边的责任,导致边关屡报辽国犯境。我身为皇帝,这军务终究是要重新整顿的。因此,我就想趁着咱们打了几个胜仗的气势北上巡边,亲临前线去看一看,了解边关大将的才具能力,也看一看咱们同辽国之间的兵力差距。没想到却看到我付以重兵的大将竟会,竟会……”说到这里,赵恒只觉得胸口的气梗在那里下不来。
刘娥忙劝他:“官家,傅潜负恩,并不是官家的错。”
赵恒摇头:“不,并不是。傅潜当日何尝不是忠勇之士?能够得到先帝的信任并不容易,我不相信他能伪装这么多年。可这样的忠勇之士,手握重兵,就会起异心。这不是傅潜一个人心性不行,而是全军的五代之风都太浓厚了。那天有人说了一句话,我当时虽然打断了他,可是……可是这句话,却一直在我的心底。”
刘娥问:“那人说了什么?”
赵恒:“五代殷鉴未远,焉知是不是又有人想做石敬瑭、杜重威——”
刘娥倒吸一口凉气。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给辽国,得辽国之助,灭后唐而建立后晋。石敬瑭死后,其手下大将杜重威挟十万兵马,在后晋与辽国开战时投辽,使得后晋灭亡。虽然石敬瑭、杜重威皆无好下场,可是两军交战,大将挟兵自重,卖主篡立,却是五代以来的传统。兵骄逐将,将骄逐君,大宋立国虽已数十载,军中旧习仍然难改。指出傅潜有做石敬瑭、杜重威之心,就是摆明了说傅潜要谋反。回想这一战中傅潜的种种作为,的确是让人不得不疑心。
赵恒却摇摇头,对刘娥解释道:“可我纵然明白,却不敢说。不能声张,不能议罪,不能让诸将群臣往这边想。这世间的事,想多了,就会生出无限猜忌和针对。所以我不能让任何一个人说傅潜曾怀不轨之心。”
傅潜,只能是腐朽畏战,只能是怯懦迟钝。
他又道:“这次若不是诸将立下大功,令辽兵败退,我甚至还不能拿傅潜怎么样。这几日朝堂之上给傅潜议罪,都说即便不是株连亲族,至少傅潜也必须是死罪。”
刘娥已经听懂了他的意思:“官家的意思是——傅潜不能死?”
赵恒点头:“是,五代之风不可遗留。君王疑臣,便要杀臣;臣子拥兵,便要叛君。人人都有杀心,唯有我,是不可以有杀心的。我下旨,只令傅潜父子流放,甚至过几年有大赦的机会,我还要赦他回来。”
刘娥也懂了。天下不宁,君臣相疑;天下太平,君臣相和。她道:“官家是明知傅潜有异心,也要当他没有异心处置。如此,边将因感念官家仁慈而打消异心,也因官家仁慈而不至于生出怨念。”
这正是赵恒继位之初在诏书上说的“召天地之和气”,因此,赵恒宁可以自己之忍辱、忍怒、忍叛,而感化公卿将相。
赵恒握着刘娥的手,道:“我很感激能遇上你。想当年你同我说起那蜀中逃亡之苦,才令我的眼睛看到了另一边。我生于帝王家,纵平时也看到了书报奏批,却只当是文字上的东西,一直以为天下处于太平盛世,不曾知蜀中流民千里逃亡;只看到这繁华开封,不曾知百里外民生已然凋敝。为君者若不知民,只凭着意气风发,只想着建功立业,这功业纵是七层琉璃宝塔,也是建在沙上的。”
刘娥一惊:“官家这话重了。”
赵恒摇摇头,长叹一声:“你不知道,我只道大宋立国这么多年,处处国泰民安,却不曾想到,京城之地固然是繁华无极,可是自出澶州一路北上,我自车驾中向外看去,只见良田俱成荒野,一连走了好几日都杳无人烟,我这一路上,走得是心中也一片荒凉啊!”
刘娥也不禁惊骇:“官家,怎会如此?澶州离京城不过百里,怎么百里之外就如此荒凉了呢?”
赵恒看向远方,伸手指给刘娥:“千里荒原,无人耕种。这是我的天下,这是大宋的天下啊!我看当年雍熙北伐时的战报,有许多举止失措的地方,本来是不理解的。比如为何要毁太原城而尽迁北地之民,并且多次错失战机,甚至让潘美、曹彬这样的大将陷于危境?如今我去了,才得以明白,原来是这样。”
刘娥有些明白:“官家的意思是,先帝当年毁太原城,就是知道守不住太原城,而雍熙北伐,其实追求的并不是燕云十六州的城池,而是百姓?”
赵恒道:“是。我现在明白为何当日赵普要提先南后北的建议了。因为如果不打下南方,那大宋就与后梁、后周等朝没有什么区别,朝廷手中的力量还不及世家大族。”
刘娥道:“所以朝廷对南方的依赖比表面上看到的更强。”
赵恒依然望向远处,似乎是在看着那澶州以北的千里荒原:“我长于京城,若不是走出去看了看,竟不知一场百年之战,令中原人丁凋敝到了何等地步。我这才知道,当年的雍熙北伐,先帝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若是那一战胜了,那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可是那一战却输了,输到先帝再也无力北伐,含恨而终;输到在我的手中,还要继续偿付这代价。”他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来,“我原先竟是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
刘娥走上前来,轻轻握住赵恒的手,合拢在一起。
入手一片冰凉,她欲要劝解,可是这沉重的话题,如何用一句轻飘飘的话来劝解?过了片刻,她只缓缓地说了一句:“所以,老天爷才将这万里江山放到陛下的手中。”她此刻不再称他为三郎,也不称官家,而称呼他陛下。
赵恒深吸一口气,把那投向万里之外的眼神收回,看着身边的人,抽出一只手来,轻轻拍了拍刘娥合拢的双手,露出了一丝微笑。
刘娥仰首看着赵恒:“原来这些日子以来,三郎每日北望,就是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情?”
赵恒叹了一口气:“我此番北巡,遇上的何止这一件事,桩桩件件,俱是不叫人轻松的,若非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真是成了井底之蛙了。怨不得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这次北巡,胜过在宫中看万本奏疏啊!”
刘娥点头道:“所以三郎这段时日,亦是为此所扰。”
赵恒亦点头道:“文臣们见天下一统,天天叫着收复燕云十六州。可如今我做了皇帝,才明白这何其难也。就连先帝当年雄心勃勃的壮举,如今想来,其更深的目的,还是夺取人口啊。打仗打的是钱粮,如今蜀中之乱方平,江南亦不轻松,国库空虚;且北地千里荒凉,沿线粮草供给不上,便是大忌。因此首要之任,便是要令军民在北地开荒。且此番北巡,似傅潜这等为保全实力临阵不战者尚不止一个,所以我只得重处傅潜以儆效尤;那日我派禁军一起参战,虽说是打退了辽人,可是我亲眼所见,咱们只是恃了人马多,实际上却不及辽人兵强马壮……”
刘娥不解地问:“我记得本朝在册兵卒之数远胜辽人,可是为何却敌不过辽人?依我愚见,朝廷每年招兵太多,可是练兵却太少了。如今国库空虚,倒不如减少兵员,加强训练,岂不一举两得……”
赵恒截断了她:“此事不可行。”
刘娥忙低下头来:“是我失言了,军国大事,原不该由我一后宫妇人擅议。”
赵恒摇头道:“你有所不知,军国大事,并非只算钱粮之账。本朝招募兵马远超前朝,并非完全只考虑行军征战之用。历朝历代,都因天灾人祸,以致田地无收。百姓饥寒交迫,铤而走险,不是落草为寇,便是割据一方,直至亡国灭朝。因此自太祖起,每遇水旱荒灾,便要去灾区招募灾民入伍,朝廷多一兵,则少一暴民。”
刘娥想到当年蜀道逃亡时所见:是啊,那时候一个村子贼过如梳,兵过如篦,若是当时朝廷就能够在蜀中将那些乱民招入军中,或许她和婆婆就不用去逃亡了吧……便道:“怨不得我只见着兵员越来越多用钱粮,原来还有这一层用意。”
赵恒点头:“是啊,所以……对于南官的任用,虽然宰相们大力反对,但我却不能任由北官永远把持中枢。我,需要南官。”
刘娥道:“我明白了。当年唐太宗开科考,说天下才子皆入吾彀中矣,本朝广开科考,恩荫官员,也是这个意思吧。天下,是何人之天下?不能再像五代时期,文臣们迎来送往、武将们坐拥重兵而常起叛心。要约束好武将,也要提拔只效忠官家的文臣。”
这一日,赵恒与刘娥说了许多许多。他要整顿吏治,他要开科举,他要鼓励生产,他要恢复农耕,他要练兵,他要备战,他要在一切都安宁以后重修律法……刘娥听着他的话,想象着未来的样子,也不禁心向往之。
恰是从离乱中走过才能明白,一个想让天下太平的帝王,比一个开疆拓土的帝王更难得。
咸平三年,赵恒亲自巡边归来不久,便雷厉风行,连着下了一系列的诏令,一反登基三年以来基本上依老臣所奏垂拱而治的局面。
二月初,下诏令百官尽言国事无讳,未能直接奏对者亦可封奏疏以闻。亲自下了一系列对边关诸将的升调之令,并令朝中五品以上官员各举荐一名堪任边关守将的武官,同时应杨延朗、杨嗣诸将之请,特诏几名边关大将拥有部分练兵之权;
二月下旬,借赏花之名,召诸将在御苑比赛骑射;
三月,亲御崇政殿面试科举进士;
四月,亲至河北城防阅武举人骑射比试;
五月,大赦天下,死罪减罪一等,流配等均开释,免百姓历年来所欠赋税,促进农桑耕种;同月,亲临城郊玉津园观看刈麦等农事,临金明池检阅水战,临琼林苑举行宴射;
六月,以向敏中为河北、河东宣抚使,促使河北一带恢复农垦;
……
就这样,咸平三年整整一年之内,赵恒不但下了多番旨意推行农桑、加强边境力量、整顿武备、派中枢诸大臣巡察安抚天下,更数次亲自举行射猎、观田,亲试文武举人、接见耆老等。
到了年底,这些举措已经大见成效,朝廷上下面目焕然一新。此间,首相吕端因病重去世,赵恒任命李沆为首相,李沆年老,政事多由赵恒新提升的给事中王旦、枢密直学士冯拯等辅佐。
赵恒在考虑了这一年文武百官尽言国事无讳的奏疏之后,接受王钦若等大臣的奏议,又下了两道特旨:
一、免天下百姓自五代以来历年内所欠朝廷所有租赋。
二、减天下冗官冗吏。
自五代以来,天下战乱纷纷,许多农民逃亡他乡。虽然战事结束,但是多年来田地抛荒,欠下官府租税无力偿交,因此不敢回家。且官府账面上看似有许多租赋可收,可是人已逃亡,实质上也无法再回收,反而令各级官员为了向上级交代,而将许多已不能回收的欠赋转嫁在当地农民头上,逼得更多的农民因交不起田租而逃亡,使得更多田地被抛荒。免去欠租,自可令逃民们安心回归田园,朝廷才能够真正有赋税收入。且逃民归家,不但能令社会稳定,还可以在战事发生时,使军队有供给线。
此项赦免人数多达数十万,赦免钱物也有一千余万,如此减赋,必然要想办法节流,才不至于收不抵支。本朝开国初,太祖为了稳定朝纲,过多任用朝廷官员及边关将士,导致冗官冗兵的存在。既然不能减兵,那便只有减官了。那些冗官数量之大,可以追溯到五代时,不但有后周的旧官吏,也有吴越、南唐、后蜀等各国归降的官员,以及大量开国武官并朝中各官员荫及子孙、家人、部属的荫官等。有司清查数月,最后查出来可减的冗官冗吏达十九万五千余人。
旨意一下,天下震惊。
这减官之举,牵涉极大极广,几乎涵盖天下所有官员。一时间,奔走相告者、倚门哀哭者、牵裳对泣者等等,几乎是搅得天下大乱。
赵恒一边裁官,一边将数千名在这几年的文武科举中脱颖而出的举子一一安置,填补空缺。
皇后郭熙秉承家教及太后李氏的作风素不干政,这不干政的好处自然由她这十几年的顺风顺水验证了。然而此时,她却深深地感觉到了不干政对自己的不利。
她或许并不能完全明白赵恒这一系列改革的前因后果,但是却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微妙之处,这微妙之处或许是赵恒所没有察觉到的,却瞒不过她。
后宫之中只有翠华殿的修仪刘娥,才是这番政治改革中的最大得益者吧。郭熙一步步地分析过来,越发觉得可怕起来:刘娥之兄刘美接替傅潜之职为监军,已经插手军界;刘美的妻舅钱惟演本为降王之后,照理说难进中枢,却借着才子之名,与朝中杨亿、刘筠诸名臣同在修史书之列,不但可以借修史博得名望,更可借此与杨亿等人将来同入中枢;刘娥当年曾暂避张旻府上,如今张旻亦得以出任昭州刺史,为一方大员……
皇帝在提升南方的官员,而刘娥,出身蜀中,结姻江南。
郭熙心中如有蛇在噬咬,皇帝为什么要为刘娥做这么多事,难道他忘记她郭熙才是皇后了吗?
郭熙看到的是宫中事,但她没有看到的是,皇帝这么做,并不是为了一个后宫的女子。清查冗官是实,但是皇帝要操控实权也是实。
但她看得也没错,这样的调整里,固然南方有一些降臣被裁,但更多北方官员的旧部、亲族也因此失位。
虽然内阁之中没有南方的官员为宰相的,但南方的官员精于政务、勇于任事,肯吃苦做事,在这次调整中得到大量迁升,已经成势。刘娥的姻亲不过是钱惟演,但是南方诸官员的提升甚至入阁,都是不可避免的事。
前朝后宫,俱有需求,因此一拍即合。皇后的几个兄长在外头走动了几回,新年一过,便有大臣上表,请求为国家计,宜早定皇储,请立太子。
赵恒至今有过四子,皇后郭氏生了三子,都是在王府出生的,长子与第四子因先天不足,都是襁褓之中便已夭亡,尚来不及赐名。另有宫人戴氏生了皇三子,那孩子长得甚是聪明可爱,不料于皇帝登基那年出了意外,也夭折了。此时后宫之中,便只有皇次子玄祐,那便是无可争议的储君了。
如今赵恒膝下独此一子,自然十分钟爱,且这番上表的是副相赵安仁及御史田锡,此二人俱是以秉直敢言而著称。但此番推举储君,分明就是北方系大臣面对南方系大臣近来的提拔之事而出招了。
太子之立,这是要影响朝政几十年后的走向的,因此这番上书,赵恒看出来了,南官们也看出来了。
赵恒想了想,就让周怀政在水阁布了茶席,叫张怀德去内阁请诸臣来品茶。
张怀德先去了东阁,北派大臣们多聚于此。
此时众人正在说话,说的正是最近皇帝这一系列举动。
皇帝继位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三年过了,正是新皇显示力量的时候。
首相李沆此时正说道:“国事、军事、科举、武举、大赦、免赋、促农桑、观水战、抚北方,官家这一系列的举动恰是这三年的深思熟虑,大宋江山,得圣明天子啊!”
王旦就道:“只是允大将有练兵之权,这个头一开,会不会……”
李沆道:“只是练兵之权而已,如今边境不宁,若边将毫无机动权力,只怕事发仓促之时无应对之法。”
寇準亦道:“自雍熙北伐之后,这十几年来,河北、河东之地大片荒野,若能够恢复农垦,我们在赋税上就不必对南方依赖太重了。”
李沆听了这话一皱眉,劝道:“你对南人的态度,过了。”
寇準不以为意:“当争则争,当夺则夺,都当好好先生,让那些南人占据朝堂,只怕他们把南唐、后蜀旧习气都带进来,不养浩然之气,只钻营细碎机巧,败坏朝纲。这朝堂的立足之地,每一分每一寸都不可轻让,否则就会误国误民。”
李沆却是知道情况,只叹息:“大宋先天不足,失了这燕云十六州,想要国用充足,边境安宁,这田地丈量、税法细分、官营博买,都要这些细碎机巧的功夫啊。”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南边的降官及余荫占据了一个个重要位置。
寇準却道:“我承认国家需要这些细碎机巧的功夫,但这些是小吏做的事,不是朝堂大臣该做的。就如那个王钦若,冒人之功,官家不知,居然还说他体恤民情,想让他入内阁做参知政事,这样的小人,再有细碎机巧的功夫,又怎堪任大臣呢?”
寇準说的是王钦若任太常丞时问三司清理欠款凭据的事。度支判官毋宾古跟王钦若说,有些欠债是旧年百姓因兵灾逃亡而欠下的钱粮,自五代起的债目一直录到现在,其实是无法征收的,不如上奏官家,请让此债务减免。王钦若听了,一边阻止毋宾古上奏,一边自己暗中让人连夜核算好数目和减免成数上奏皇帝,皇帝因此褒奖了王钦若。
北官们知此事,皆为毋宾古不平,道:“正是,此非君子所为也,这样的人,岂能做国之重臣!”
但同样一件事,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却是不一样的。
王钦若的说法是这样的:“毋宾古自己无能糊涂,既知三司清欠多年积弊,这么多年却不思改进,待质问起来,就总用这个理由搪塞。且总数不清,能追回多少不清,减免多少没个成算。官家岂是个糊涂的,如何能由着他说一句赦免就赦免?若不是我算清了报上去请官家赦免,这笔糊涂账从五代积到如今,还想再积多少年?”
钱惟演劝他:“好在官家知道你辛苦做事,不必勉强。”
王钦若叹息:“国朝一统大江南北,可是有形的一统易,心中的一统难。我们这些南方出身的官员在朝中尤难立足,在那些人的眼中,我们这些做实事的人只配小吏一流,岂容与他们同列。我等一事未做就先受攻击,不得不察言观色,战战兢兢,这却又成了一重罪名,开口闭口小人行径。哼!”
冯拯就道:“幸而官家明察秋毫,知道谁是努力做事的人。”
钱惟演又说了一句:“我听说他们欲阻止允大将练兵之权。”
王钦若哼了一声,阴阳怪气地道:“大将不准练兵,南人不准当官,横竖这朝堂只余几个书生大言,空谈误国就好。”
南官们皆不说了,都叹了口气,脸上也有愤然之色。
本朝是从后周得的江山,北派的重臣,溯其渊源,多半自其父祖荫亲,或提携有恩的上级,都有在后周乃至后汉、后晋、后唐时代为官的经历,而勾连成一股看似分散,实则理念认同、互相支援的力量。也恰恰是这股力量的存在,使得官宦世族俱能够抱成一团,虽经五代之乱,军阀们如走马灯似的更替,但这些书香大族却没有像唐末一样,经历一次权力更替就“天街踏尽公卿骨”,反而是越来越强大。
其中历经五代十帝均为宰相的冯道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冯道以其不屈的意志和娴熟的政务能力在身边聚集了一批顶级人才,他们唯冯道马首是瞻。那些军阀经历了唐末的血腥屠杀及一代代朝起暮落,是历经洗礼而生存下来的胜利者,远比刚起事的草莽更精明。他们目睹无数的政权倒塌,加之那些文士长久游说,以血的代价认清,若想要寻找更长久稳固的统治,就必须尊重士大夫们的行政能力。
而冯道,正是士大夫们推出去与军阀周旋的首脑,所以郭威想称帝的时候,见冯道不对自己行礼,就知时机未到而暂退。士大夫们对冯道广为称赞,将他推上“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的声望顶峰。
这股力量在进入新王朝的时候,也产生了新的变化。
世家大族对于军队擅权的恐惧是一以贯之的,所以才有开国之后游说太祖皇帝“杯酒释兵权”的举措。他们对于太宗皇帝擅自北伐,也多有不认可。同时,太宗皇帝时代监军制度对军队的控制,及设立枢密使将军队指挥权力收归等措施导致的一系列军事失当,究其原因,太宗皇帝自己的性情与才能固然是一方面,重臣们施力影响亦是极重要的另一方面。
与之相应的,就是对南方官员的排斥。北官是立国有功之臣,擅长兵事,而南方多年无战事,南官们更擅长抚民安政经济之学。但因南方官员最初都是亡国降臣,先天低人一等。随着大宋立国日久,南方官员于实务上多出成绩而逐步升迁,渐渐影响到朝堂上人数比例。且太宗皇帝时又大兴科举,南方人入朝更多,不能不让北官们为之警惕。
虽然这也并不是一概而论,南官中有才华者也能被北官所赏识,而北官中心胸广阔者也会与南官交好,但这里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就是入阁。
本朝开国至今,尚无南方人入阁为相。
而王钦若,却想当这个第一人,所以他首当其冲遭到了极大的攻击,寇準就公然骂他“小人”,说他“钻营”,由此,王钦若对寇準可谓相当厌憎。
王钦若就说:“我颇想修史,好点评点评冯道。”
丁谓阻止他:“千万不可,若是你敢这么做,他们岂能放过你。”
王钦若也点头,叹气道:“我看,起码还得等上五十年。我想着,必是我们南人,会对冯道有一番重新评定。”
他倒是不曾想到,果然再过五十年,由江西人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就把对冯道的评定由“厚德稽古,宏才伟量,朝代迁贸,屹若巨山”变成了“矫行以取称于世”。自此以后,冯道风评一落千丈,被后世视为无耻之人,则又不为此时的士大夫们所知了。
两人这时候又说起皇帝召众臣商议重定律法的事情来。
五代十国时期,乱世为政,律令不一。大宋建立之后,便急需一个统一的律令。在这样的背景下,淳化三年(992),太宗皇帝以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的内容为蓝本,只在字句上略一修改,便将《淳化令》颁行天下。
只是此时距宋开国已有四十一年,若仍以唐令为标准,已显得不合时宜。赵恒早在为开封府尹时,就遇过许多案子没有合适的律令来判决的情况。再加上后蜀、南唐、吴越等南方诸国与北方又不一样,因此,制定出一部适合本朝的律令已经是当务之急。
然而在这一桩上,又存在极大的争议:本朝不抑兼并,经济上依赖官营榷务极大,因此关于土地田亩、经营度支等方面的律法制定就不得不依赖南官,可北官却不容许南官插手。他们却不曾想到,本朝有大半国土都在南方,这岂是他们能阻止得了的。诸如此类的矛盾层出不穷,这新律法的研究就在磕磕碰碰中进展甚慢。
众人正说着话,内侍张怀德来了,请了诸人去水阁。
结果南官走到外头,正遇上东阁的北官们,双方相遇,北官们自然斜眼等南官让步,冯拯让了一步,王钦若却不肯让。
李沆就笑道:“官家也召了你们去啊。”
冯拯拉了拉王钦若,示意他后退一步。若是不论派系,李沆毕竟是宰相,王钦若让的是宰相之尊,倒也无伤尊严。
王钦若只得退后一步,拱手道:“是。相公辛苦。”
李沆就笑呵呵地道:“都辛苦,都辛苦。”
寇準却冷笑道:“同他们有什么好说的,一堆鸟人鸟语,话都说不利索。”
这时候的朝堂,派别真的很容易分辨,北人都是关洛口音,南边的蜀中口音一派,江南口音又一派,只要一张口,就知道是站哪派的。若下了朝,几个地方成堆的臣子们一说话,所谓南腔北调,若说得快了,真是除了本地人,旁人是听不懂的。北官们就很讨厌南官们扎堆说着自己听不懂的话,而南官们说起中原话来,总带点南方腔调,就被北官们斥之以“鸟人鸟语”。
寇準这话顿时惹恼南官,他们齐声道:“你怎可以言语辱人——”
眼见就要吵起来,就见后头又来了一行人,当先一个拄杖老者笑道:“这都是怎么了,好好的吵什么,难道是天气太热,要争冰饮不成?”
众人见了,一齐行礼,却是上月刚刚被皇帝起召复相的老宰相吕蒙正,这是他第三度复相了。本朝三度为相的,前头只有一个赵普,后头有没有人,恐怕也难说了。
去年吕端去世,赵恒提拔了李沆上来,但还是觉得有些不足。这次裁减冗官过多,恐百官生事,因此才先请了吕蒙正出来复相,再下旨推行。吕蒙正资历深年纪大,不太管具体的事,但有他在阁中,镇得住群臣。吕蒙正气量大,能识人,因此北官中固然有许多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南官中也有许多是他打破成见一力推荐来的。
众人见他来了,俱不敢辩,连寇準都恭敬地上来扶他。
吕蒙正拍了拍寇準的手,意味深长地道:“天下一统,何分南北?俱是大臣,你要多些气量才是。”
寇準不好违他,只得称是。
见众人都应是,吕蒙正便一团和乐地带着众人去了后头水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