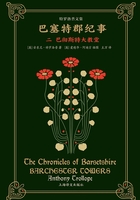
第9章 斯坦霍普家
这时候,普劳迪博士已经就任主教三个月了。他在主教区里已经促成了一些改变,这至少显示出了一个思想活跃的人的精力。这些事里有一件是,到外地去的牧师全得到了相当强硬的暗示,不容他们不予重视。已故的亲爱的老格伦雷主教在这个问题上过分宽厚,会吏长也始终没有想对那些找出一些体面的借口离开的人过分严厉。再说,他们全很大方地为自己的职务作了安排。
在这方面,主教区内最大的罪人就是维舍·斯坦霍普博士。他好多年来一天工作也没有做,然而除了他自身方面缺乏这种意向外,并没有理由说他不尽职。他在主教区内担任着一个受俸牧师的职务,在大教堂区内有一所最精美的住宅,还据有大山楂子树[112]和斯托格平古姆两个大教区。真个的,他据有三个教区的牧师职位,因为爱德塘[113]教区是和斯托格平古姆联合起来的。他在意大利居住了十二年,最初到那儿去是由于一次咽喉疼痛。那种咽喉疼痛虽然始终没有怎么剧烈地再发过,对他却大有好处,因为这使他能够就此一直过着悠闲安逸的生活。
这时候,他奉召回国——说真的,并不是粗暴无礼地,或是通过任何强制性的命令,而是凭着他觉得不能忽视的一道训谕。斯洛普先生根据主教的愿望写了一封信给他。首先,斯洛普先生说,主教在主教区内非常需要维舍·斯坦霍普博士的宝贵合作。其次,他说,主教认为私下结识一下他区内最引人注目的牧师,是他的无可旁贷的职责。再有,主教认为,为了斯坦霍普博士自身的利益,斯坦霍普博士至少暂时应当回到巴彻斯特来,这是绝对必要的。最后据说,教会的主教们对于教士缺席的情况这时表示了那么强烈的情绪,因此维舍·斯坦霍普博士不应让自己的姓名出现在几个月内大概即将递呈给全国宗教会议[114]的那份名单上。
这个最后的威胁中具有一种含糊不清而又十分可怕的意味,因此斯坦霍普博士决计夏天到巴彻斯特他的公馆里来盘桓上两三个月。他的教区长住宅全由他的副牧师居住着。他觉得自己由于长期不工作,已经不适合做教区的职务了,但是他的受俸牧师公馆还空着保留给他。他认为自己也许偶尔还能作为受俸牧师宣讲一篇讲道文。因此,他带着全家到了巴彻斯特。我们必须来把他和他的家属一一介绍给读者。
斯坦霍普家一家人最大的特点或许可以说是冷漠无情,可是他们大多数人同时脾气又那么好,因此这种缺乏感情几乎是不大被世人注意的。他们动辄施点儿小恩小惠给邻居们,因此邻居们没有看到,他们对周围人们的幸福与利益多么漠不关心。斯坦霍普家的人会在你患病时来看望你(只要不是传染病的话),会给你带来橘子、法国小说和最新的一点儿丑闻,随后以同样漠不关心的平静神情听到你的死亡或是康复。他们对待彼此的方式,就和对待世人的态度一样。他们再三容忍,往往像我们今后可以看到的那样,也很有必要容忍,不过他们之间的爱护难得超出这种情绪。这家人中每一个成员能够做出多少事,的确做了多少事,来妨碍另外四个人的福利,这一点是令人吃惊的。
因为他们一家是五口人,那就是:博士、斯坦霍普太太、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许,博士是他们中最平庸、最可尊重的人,然而他具有的那些优良品质竟然全是消极的。他是一位容貌端庄、血气旺、年龄大约六十上下的人,一头蓬松的白发,有点儿像最上等的羊毛,络腮胡子很大、很白,使他的脸看上去像一只年老、和善的睡狮。他的服装是无可指摘的。尽管他在意大利居住了这么多年,服装却一直是庄重的牧师色泽,不过始终不是牧师气息很浓的。他是一位不好多话的人,可是他说的那一点儿话,一般总说得恰到好处。他阅读的书籍平时总是最轻松的传奇与诗歌,用意也不总是惩恶扬善的。他是个地地道道的bonvivant[115],是个擅长于品酒的人,虽然他饮酒从不过量,又是一切烹调事务的一个最不讲情面的批评家。自从一个家庭围绕着他成长起来后,他在自己家里有不少事情得加以宽恕,他也就宽恕了一切——只有疏忽他的那顿晚餐,是一个例外。他在这方面的弱点如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的脾气也难得受到考验。由于斯坦霍普博士是一个教士,可以相信,他的宗教信念构成了他的个性的一大部分,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说他有宗教信念,这是应该相信的,但是他很少把它们强加于人,连对子女也是如此。他这方面的这种克制并不是存心的,不过很能代表他这个人的个性。我们并不是说他事先就决定,决不去影响儿女们的思想,可是他惯常那么懒散,因此他这么做的时刻始终就没有到来,等它到来时,这么做的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问父亲具有什么样的信念,子女至少仅仅是他领取俸禄的这个教会中漠不关心的教友。
这就是斯坦霍普博士。斯坦霍普太太个性上的特征,比她丈夫的还要含糊不明。她在意大利过的far niente[116]的生活已经深入她的心灵,使她渐渐把清静无为看作是人世间唯一的美德。在态度和外貌方面,她是落落大方、讨人欢喜的。她年轻时曾经是个美人儿,就连现在五十五岁了,也还是个标致的娘儿们。她的衣服总是十分精美的,白天总齐齐整整只穿上去一次,而且总要到三四点钟之间才走出房来,但是到她出来时,她总修饰得顶好。这一番辛苦部分是她自己出的力,还是完全是她的贴身女仆出的力,这是像作者这样一个人不应去妄加揣测的。她的衣服的款式一向很精致,可又从来不过分着意。她的服装很华美,可并不打扮得艳丽俗气。装饰品是昂贵的、罕见的,是那种免不了会引起人家注意,可看来又不像是为那个目的而佩戴的。她很知道修饰自己外表的那个重大的“建筑学秘密”,从来没有贬低身份去“构造出”一个装饰来。但是当我们说斯坦霍普太太知道怎样穿着,每天都运用自己的学问时,我们把话也就说尽了。她在生活中其他什么意图全没有。真个的,她不去干预别人的意图,这可是一个长处。早年,她为博士的晚餐曾经吃过很大的苦头,但是过去这十一二年,大女儿夏洛特已经从她手里接过了这份苦差事,她没有多少事得去烦心了,——没有多少事烦心,那是说,在要求他们作这次可怕的英格兰之行的那个通知寄来以前;在那以后,真个的,她的生活是很辛苦的。就这样一个人来说,从科摩湖滨搬运到巴彻斯特城去的那份辛苦,是十分吃力的活儿,就算搬运人十分留神并始终小心谨慎的话。斯坦霍普太太不得不把她的每一件衣服全从行囊中取出折叠起来。
夏洛特·斯坦霍普这时候大约三十五岁。不管她具有什么过失,她却没有老小姐们特别具有的那种。她的衣着并不显得年轻,谈吐并不显得年轻,真个的,外表也不显得年轻。她对自己的生活似乎十分满足,压根儿并不装出年轻人的风度来。她是一个秀丽的年轻妇女。倘若她是个男人,那也会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男人。家里的一切活儿,仆人不干的,全由她来做。她作出种种吩咐,缴款付账,雇用和打发走仆人,沏茶,切肉,管理斯坦霍普家庭里的一切。她,也只有她,能够说动父亲去照看一下自己种种世俗事务的情况。她,也只有她,能够稍许控制住妹妹干的种种荒唐事。她,也只有她,防止了他们全家陷入绝对的贫穷与不名誉。这时候,他们就是根据她的意见,才发觉自己很不惬意地待在巴彻斯特的。
到此为止,夏洛特·斯坦霍普的个性并不是令人讨厌的。不过有一点还该说一说:她在家里具有的影响,虽然多少是给用去促进他们在世间的福利,却并没有像原可以的那样,用去助长他们的真正利益。她帮助父亲对他的职责漠不关心,告诉他,他的教区是他个人的产业,就和他哥哥的庄园是那位可尊敬的贵族的产业一样。过去几年,博士倒不时表示出想回英国来一趟的愿望,她把流露出的所有这些小的愿望都扑灭下去了。她曾经怂恿母亲懒散怠惰,这样她自己可以成为斯坦霍普家的女主人和大管家。她曾经怂恿并助长了妹妹干的种种蠢事,虽然她始终愿意,时常也能够保护着她,使她逃脱那些蠢事可能产生的后果。她曾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惯坏了她的兄弟,让他踏入社会,成了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懒汉,又没有分文可以说是他自己的。
斯坦霍普小姐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大多数话题她都能谈,而且实在也不在意谈的是什么话题。她因为不受英国偏见的影响而感到很自豪,同时她还可以加上一点:她也不受女性娇气的影响。宗教方面,她是一个纯自由思想者[117],很缺乏真实的爱,专喜欢在父亲的烦扰的头脑面前抛出自己的见解来。倘使她动摇了他对国教残存的那一丁点儿信仰,那她就会感到十分满意,不过要他放弃教会里职位的这个想头,却始终没有一次出现在她的脑子里。说真的,他从其他方面得不到任何收入的时候,怎么能够放弃呢?
不过他们家最突出的两个成员还有待我们来叙述一下。第二个孩子在受洗礼时取名叫马德琳,她曾经是一个大美人儿。其实我们用不着说“曾经”,因为她从来没有比我们写到的这时候更加美丽了,虽然她身体多年前因为一个意外事故而变得残废。我们没有必要来详述一下马德琳·斯坦霍普早年的历史。她到意大利去的时候大约十七岁,曾经得到允许在米兰的各个沙龙里和科摩湖滨那些拥挤的别墅里充分展现了一下她的艳丽绝伦的姿色。她经历了种种奇遇,使她变得名噪一时,可并没有失去她的声誉。她毁了十二三个大献殷勤的男子的心,自己的感情却没有一次受到影响。为了她的姿色,人们争吵流血。她欣喜而激动地听到了这些冲突。据人家传说,有一次她还乔装改扮成一个小厮站在一旁,看着她的情人倒下。
如同时常发生的那样,她嫁给了向她求婚的最恶劣的那个人。她为什么选中了保洛·内罗尼,眼下用不着来细说。保洛·内罗尼是一个出身不好、没有产业的人,当时仅仅是教皇卫队中的一名队长,到米兰来不是单单投机冒险,就是充当间谍。他为人脾气粗暴,态度油滑,身材猥琐,脸膛黝黑,谈吐那么虚伪,时时刻刻都会给人发觉出来。当结婚的时候到来时,她大概没有其他的选择。不管怎么说,他成了她的丈夫。在湖泊区度过了一个长时期的蜜月以后,他们一块儿到罗马去,教廷的队长曾白费力气地试图说服妻子留下不去。
六个月后,她回到父亲的家里来,成了一位跛足的母亲。她甚至事先没有通知就到达了,身上几乎衣不蔽体,给新娘的嫁妆增添光彩的那许许多多首饰一件也没有了。婴儿是由米兰的一个穷姑娘抱着。这是她新雇了来代替陪她走了这么远的那个罗马女用人的。那个女用人据她女主人说,变得很想家,所以回去了。很清楚,这位小姐决计不让一个目击者来讲述她在罗马生活中的遭遇。
她说,她在登上一处古迹的遗址时摔了一跤,严重地损伤了一面膝盖的筋肉,非常严重,以致当她站起来时,她比平日的高度矮了八英寸——非常严重,以致当她试图走动时,她只能痛苦地拖曳着走,凸出半边屁股,把一只脚比驼背的人还不雅观地伸了出去。因此她一下子打定主意,从此不再站起身,也决不试图走动了。
多种传说跟在她身后很快就传来了,证明她遭到了内罗尼蛮横的虐待,她的不幸就是内罗尼的暴力行为所造成的。尽管如此,关于她的丈夫,谈到的很少,而谈到的那一点儿使家里人很清楚地知道,决不会再见到或听说到内罗尼“先生”[118]了。允许这个可怜的、遭到虐待的美人儿重行享有过去的家庭权利,这是没有问题的,把她的新生女儿收养在斯坦霍普家,这也是没有问题的。斯坦霍普家虽然冷漠无情,却并不自私。这母女俩给接纳进去,受到宠爱和照料,有一阵子几乎十分喜欢,随后老夫妇俩又觉得她们是家里的两个最讨厌的人。可是这个女人却回到了家里,而且长待下去,任意而为,尽管那种行为和一位英国牧师平日的习惯是很不相称的。
内罗尼太太虽然被迫放弃了世上的一切活动,却压根儿无意遁世。她的美貌并没有受到损害,而那种美貌是很特出的。她的浓密、华美的褐色头发,像一道道希腊式缎带[119]那样裹住了她的头,把前额和脸蛋儿尽可能地衬托出来。她的前额虽然相当低,但由于轮廓均匀、肤色晶莹洁白,所以非常俊美。眼睛又大又长,炯炯有神。倘使我可以很冒昧地说它们亮得像魔鬼[120]的一样,我或许最确切地表达出了她眼睛光彩的深度。那是一双看来很可怕的眼睛,完全会阻止任何心地平静、精神安逸的人去和这样一个敌人交锋。这双眼睛里有才气,有热情的火焰和焕发的机智,可就是没有爱。相反的,只有残忍与勇气,一种渴想征服的欲望,狡黠奸诈,以及一种恶作剧的意愿。然而,作为眼睛,它们是十分俊俏的。眼睫毛很长,很完美,而她注视着爱慕她的情人的那种长时间镇定自若的目光,既迷惑又吓住了他。她是一个蛇妖[121],一个热爱美色的人是逃脱不了她的。她的鼻子、嘴、牙齿、下巴、颈子和胸部没有一处不生得尽善尽美,到二十八岁时比她在十八岁时还要完美。在她脸上还焕发着这种妩媚的姿色,身个儿由于残疾而遭到损害后,她决心让人们依然看见她,不过只看见她斜靠在一张沙发上,这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她的这一决心实行起来并不是没有困难。她在米兰仍旧常常到歌剧院去,偶尔还出现在noblesse[122]的大客厅里。她让人把自己从马车上抬出抬进,而且要一点儿不影响到她的媚人的姿态,不揉皱她的衣服,不暴露出她的残疾来。她的姐姐总陪伴着她,还有一个女用人和一个男仆,遇到隆重的场合,则有两个男仆。要达到她的目的,比这数目少的人是办不到的。但是,尽管她贫穷,她却达到了目的。接下来,使她父亲不挺满意的,米兰的比较放荡的青年人又常常上斯坦霍普家的别墅来,包围了她的长沙发椅。有时候,她父亲会气恼起来,脸上露出一丝不高兴的神色,他还会表示反对,可是夏洛特会用烹饪术的某种独特的“成就”使他平息下去,于是一切又会安稳上一阵子。
马德琳在她的房间里,她的身上,以及她的女性用品等的装饰方面,喜爱各种各样奢华、精致的小玩艺儿。这在她自己准备的名片上最为明显。我们会说,在她目前的情况中,这样一件东西不会有多大用处,因为她正式外出访问,是多么不可能,但是她自己的见解可不是这样。她的名片四周有一道很阔的金边,上面印有三行字:
马德琳“夫人”[123]
维舍·内罗尼
——纳塔·斯坦霍普
在姓名上面,还印有一个色彩鲜明的金冠,确实显得很华贵。她怎么想着给自己编造出这样一个姓名来,这是很难加以说明的。她父亲的名字叫维舍,就像别人取名叫托马斯一样。她没有权使用它,就像一个乔赛亚·琼斯先生的女儿,嫁给一个史密斯先生以后,没有权自称乔赛亚·史密斯太太一样。那个金冠也是同样不合适的,或许加上去更没有什么借口。保洛·内罗尼没有一个最最含糊的头衔,可以自称是意大利贵族的后裔。如果这两口儿是在英国邂逅的,内罗尼大概就会是一位伯爵,可是他们是在意大利相遇的,他那方面的任何这种冒充,都会是荒谬可笑的。然而,王冠是一个很好看的装饰品,如果印在名片上可以安慰安慰一个可怜的跛足女人,那么谁又会不乐意由她去呢?
她绝口不提她的丈夫,或是他个人的家庭,不过跟爱慕她的情人待在一起时,她时常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暗暗讲到自己的婚后生活与孤独的状况,并且指着她的女儿说,她是皇帝们的最后一点骨血,这样提到内罗尼有古罗马皇族的血统,古罗马皇帝中最暴虐的一个就是出自那个家族的[124]。
“夫人”可不是没有才干,也不是不具备某种勤奋的本质。她写起信来孜孜不倦,而她的书信也是值得所花的那笔邮资的。她的信里充满了机智、恶作剧、讽刺、爱情、自由主义哲学、自由的宗教信仰,以及,啊呀!放肆的下流玩笑。然而,主题完全取决于收信人。除了端庄的年轻妇女或是古板的老婆子以外,她准备跟随便什么人通信。她还创作一类诗,一般是用意大利文创作,又写一些篇幅很短的传奇,一般是用法文写。她阅读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作品,作为一个现代语言学家,当真是非常熟练的。这就是这时候前来伤害巴彻斯特男人们心的这个女人。
埃塞尔伯特·斯坦霍普在某些方面很像他的小姐姐,不过作为一个男人,他可不及她作为一个女人那么难以估量。他的最大的过失是,完全缺乏操守,使他没有能作为一个没有财产的人的儿子,自行去谋生。家里曾经作过多次尝试,想使他这么做,但是这些尝试全失败了。这主要倒不是由于他那方面的懒散,而是由于不合他胃口时,他就不愿意卖力。他在伊顿[125]受的教育,原来打算学做牧师,但是在剑桥读了一学期后,他厌恶地离开了那儿,并且通知他父亲说他想去学法律。为了做一些准备,他认为最好应当到一所德国大学去学习,因此就到莱比锡去了。他在那儿待了两年,带回来德语的知识和对美术的爱好。不过他仍旧打算做一个律师,于是到律师事务所去,拜倒在一位博学的人士门下,在伦敦度过了一个时期。他在那儿发觉自己的才能使他倾向于过一个艺术家的生活,于是又决计靠绘画来谋生。抱着这一目的,他回到米兰,收拾好了到罗马去。他作为一个画家,本来也许可以自行谋生的,因为他只要用功,便能崭露头角。但是到了罗马,他却见异思迁。不久,他写信回家要钱,说他信奉了天主教,已经是耶稣会[126]的一个新信徒,就要和别人一块儿出发上巴勒斯坦去,执行使犹太人改信天主教的使命。他的确到了朱迪亚[127],可是并没有能使犹太人改变信仰,反而被他们说得自己信了犹太教。他又写信回家说,摩西[128]是给予人世间最完善的法律的唯一先知,又说真正的救世主就快到来了,重大的事情正在巴勒斯坦进行着,还说他遇见了西多尼亚家族的一个成员[129],一个最出色的人,这时候正上西欧去,他说动了这人,使他离开了预定的路线,目的是来访问一下斯坦霍普家的别墅。埃塞尔伯特接下去表示,希望母亲和两位姐姐乐意听这位惊人的预言家谈谈。他的父亲他知道,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是不能这么做的。然而,这位西多尼亚并不怎么喜欢他,不像那个家庭里的另一个人从前喜欢一位年轻的英国贵族那样。至少他并没有提供给他一堆堆像狮子那么高大的黄金[130],因此信仰了犹太教的埃塞尔伯特,不得不再一次凭借基督教教会的收入来生活。
我们用不着说,那位父亲怎样发誓说他决不再汇钱去,也决不接待犹太人;也用不着说夏洛特怎样讲,不能让埃塞尔伯特待在耶路撒冷身无分文,以及“内罗尼夫人”怎样决心要使这个西多尼亚拜倒在她的脚下。那笔钱汇了出去,那个犹太人也当真来了。那个犹太人也当真来了,可是他压根儿不合“夫人”的胃口。他是一个肮脏的小老头儿,虽然没有提供金狮子,却似乎使小斯坦霍普摆脱了贫困。他干脆拒绝离开别墅,直到他从博士那儿得到了一张给博士在伦敦的银行家的汇票。
埃塞尔伯特并没有长期信奉犹太教。他不久就重新出现在别墅里,对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偏见,同时抱着坚定的决心,要以雕塑家的身份获得声誉和财富。他带回家来一些他在罗马创作的模型,它们使人觉得他实在颇可造就,因此父亲给说动了进一步花钱去促进这种意图。埃塞尔伯特在卡拉拉[131]开设了一家铺子,或者不如说是租下了几间房和一间工作室,在那儿糟蹋了不少云石,制作了几件美丽的雕像。从那时(如今已经有四年了)以后,他不断往来于卡拉拉和别墅之间,不过他在工作室逗留的时间越来越短,在别墅逗留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卡拉拉可不是一个英国人乐意居住的地方。
当全家动身回英国来时,他决心不单独留在后面,于是在大姐姐的帮助下,不顾父亲的反对,达到了他的目的。他说,他有必要到英国来获得一些订货。不这样,他怎样在自己的这一行中搞出个名堂来呢?
在容貌方面,埃塞尔伯特·斯坦霍普是一个顶特别的人。他确实很漂亮,生有小姐姐马德琳的那种眼睛,可是没有那种凝神注视的目光,也没有那种凶狠冷酷、狡黠而又坚定的神色。两眼的颜色也比她的要浅得多,是一种异常澄澈的浅蓝色,这使他的脸显得与众不同,倘使没有别的使它显得与众不同的话。我们跟埃塞尔伯特一块儿走进一间房时,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的蓝眼睛,离开那间房后,最后才会忘却的几乎也是他的蓝眼睛。他的浅色头发很长、很光滑,一直拖到上衣上。胡须是在圣地[132]蓄起的,显得俨然可畏。他从来不剃胡子,也难得去修剪它。胡须柔软、整洁而有光泽,总的说来并不惹人讨厌。它是妇女们可能想绕起来,用它代替丝线,绣成她们需要的花样。他的肤色是白净的,几乎是嫩红色,他身量不高,四肢细瘦,但很匀称,嗓音特别悦耳动听。
他的举止与衣着也同样与众不同。他丝毫没有英国人的那种mauvaise honte[133],并不需要任何寒暄介绍来使自己讨人欢喜。他惯常不拘任何礼节就去跟陌生男人和女人攀谈,在这么做时似乎也从来没有碰到非难。他的服装是无法加以形容的,因为它多种多样,可是它在颜色与式样方面,总是和他一时混在一块儿的那些人的完全相反。
他惯常喜欢跟女人调情,这么做的时候良心上毫无顾忌,也就是说,丝毫没有想到这种作风是不对的。他没有怕给触痛的心情,简直不知道人类会受到这样的损伤。他没有去多想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有人问他,他就会说,待一个女人薄情,意味着损害到她在社会上的上升。因此,他的操守不允许他去垂涎一个姑娘,要是他认为有一个适合她下嫁的男人在场的话。这样,他的温厚的性格常常妨碍了他的玩乐,不过没有其他的动机会使他不去对他看中的每一个姑娘尽情倾吐出他的爱慕之情来。
但是伯蒂·斯坦霍普——人家一般全这样叫唤他——在男人中和女人中都很受欢迎,在英国人和在意大利人中也一样受到欢迎。他认识的人非常多,包括各种各样的人。他并不注重等级,也不厌恶身份比他低的人。他跟英国贵族、德国店主和罗马教士都很亲密。对他说来,所有的人几乎全都一样。他是脱离了任何偏见的。没有什么德行能够使他倾倒,也没有什么罪恶能够使他大吃一惊。他具有一种生来文雅的态度,似乎使他有资格出入最高的阶层,然而他在最低下的阶层中也从不显得不相称。他没有原则,不顾别人,不尊重自己,也不渴望在蜂房中做一个不单单是雄蜂的角色,只要他作为雄蜂,可以得到足够他需要的蜂蜜的话。关于蜂蜜,大概可以预言,他在往后的日子里只会获得不很充足的数量。
这就是斯坦霍普家的家庭成员。他们这时候忽然前来,加入了巴彻斯特大教堂区的宗教界。也许,不可能想象出比这更奇怪的结合了。这可不像是他们全体落进了以前一直不知道、没提过的这片大教堂区。那样的话,新来的人和普劳迪一伙人或是格伦雷一伙人就根本不可能混到一起了。情况远不是这样。巴彻斯特对斯坦霍普家每一个人的名字全都知道,所以准备张开胳膊来欢迎他们。博士是巴彻斯特的一位受俸牧师,一位教区长,是它的一根擎天柱。再说,普劳迪家和格伦雷家全都指望他是一位可靠的盟友。
他自己是一位贵族的弟弟,他妻子是另一位贵族的妹妹——这两位贵族都是倾向于辉格党的爵爷,新主教和他们结成了某种同盟。这就足以使斯洛普先生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在他的敌人可以出奇制胜之前,他能把斯坦霍普博士拉拢到他那一方去。另一方面,老教长多年以前,在博士致力于牧师工作时,曾经大力帮助他升任高级圣职,而这两位博士,斯坦霍普和格伦雷,多年前以年轻牧师的身份,曾经在牛津的公共宿舍里欢聚在一起。格伦雷博士因此毫不怀疑,认为新回来的人管保会站到他的旗帜下来。
他们谁也没怎么想到,斯坦霍普家这时候是由一些什么样的成员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