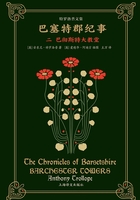
第10章 普劳迪夫人的招待会——开始
主教和他太太第一次来,只在巴彻斯特度过了三四天。主教大人如同我们见到的那样,已经正式就职,可是尽管他原来想使自己的举止中具有不少高级教士的尊严,却由于家庭牧师的那篇鲁莽的讲道文,而给大大搅乱了。他几乎不敢抬眼去看他的牧师们的脸,不敢用严厉的脸色表示,他实在的意思就是他的“总管”代表他说的那样。他也不敢把斯洛普先生抛开,让周围的人看到他并不赞同这篇讲道文,而对之产生不满。
因此,他以一种沉闷的态度为他的教区人民祝福,自己一点儿也不觉得满意。他走回主教公馆去,心里十分怀疑,不知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该对那个家庭牧师说点儿什么。他并没有怀疑上很久。他刚费力地脱去细麻布法衣[134],他的同甘共苦的伙伴[135]便走进了他的书斋,连坐还没有坐下就大声嚷道:
“主教,你听说过一篇比这更崇高、更得体、更发聋振聩的讲道吗?”
“噢,亲爱的,哈哈——嗯——唔!”主教不知说什么是好了。
“我希望,主教,你总不见得是说你不赞成吧?”
夫人的目光里有一种神色,不允许主教此时表示不赞成。他感到要是自己打算表示不赞成。那么必须不是这会儿就是永远不说,可是他又觉得眼下实在无法说。不能由他来把内心想的对他的贤内助说,斯洛普先生的讲道文是不合时宜、傲慢无礼和惹人气恼的。
“不是,不是,”主教回答,“不是,我可不能说我不赞成——那是一篇很机敏的讲道文,用意很好,大概会起不少好作用。”最后这句夸赞话是加上去的,因为他看到前面说的那几句话压根儿没使普劳迪夫人感到满意。
“希望是这样,”她说,“我确信这篇讲道文是应该讲的。你一生中听见过有什么比哈定先生唱连祷更像演戏的事呢,主教?我要请斯洛普先生继续发表一连串关于这个问题的讲道文,直到这种情况完全改变。咱们在咱们的大教堂里,至少要有一种体面的、神圣的、朴实的早礼拜式。这里决不可以再有什么演戏的事了。”说完,夫人便打铃叫人安排午饭。
主教对于大教堂、教长、圣诗班领唱人和教堂礼拜式,比他妻子知道的要多,对于主教的权力知道的也比她多。可是他认为眼下最好不去多谈这个问题。
“亲爱的,”他说,“我想咱们星期二非得回到伦敦去。我发觉我待在这儿会给政府带来很多不便。”
主教知道,他太太对这个提议是不会反对的。他还感到,这样从战场上撤走,激烈的战斗或许可以在他不在这儿的时候结束掉。
“斯洛普先生当然就留在这儿啰?”夫人说。
“唔,当然啦。”主教说。
这样,在主教公馆里逗留了不到一星期,主教就从巴彻斯特溜走了,两个月都没有回来,到那时候伦敦的社交季节已经结束。在这一时期里,斯洛普先生并没有闲着,不过他也没有再试图在大教堂里讲道。普劳迪夫人写了几封信来,建议他发表一连串讲道文。作为答复,他解释说,他至少希望把这样一件事延缓到她在这儿,可以来听听的时候。
斯洛普先生利用这一时期来巩固一个普劳迪—斯洛普党——或者不如说是一个斯洛普—普劳迪党。他可没有白费光阴。他并不去干扰教长和牧师会,只用一些小事情去戏弄他们,通知他们说,主教希望这样,主教觉得那样,这种方式使他们感到十分烦恼,可是他们又不能抱怨。他在那个城市郊区的一座遥远的教堂里讲过一两次道,不过并没有提到大教堂的礼拜式。他开始成立了两所“主教的巴彻斯特安息日学校”,发出通知说还计划设置一个“主教的巴彻斯特男青年安息日晚讲堂”——又写了三四封信给巴彻斯特铁路分公司的经理,告诉他主教多么急切地希望,星期日的几次列车应停止驶行。
但是两个月后,主教和夫人又回来了。作为通报他们即将回来的一个美好的预兆,他们答应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晚会。请帖是从伦敦发出的——注明了日期,从布鲁顿街发出,并且是用褐色纸张包成一大包,由那条可恶的破坏安息日的铁路送来,交给斯洛普先生的。巴彻斯特城里和城外方圆两英里内所有自命是上流社会先生和女士的人们,全给邀请到了。请帖送给了主教区里所有的牧师,还送给了许多其他很有名望的教士。主教,至少是主教夫人,觉得很有把握,认为这些人是不会来的。不过这次晚会却打算开得宾客盈门,引人注目。他们作好准备,打算接待一百位左右的来宾。
话说这时,格伦雷派人士中情绪有点儿激动不安,他们应不应该接受主教的邀请呢?他们大伙儿最初的感觉是,借故为自己和妻子女儿写一封最简短的辞谢信。可是渐渐地,策略战胜了愤怒的情绪。会吏长察觉到,如果他听凭大教堂的牧师使主教有正当的生气理由,那么他就大为失策了。他们全体举行了秘密会议,同意全去赴约。他们要表示出来,尽管他们也许不喜欢这个人,他们却乐意对这个职位表示尊敬。他们同意去了。老教长也将缓缓地走去,就算只去半小时的话。大教堂司铎、司库、会吏长、受俸牧师和低级驻堂牧师全都要去,而且全带着他们的太太。哈定先生特别受到嘱咐,要他前去,他心里拿定主意要远远躲开普劳迪夫人。波尔德太太也决定前去,虽然她父亲告诉她,她那方面绝对没有必要得作出这样的牺牲。当全巴彻斯特都到那儿去的时候,爱莉娜和玛丽·波尔德全不明白,她们为什么不应该去。她们不是单独受到邀请的吗?跟主教的那张大请帖一起,那个家庭牧师不是还另外附有一封措辞极为恭敬的短信吗?
斯坦霍普家全家也都要去赴会。就连那位懒懒散散的母亲在这样一个时刻也振作起来了。他们刚才到达,请帖就已经在牧师公馆中候着他们了。巴彻斯特谁也还没有看见他们。他们能有什么更好的机会在巴彻斯特社会上露面呢?有几位老朋友,例如会吏长和他太太,来拜访了他们,见到了博士和他的大女儿,但是这个家庭的“杰出人物”还没有为人所知哩。
说真的,博士心里很想阻止“夫人”[136]接受主教的邀请,可是她本人作出决定要接受。如果她父亲对于把女儿抱进主教公馆去觉得害臊,她可没有这种感觉。
“真个的,我要去。”她对姐姐说,姐姐曾经很平和地试图劝说她不要去,说客人尽是些牧师和牧师妻子。“牧师敢情跟其他的人一样,如果你把他们的黑法衣剥去了的话,至于他们的妻子,她们大概不会叫我怎么为难。你可以告诉爸爸,我压根儿不打算给留在家里。”
姐姐告诉了爸爸,他觉得除了听凭她去以外,自己什么办法也没有。他还觉得,现在来为自己的儿女感到害臊是无益的。他们成了这样,是在他的纵容下变得如此的。他铺的床,就得由他睡。他播的种,就得由他割[137]。当然,他并没有用这种话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不过这却是他思想的要点。他怕看见马德琳成为主教的一位客人,倒不是因为她脚跛了,而是因为他知道她会施展她惯用的诱人伎俩,一举一动必然会使规规矩矩的英国妇女感到讨厌。在意大利,这种情况使他生气,可是没有使他震惊。在那儿,这种情况并不使谁感到吃惊,但是在巴彻斯特这儿,在自己同道的牧师们当中,给人家看到这种情况他觉得很害臊。这就是他的心情,可是他抑制住了。如果他的同道牧师们大吃一惊的话,那又怎样呢!他们不能因为他一个出了嫁的女儿行为太放肆,就把他在教会里的职务夺走。
内罗尼夫人好歹并不担心自己会使随便谁大吃一惊。她就希望引起一场大轰动,让牧师们拜倒在她的脚下(因为巴彻斯特的男人主要就是牧师),并且办得到的话,让每一个牧师的妻子全满怀嫉妒、脸色铁青地转回家去。对她说来,没有人年纪太大,几乎也没有人年纪太轻。没有人是过于神圣的,也没有人过于世俗。她完全准备勾引主教本人,然后翘起头来对着主教的太太。她毫不怀疑自己能够得手,因为她向来总是成功的,不过有一件事绝对必要,她必须有一张沙发供她专用。
给斯坦霍普博士和太太,以及他们子女的请帖,也是装在一只封套里送来的,封套上写着斯洛普先生的姓名。“夫人”不久就知道,普劳迪夫人还没有回到主教公馆来,那个家庭牧师正在负责处理一切。去和他联系要比去和主教夫人联系她更为擅长,因此她写了世上最绮丽的一封短笺给他,在五行文字中说明了自己要说的一切。她说要她不来结识一下巴彻斯特主教和主教夫人,还有斯洛普先生,那是多么不可能,接下去便叙述了一下自己的痛苦状况,最后表示深信,普劳迪夫人对于她请求允许给抬到一张沙发上去,一定会原谅她的鲁莽冒昧的。接着,她附去了一张她的精美的名片。她收到了斯洛普先生的一封同样客气的复信——一定放一张沙发在大客厅里,就在那道大楼梯通上来的地方,专供她使用。
随后,招待会的日期到了。主教和他夫人到那个重大日子的上午才从伦敦回来,像这类大人物该做的那样,不过斯洛普先生曾经日夜操劳,照料着把一切都安排就绪。要做的事情可不少。天知道主教公馆从什么时候以来就没有见到过宾客了。需要添置一些新家具,新的锅盘碗盏,新的茶杯茶碟。普劳迪夫人起初说过,她决不自贬身份去在意饮食这种庸俗的事,但是斯洛普先生出于节约却劝说她,或者不如说是写信给她!主教们应当热情好客,而好客就意味着饮食。这样,这个晚餐会才蒙她同意了,不过客人们全得站着吃。
公馆的二楼上有四间房,每一间都通进另一间去。它们是两间客厅、一间接待室和普劳迪夫人的小客厅。从前,这些房间里有一间是格伦雷主教的卧房,另一间是他的起居室兼书房。然而,现在的主教却搬到楼下一间后客厅去住了,并且获悉,他在餐厅里可以很好地接待他的牧师们,如果他们人来得太多,无法让进他那间很小的私室去的话。他开头不愿意让步,可是经过一场短暂的辩论后,终于屈服了。
普劳迪夫人在察看她那套房间时,心头十分激动。这几间房实在富丽堂皇,至少在烛光下会显得是如此,但是它们却没花多少钱就布置起来了,这是很可赞赏的。大房间里挤满了人、洋溢着灯光时,总显得很气派,因为房间很大,挤满了人,又灯烛辉煌。小房间就需要昂贵的装饰和考究的家具。普劳迪夫人知道这一点,尽量利用了它。她因此弄来了有十二只灯头的巨型煤气灯,悬挂在每一间房的天花板上。
客人将在十点钟到达,晚餐将从十二点持续到一点,到一点半,大家全都散去。马车将由市区里的那道大门进来,由外面的那道大门离去。要求马车在一点前一刻就准备来接人。这件事安排得十分周到,斯洛普先生可真是挺有价值的。
九点半钟,主教和他太太,以及他们的三个女儿走进了那间大接待室。他们全很华丽、很严肃。斯洛普先生正在楼下对酒做一些最后的吩咐。他很知道副牧师和乡下教区牧师,以及他们的家眷,并不像大教堂区里的长老们那样,不需要这么慷慨的一件东西。在这类事情上,有一种大有裨益的等级之分。二十先令一打的马尔撒拉酒[138],对于外面角落里附加的那几桌来宾也就很不错了。
“主教,”主教大人坐下时,夫人这么说,“请你别坐在沙发上。沙发是专为一位女士安排的。”
主教忙一跳站起身,在一张藤心椅子上坐下。“一位女士?”他恭顺地问,“你是说专为一位女士安排的吗,亲爱的?”
“是呀,主教,专为一位女士安排的。”他妻子说,不屑详细去解释。
“她没有腿,爸爸。”小女儿吃吃笑着说。
“没有腿!”主教睁大了眼睛说。
“胡说,内塔,你说些什么呀,”奥利维亚说,“她有腿,可她不能行走。她平时不得不总躺下,由三四个男人抬着她到处走。”
“啊呀,多么古怪啊!”奥古斯塔说,“总由四个男人抬来抬去!我想我决不喜欢这样。我后面没问题吗,妈妈?我觉得好像是敞开着。”她转过身去,把背对着关心的母亲。
“敞开着!你当然是敞开着啰,”她说,“裙带挂下来有一码长。我不知道干吗付给理查兹太太这么高的工资,如果她不能操心照料着你们的外表是否合式的话。”说着,普劳迪夫人把这儿的带子掖了掖,把那儿的衣服拉了拉,又把女儿推了推,摇了摇,然后才说她没问题了。
“可是,”主教又说,他对这位神秘的女士和她的腿感到非常好奇,“使用这张沙发的究竟是谁呢?她姓什么,内塔?”
前门上一阵雷鸣般的敲门声打断了这次谈话。普劳迪夫人站起来,轻轻地动了一下,用手扶了扶帽子的两边,朝镜子里瞧了瞧。每一个姑娘都蹑手蹑脚地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胸前的蝴蝶结。斯洛普先生三级并作一级奔上楼来了。
“究竟是谁,内塔?”主教悄声对小女儿说。
“是马德琳·维舍·内罗尼‘夫人’,”女儿悄声回答,“您可得留神,别让谁坐在这张沙发上。”
“马德琳·维西尼罗尼‘夫人’[139]。”这个迷惑不解的大教士自己嘀咕说。要是内塔告诉他奥德的公主[140]或是西群岛的波马拉女王[141]要来光临,他也不会更为吃惊了。马德琳·维西尼罗尼“夫人”,她的腿站不起来,事先说好要在他的客厅里使用一张沙发!——她会是谁呢?可是那会儿他无法进一步再去询问,因为仆人通报说,斯坦霍普博士和太太来了。他们稍早一点儿就给送出来,以便“夫人”可以有充分时间很方便地给抬上马车。
主教笑容满面地迎着这位受俸牧师的太太,主教夫人也笑容满面地迎着这位受俸牧师。斯洛普先生也给介绍过了,他很高兴结识一位常听见人家说起的长老。博士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显得仿佛无法来回答一下斯洛普先生的这句恭维话,因为,说真的,他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斯洛普先生。博士尽管长期不在国内,见到一位英国高尚人士,还是识别得出来的[142]。
接着,客人大批到来了:奎瓦富先生和太太,以及他们的三个成年的女儿。贾德威克先生和太太,以及他们的三个女儿。那位粗壮结实的大教堂司铎和他的太太,以及牛津回来的一个做牧师的儿子。那个没有家累的瘦小的博士。哈定先生跟爱莉娜和波尔德小姐。教长由一个憔悴的老闺女搀扶着,她是他唯一的孩子,这时候和他生活在一起。这位小姐对于石头、蕨类植物、一般植物和害虫很有研究,曾经写过一部关于花瓣的书。特雷福伊尔小姐就她的为人而言,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我们还可以看到法律代理人芬雷先生和他的妻子,这使许多以前在客厅里从来没有会见过他的人感到十分惊愕。巴彻斯特的五位医师全都到了,还有那位退休的药剂师兼拔牙医生老斯卡尔彭,他收到主教的请帖后,第一次受到教育,要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上层社会的人士。随后,会吏长和他太太带着大女儿格里珊尔妲[143]来了。格里珊尔妲是一个身材苗条、脸色苍白、腼腆怕羞的十七岁姑娘。她紧跟着她的母亲,用恬静而又留神的眼睛注视着外界,是一个长大成人后,管保会变得十分俏丽的人儿。
这样,房间里便挤满了来宾。他们三三五五,形成了一小群一小群。每一个新来的客人都向主教致意,然后朝前走去,以免这位大人物来过分招待。会吏长热忱地跟斯坦霍普博士握手。格伦雷太太挨着博士太太的身旁坐下。普劳迪夫人摆出很有分寸的风度忙来忙去,对人献出多少殷勤,完全按照各个客人的身份来决定,就像斯洛普先生对于款待客人的酒那样。但是沙发依然空着,二十五位女士和五位先生,都曾由那个留神注意的家庭牧师彬彬有礼地预先说了一声,才没有在那儿坐下。
“她干吗不来呢?”主教暗自想着。他一心想到那位“夫人”,因此几乎忘了自己作为主教一举一动该如何了。
最后,一辆马车疾驶到门厅的台阶前。它驶来的方式和那天晚上驶来的任何其他车辆大不相同。公馆里起了一大阵骚动。博士站在客厅里,听见了它,知道他的女儿来了,于是退到最远的角落里去,在那儿可以不看见她进来。普劳迪夫人这时候振作起精神,觉得有件重要的事情即将到来了。主教本能地知道维西尼罗尼夫人终于来了。斯洛普先生急匆匆地走进了门厅,预备从旁帮助。
然而,他在门厅台阶上碰到的“扈从”险些儿把他撞翻,踏倒。他尽可能站起身来,跟着“扈从”走上了楼。“夫人”给头朝前抬了进来,她的头部是由她兄弟和一个惯常做这种差使的意大利男仆照料着,脚是由夫人的女用人和夫人的意大利小厮照料着,夏洛特·斯坦霍普跟在后面,照料着一切都做得相当大方和得体。这样,他们很轻松地走上了楼,进了客厅,人们立刻让出了一条大路,“夫人”很安稳地在长沙发椅上靠坐下。她事先曾经派了一个仆人来打听,是一张头在左边的还是头在右边的沙发[144],因为她需要根据这一情况穿好衣服,特别是戴好手镯。
她的衣服很合身。它是一件白天鹅绒服装,上面没有别的装饰品,只有胸前用考究的白花边和珍珠盘成的一些花纹,袖口也盘有一圈同样的花纹。在前额上,她扎了一条红天鹅绒带子,中央闪亮着一只华丽的镶嵌成的丘比特像[145],他的翅膀是极其可爱的天蓝色,丰满的脸蛋儿是极其明净的淡红色。她靠坐在那儿,露出一只胳膊来。在那只胳膊上,她戴了三只精美的手镯,每一只上的宝石全不一样。在她身下的沙发上,铺有一件大红绸披风或是围巾,从沙发头上、靠垫上一直铺到了她的整个儿身子下面,把她的脚也遮盖起来了。她穿着这样的衣服,外表又打扮成这样,显得那么艳丽而又那么文静,身下披风的颜色把白衣服的晶莹纯洁衬托出来,并且有所增强,再加上那个美丽的脸庞和那双大胆、闪亮、咄咄逼人的大眼睛,所以不论男女,都不可能不去看她。
有好几分钟,男男女女别的事不做,就那样看着她。
抬她的人也很值得注意。那三个仆人全是意大利人。尽管他们在自己国家或许并不特别,在巴彻斯特的主教公馆里却很特别。那个男仆尤其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使有些人心里疑惑不定,不知他是朋友呢,还是仆人。他们对埃塞尔伯特也同样感到疑疑惑惑。那个男仆身穿一件宽大、普通的黑呢晨礼服。他生着一张肥胖、洁净、心满意足的脸,脸上一点儿胡碴儿也没有。脖子上围着一条松散的黑绸领巾。主教试图朝他哈哈腰,可是这个仆人由于受过很好的训练,压根儿没有去注意主教,他轻松自在地走出了那间房,后面跟着那个女用人和那个小厮。
埃塞尔伯特·斯坦霍普从上到下穿了一身浅蓝色的服装。他穿着极其宽松的蓝上衣,像猎装那样剪裁得四四方方,而且很短,还用天蓝色的丝带滚了边,里面穿着一件蓝缎子的背心,围了一条蓝领巾,用一只珊瑚环把它束在喉咙下面,下身穿着一条宽大的蓝裤子,几乎把脚也遮盖起来了。他的柔软、光滑的胡子这天显得前所未有的柔软、光滑。
主教先前犯过一次错误,所以这时候以为他也是一个仆人,因此空出地方来,让他走过去。可是埃塞尔伯特很快便纠正了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