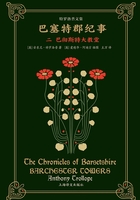
第5章 午后的一次正式拜访
普劳迪博士根据我们已经提过的那项议会法令,不得不很快重新委派一位养老院院长,这件事是众所周知的,不过谁也没有想到他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谁也一刻没有想到,除哈定先生外,他能委派别的什么人。哈定先生听到这件事并没有过分使他烦恼就解决了以后,自己也认为,他管保会回到那所可喜的住宅和花园里去。虽然这样一次重返是会有不少令人忧郁的,不,几乎是令人伤心的事情,可是他仍旧乐意回去。他的女儿大概可以给说动了回来跟他一块儿住。真个的,她几乎已经答应这么办了,尽管她仍旧抱有一种想法,认为那个最了不起的人儿,人类的那个重要的小不点儿,世上的那个小神明,她的毛娃子小约翰·波尔德,理应自己有一所住宅。
哈定先生对这件事的心情就是这样,他个人对于任命普劳迪博士来当主教并不感到有什么特殊的利害关系。他和巴彻斯特的其他人一样,对于派一个新人到他们中来全感到很遗憾。他们深知,这个人的想法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不过哈定先生本人在教义的要点上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所以完全准备以一种庄重得体的态度欢迎普劳迪博士到巴彻斯特来。他一无所求,一无所惧。他觉得自己是应该跟主教保持友好关系的,他并没有预见到有什么障碍会妨害到这种关系。
在主教和他的家庭牧师抵达后的第二天,他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情前往主教公馆去作礼节性拜访。不过他不是独自去的。格伦雷博士提议陪同他一块儿去。哈定先生对于有一个人陪着,并不觉得遗憾,因为这个人会从他肩上把这样一次会晤中寒暄应酬的负担接过去。在主教的就职典礼上,格伦雷博士曾经被介绍给主教。哈定先生当时也在场,然而他却待在后面不惹人注目的地方。现在,他就要第一次给引进去谒见那位大人物了。
会吏长的情绪要比他强烈得多。他决不会听任自己的权利遭到人家忽视,也决不能原谅对另一个人表示出的偏袒。普劳迪博士正扮演着挫败他这位朱诺的维纳斯[72]。他是准备对自己也希望得到的果实的实际获得人,以及他的全体仆从、家庭牧师和其他的人,进行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的。
虽然如此,他觉得还是应该像一位老会吏长对待一位新来的主教那样,对这个闯进来的人尽他的礼数。尽管他很知道普劳迪博士对于不信奉国教的人、教会改革、星期委员会[73]等等所抱的可恶的见解,尽管他不喜欢这个人,憎恶他的学说,可是他仍然准备对主教的身份表示敬意。因此,他和哈定先生一块儿到主教公馆拜访去了。
主教大人这时候正在家,两位客人于是给领着穿过过去常常进出的那个门厅,进入那间熟悉的屋子,慈祥的老主教过去就总坐在那儿。那套家具是按估定的价格买来的,每一张椅子、每一张桌子、靠墙放的每一只书架、地毡上的每一个正方形花纹,对他们俩,全都和自己的卧房一样熟悉。虽然这样,他们顿时便感到自己在那儿是陌生人了。家具大部分还是原来的,可是那地方已经变了样。新放了一张沙发进去,那是一件令人厌恶的印花棉布家具,非常不合乎高级教士的身份,几乎是亵渎神明的。在英国国教任何一位庄重的高教派教士的书房里,还从来没有放过这样一张沙发。旧窗帘也已经换去了。当然,那些窗帘都早已失去了光泽,原来是鲜艳、漂亮的红玉色,后来已经褪成了红褐色。不过哈定先生却认为从前那种红褐色,要比这时用的华丽而俗气的浅黄色劣质波纹布可取多了,但是普劳迪夫人则认为,这种波纹布用在外郡城市巴彻斯特她丈夫自己的房间里挺不错。
我们的朋友发现普劳迪博士正坐在老主教的椅子上,穿着簇新的黑色长坎肩[74],显得很神气。他们还发现,斯洛普先生热切而自诩地站在壁炉前的地毡上,就像会吏长过去惯常站在那儿那样。不过他们同时又发现,普劳迪夫人坐在那张沙发上。这是一项“革新”,我们从巴彻斯特主教的全部历史记载中,也许就无法找出一个先例来。
但是她却坐在那儿,他们只好尽量凑合着。通过了不少礼节来介绍。会吏长先和主教握手,然后通报了哈定先生的姓名。哈定先生受到了主教对圣诗班领唱人理应给予的那份欢迎。接下去,主教大人把他们介绍给他的夫人,先以会吏长应当享有的种种荣誉介绍了会吏长,接下去才介绍了领唱人,礼遇也有所递减。在这以后,斯洛普先生自我介绍了一番。不错,主教的确报了他的姓名,普劳迪夫人也用比较响亮的声音报了,可是斯洛普先生自己承担起了介绍自己的主要责任。他对于结识格伦雷博士感到十分高兴,他在主教区内会吏长行使职权的那部分地方[75],听说到不少会吏长的善举(从而存心装作不知道会吏长以前在整个主教区里享有的无限统治权)。他深知,主教大人在主教区里那部分地方非常要倚仗格伦雷博士将会给予的协助。接着,他伸出手,握住这个新对头的手,毫不留情地用汗水濡湿了它。格伦雷博士也回鞠了一躬,显得很生硬,他皱了皱眉头,还用手绢揩了揩手。斯洛普先生若无其事,这时候才注意到了领唱人,于是屈尊来俯就这个等级稍低的教士。他使劲儿握了握哈定先生的手,真个的,他的手很潮湿,但很亲热。他还说自己很乐意结识——啊,不错,哈定先生。他实在没有听清楚他的姓名——“大教堂圣诗班的领唱人,”斯洛普先生猜测。哈定先生说,这正是他卑微的工作的性质。“另外还担任一个教区的工作吧,”斯洛普先生这么提示。哈定先生承认自己还承担圣喀思伯特教堂那份很小的职责。斯洛普先生赏够了哈定先生脸面以后,便撇下他,加入权力较高的人们的谈话中去了。
当时在场的有四个人,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是主教区内最重要的人物,真个的,他自己或是她自己,因为普劳迪夫人也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的意见那么各不相同,所以一块儿相处得很融洽是不大可能的。主教本人如今明明白白地穿着长坎肩,主要也就倚仗着这一点——倚仗着这一点和他的头衔,因为这两件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会吏长很熟悉他的话题,而且真正懂得主教的职责,这是其他人全及不上的。这是他强有力的一点。普劳迪夫人因为是女人,从而占了一点儿便宜,她又习惯于发号施令,所以一点儿也没有给格伦雷博士脸上和身个儿上的那种傲慢神气所吓倒。斯洛普先生可以倚仗的就只是他自己和他的胆量与机智,不过他却泰然自若,深信自己不久就会战胜这些非常信赖外表的软弱的人,像主教和会吏长两人当时显出来的那样。
“您住在巴彻斯特吗,格伦雷博士?”夫人带着最亲切的微笑问。
格伦雷博士解释说,他住在普勒姆斯特德—埃皮斯柯派他自己的教区里,就在城外几英里路的地方。夫人听了忙说,她希望到路途并不太远的乡间走一趟,因为她很乐意去结识一下格伦雷太太。等她的马儿到了巴彻斯特以后,她一定趁早去一次。他们的马儿目前还在伦敦,不会立刻就给运来,因为主教几天之后就不得不回京城去一趟。格伦雷博士无疑知道,“大学改进委员会”[76]眼下很需要主教。说真的,那个委员会少了他,就不能很好地进行工作,因为他们的最后报告这时候正得起草。主教还是“工业城镇早晚主日学校协会”的赞助人、会长或是理事,他必须为这个协会准备一份计划,因此目前马儿不会运到巴彻斯特来。但是不论什么时候,等马儿一运来,她就会利用最早的机会到普勒姆斯特德—埃皮斯柯派去拜访,只要去乡间拜访的路途不是太远的话。
会吏长鞠了第五个躬:每逢对方一提到马儿,他就鞠上一躬,并且保证说,格伦雷太太会感到十分荣幸,如果能早日来到主教公馆拜访的话。普劳迪夫人说,那她会感到很高兴的,她本来不好邀请人家来,因为她拿不准格伦雷太太有没有马。再说,路途也可能是如何如何。
格伦雷博士又鞠了一躬,但是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可以把普劳迪家的每一件财产全部买下,然后作为礼物归还给他们,而不怎么感到这一损失。自从结婚以后,他就另外备有两匹马儿,专供太太使用,而普劳迪夫人以前在社交季节总在伦敦街头按月计费雇用马车,在其他的时候则设法步行,或者去马车行叫一辆轻便马车。
“关于安息日学校[77]的安排,在会吏长您的教区里一般是不是很不错呢?”斯洛普先生问。
“安息日学校!”会吏长装作惊讶地重复了一遍,“真个的,我可没法说。这主要取决于教区牧师的妻子和女儿。普勒姆斯特德就没有。”
这可以说是会吏长撒的一个小谎,因为格伦雷太太办有一所很不错的学校。当然,它并不完全是一所主日学校,也不被这样称着,不过那位可以作为楷模的太太在上教堂前总到那儿去一小时,听孩子们念教义问答,照料着他们洗洗手,结好鞋带,干净整洁地上教堂去。她女儿格里珊儿和佛洛林妲总提一篮子星期六下午烘好的大圆面包到那儿去,把它们分给没有特别失宠的孩子。这些面包在教堂仪式结束后就给相当满意地带回家去,吃茶点时候趁热吃,因为那时它已经给切开烤过了。普勒姆斯特德的儿童们真会睁大两眼,如果他们听见他们尊敬的牧师说,他的教区里没有主日学校的话。
斯洛普先生只把眼睛睁大了点儿,还微微耸了耸肩。然而,他并不准备放弃他心爱的计划。
“我恐怕这儿有不少人安息日出去旅行吧,”他说,“我看了《铁路指南》[78],发现每逢休息日有三班火车开进来,三班火车开出去。能不能采取什么办法劝说铁路公司取消这几班列车呢?您认为,格伦雷博士,花一点儿精力是不是可以减少这种邪恶呢?”
“我因为不是董事,实在没法说。但是要是你能把旅客拉走,那么铁路公司大概就会把那几班车取消啦,”博士说,“这只是红利的问题。”
“可是当然,格伦雷博士,”夫人说,“咱们对这问题的看法当然该不同啦。比方说吧,您和我处在咱们的地位上,当然该做咱们能做的一切来控制住这么严重的一个罪恶。您认为是这样吗,哈定先生?”她转身对着领唱人,他这时候正默不作声、很不快活地坐在一旁。
哈定先生认为,所有的搬运工人、烧火工人、列车员、司闸工、扳道工,全应当有机会上教堂去。他希望他们全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当然啦,当然啦,”普劳迪夫人说下去,“那当然是不够的。那样当然不会使人严格遵守安息日,而咱们受的教导却认为,严格遵守不仅是有利的,而且是必要的。当然——”
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格伦雷博士是不会被迫去跟普劳迪夫人就教义上的一点进行一场辩论的,更不会去跟斯洛普先生进行一场辩论了。因此,他不拘礼节地转过身,背对沙发,开始表示,希望普劳迪博士觉得公馆的修缮工作还能合他的意[79]。
“是呀,是呀。”主教大人说。总的说来,他认为是这样——总的说来,他可不知道有多少可抱怨的理由。那位建筑师大概会——可是他的替身斯洛普先生已经侧身走到了他的椅子旁边,斯洛普先生没有容主教大人把这句语意不明的话说完。
“有一点我想提一提,会吏长先生。主教大人叫我在公馆里各处走走。我瞧见第二个马厩里的分隔栏不太完善。”
“怎么——那儿可以拴上十二匹马。”会吏长说。
“大概是这样,”另一个说,“真个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可是您知道,客人们往往需要那么许多地方。主教有那么许多亲亲眷眷,他们总是自己备得有马。”
格伦雷博士答应,至少在原来马厩的建筑允许的范围内,为亲戚们的马匹再做出适当的安排。他将亲自和建筑师联系一下。
“还有那个马车房,格伦雷博士,”斯洛普先生说下去,“在那个大马车房里,实在匀不出什么地方来多停一辆马车,而小马车房里当然只好停一辆了。”
“还有煤气,”夫人插话说,“屋子里到处全没有煤气,除了厨房和走道里,哪儿也没有。公馆里当然应当各处全装好煤气管,还有热水管。除了底层,楼上随便哪儿也没有装热水管。当然应该有这种设备,可以在寝室里用得到热水,不必从厨房里用大壶把热水提上去。”
主教坚决认为,应当有热水管。热水对于主教公馆内的舒适,是不可缺少的。说真的,在任何一位上流人士的合适的宅子里,热水都是必需品。
斯洛普先生说,花园围墙的盖顶[80]有许多处都损坏了。
普劳迪夫人发现,下房里有一个大窟窿,显然是老鼠咬出来的。
主教表示他十分讨厌老鼠。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他对随便什么都没有像对老鼠那么憎恶。
此外,斯洛普先生还说,外屋的门锁全有缺陷。他可以特别提出贮煤室和劈柴房来。
普劳迪夫人还看到,仆人们寝室门上的锁也同样不安全。真个的,整所宅子的锁全是老式的、不起作用的。
主教认为有不少事全取决于一把好锁,也有不少事取决于钥匙。他曾经注意到,毛病往往出在钥匙上,尤其是如果榫槽扭歪了一点儿的话。
斯洛普先生还在数说着他那一大堆不满的事情时,会吏长嗓音相当洪亮地打断了他的话。会吏长成功地解释明白,这些问题理应向主教区的建筑师,或者不如说,他的工头去细讲,他,格伦雷博士问到公馆里是否舒适,只不过是问候问候。但是有这么许多事情全不称心,他觉得很遗憾。说完,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逃走了。
普劳迪夫人尽管设法从旁帮着扼要地说明主教公馆的破旧情况,却并没有因此就放过哈定先生,也没有停止她对安息日进行娱乐活动这种罪恶的反复盘问。她一遍又一遍朝着哈定先生虔诚的脑袋抛出了她的“当然啦,当然啦”,那位先生对这种攻击简直有点儿招架不住了。
他以前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讨厌的干扰。过去,妇女们向他请教宗教问题时,总相当恭敬地听着他乐意要讲的话,而且如果意见不同,那也只是默默地表示不同。可是普劳迪夫人却质问他,接下去又教训他。“你和你的儿女、仆婢……无论何工都不可作,”[81]她气概非凡地说,而且说了不止一遍,仿佛哈定先生忘了这句话似的。她一面引用这条她特别喜欢的戒律,一面用一只手指朝着他摆摆,仿佛威胁要惩罚他似的。接着,她又断然要他说明,他是否认为安息日旅行是一件令人厌恶的行为,一件亵渎神明的行为。
哈定先生一生中从来没有给人这样逼迫过。他觉得一个女人对一位比她年长许多的有身份的先生和教士这么放肆地讲话,他实在应该斥责她,然而想到在他第一次到主教公馆来拜访的时候,当着主教的面竟然斥责主教的妻子,他又畏缩起来。再说,讲老实话,他也多少有点儿怕她。她看见他一语不发、若有所思地坐在那儿,并没有停止她的攻击。
“我希望,哈定先生,”她说,一面慢吞吞地、一本正经地摇摇头,“我希望您不会让我认为您赞成安息日旅行吧。”说着,她目光里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神色直盯着他的两眼。
这可叫人受不了啦,因为斯洛普先生这会儿正望着他,主教也望着他,会吏长也是如此,会吏长已经在房间那边告辞完毕了。哈定先生因此也站起身,把手伸给普劳迪夫人,说:“要是您哪个星期日上圣喀思伯特教堂来,我一定就这个问题为您讲一次道。”
这样,会吏长和圣诗班领唱人便起身告辞,对夫人深深鞠了一躬,又和主教握了握手,然后以各自能采用的最好的方法,从斯洛普先生的面前溜走。哈定先生这回又遭到了粗暴的对待,可是格伦雷博士心底里却坚决起誓,尘世间的不论什么顾虑,都决不能使他再去碰这个肮脏污秽的畜生的爪子了。
倘使我具有一位气势磅礴的诗人的笔力,我就会写一首叙事诗来称颂会吏长所感到的愤怒了[82]。主教公馆的台阶往下通到一条宽阔曲折的砂砾路上,那儿有一道小门,外面就是街道,很靠近通入大教堂区的那座门楼。主教公馆门外的那条大路向左转去,穿过宽敞的园林,直达距离大教堂半英里外通向伦敦的那条大道。
他们俩在穿过那道小门,走进大教堂区以前,谁也没有说话,不过圣诗班领唱人从他同伴的脸色上很清楚地看出来,一场龙卷风就要兴起来了,他自己也不想去阻拦它。虽然他生性远不像会吏长那么容易恼怒,但也生气了,他——那位温良谦和的人——他甚至也想用随便什么只要是不礼貌的语言来把自己的愤慨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