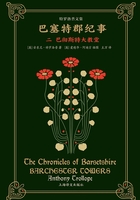
第4章 主教的家庭牧师
关于斯洛普牧师的家庭出身,我可无法说出多少话来。我听人家讲,他是帮着给那位特·香迪先生[58]接生的杰出大夫的直系后代,早年为了读出来好听,在自己的姓氏后面加了一个字母“e”,像在他以前的其他大人物做过的那样。假如这是实情,那么我猜他受洗礼时取的名字大概是奥巴代亚(这正是他的名字)[59],为的是纪念他祖先那么大显身手的那场冲突。然而我就这个问题进行的全部研究,都没有能使我确定这个家族改变了宗教信仰的日期。
他早先是剑桥大学的一名减费生,在那儿的表现至少很不错,因为经过了适当的时期,他成了一位硕士,有些大学生归他辅导。从那里,他调到了伦敦,成为贝克街上新造的一所区教堂的传道师。就在他担任这个职位的时候,他提出的一些关于宗教问题的看法和普劳迪夫人志趣很相投,使她很赏识他,他们的交往变得很频繁,很亲密。
斯洛普先生这样亲密地置身在那几位普劳迪小姐当中以后,某种超出友谊的柔情自然而然便产生了。他和他寄予厚望的那位大小姐奥利维亚之间互相倾吐过一些爱慕之情。但是顶到这会儿,并没有作出什么顺利的安排。实际上,斯洛普先生曾经明白地向她求过爱,可是后来知道博士在世上没有直接的存款可以给他的孩子时,连忙又收回了自己的话。普劳迪小姐经他那方面这样一说之后,也不会很快就接受任何进一步求爱的表示,这是不难想象的。在普劳迪博士奉派担任巴彻斯特主教以后,斯洛普先生的看法确实稍许改变了点儿。主教们就算家境贫穷,也可以替当牧师的孩子们安排一下。斯洛普先生开始后悔,自己没有把私心杂念排开一点儿。他听到博士高升的消息后,立刻重新开始了追求,说真的,并不是炽热地,而是殷勤有礼,保持相当距离的。可是奥利维亚·普劳迪是一个颇有志气的姑娘,身上有两位贵族的血液。而更好的是,她的名册上已经另有了一位情人。所以斯洛普先生只好空叹息了。不久,这一对男女不可避免便结下了不解的仇恨。
经过这样一件事后,普劳迪夫人和这个年轻牧师的交情竟然还很牢固,这一点想来也许很特别。但是说老实话,她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她本人虽然很喜欢斯洛普先生,却从没有想到她的一个女儿也会喜欢他。她想到她们出身高贵,在社交方面又享有种种好处,指望她们能结下一种大不相同的姻缘。那位先生和那位小姐觉得没有必要来让她知道。奥利维亚的两个妹妹都知道这件事,仆人们也全知道,住在附近两边房子里的邻居们也全知道,就是普劳迪夫人给蒙在鼓里。
斯洛普先生不久便想到,既然自己给挑选了来做主教的家庭牧师,就能够得到主教馈赠的这份礼物中的好处,而不必去为主教的女儿烦恼。这样安慰了一下自己后,他觉得能够忍受失恋的痛苦了。当他在火车车厢里坐下,面对着主教和普劳迪夫人时,当他们第一次上路到巴彻斯特来时,他心里开始为未来的生活拟定一项计划。他很知道提拔他的人的长处,不过他也知道他的短处。他相当正确地知道,新主教正兴高采烈,会尽力干出一些什么事来。他还准确无误地猜到,社会生活比起主教区职务的种种琐事,要更合乎那位大人物的胃口。
因此,他,斯洛普先生,事实上就会成为巴彻斯特的主教了。这就是他的决定。说句公道话,斯洛普先生既有勇气又有魄力,可以把自己的决定付诸实行。他知道大概有一场恶仗要打,因为另一个工于心计的人也同样渴望取得主教的权力与圣职授予权,那就是普劳迪夫人,她也乐意当巴彻斯特的主教。不过斯洛普先生自认为他用谋略能够战胜那位夫人。因为她必须常常住在伦敦,可他却一直待在当地。她对不少事情必然一无所知,而他却会知道教区里的一切巨细。开头,毫无疑问,他在某些事情上非得奉承、哄骗,也许还得作出一些让步,但是他对最后胜利却是深信不疑的。如果所有其他的手段全失败了,他可以和主教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夫人,使那个倒楣人的心里鼓起勇气,彻底夺去那个女人的权柄,把丈夫解放出来。
这些就是他坐在火车车厢里,望着昏昏沉沉打盹儿的那两口儿时,心里所想到的。斯洛普先生不是一个为这种想头白操心的人,他具有超出一般人的才能,而且很有胆量。虽然他能够自贬身份,讨好拍马,并且倘有需要的话,真能够卑躬屈节,但是内心里,他还是可以扮演一位暴君的。他有这种能力,当然也就有这种愿望。他的才学并不是特别出众的,可是它们能完全听他支配,他知道怎样运用它们。他具有几分讲道的口才,对男人,说真的,不可能有多大说服力,可是对女性却非常有影响。在他的讲道文里,他多半进行指责,用一种并非令人不快的恐怖内容,使心地软弱的听众[60]激动起来,并在她们心上留下一个印象,认为全体男人都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里,全体女人也是如此,只有晚上经常在贝克街听他讲道的人不在其内。他的神色和语音十分严厉,以致人们不能不以为,他的确是把世上的大部分人都看作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因此他不屑去加以照管了。在他从街头走过时,他的脸上就表明了他对世上邪恶的憎恶,他的眼角旁边经常暗含着一种强烈谴责的神情。
在教义方面,他和提拔他的人一样,也宽容不信奉国教的人,如果一个思想这么严密的人会宽容什么事情的话。他跟韦斯利—循道公会教徒[61]有一些共同之处,不过想到普西派教徒[62]的罪恶,他的心就痛苦得颤抖起来。他的反感既涉及内心的事物,也涉及外界的事物。他看到一座屋顶坡度很陡的新教堂,就感到恼怒,一件把胸部完全遮起的黑绸背心,在他眼里就是撒旦的象征,而一本亵渎神明的笑话集在他看来,并不比一本用红字印的、封底装饰着一个十字架的祈祷书,更为肮脏地玷污了一个基督徒在教堂中的座位。大多数活跃的教士都有自己的嗜好,而严格遵守星期日便是他的嗜好。然而,“星期日”是一个从来没有玷污过他嘴巴的词儿——他总是说“安息日”。一个人“亵渎了安息日”,像他喜欢说的那样,对他来讲便是无上的乐事。他就靠这个发了起来,就像一个警察靠社会上一般人的坏习惯发了起来那样。这是他晚上讲道中最爱讲的话题,是他口若悬河的源泉,也是他左右妇女心情的全部奥秘。在他看来,上帝的启示就只显示在要犹太人遵守的那一条法则里[63]。在他看来,我们救世主的宽恕是白说了的;在他看来,在山上由耶稣亲口讲的那篇讲道也是白讲了的[64]——“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65]。”在他看来,《新约全书》相当无关紧要,因为从那里面他无法为他喜欢行使的统治权获得什么新的权力,而他是喜欢至少对尘世间人类分配到的时间的七分之一[66],行使统治权的。
斯洛普先生身材很高,体格结实,手脚都很粗大,就和他家里所有的人一样,不过他的胸膛和肩膀全很宽阔,这抵消了那方面的多余部分。总的说来,他的身个儿是匀称的。不过他的容貌并不特别讨人喜欢。他的头发又细又直,颜色是暗暗的淡红色,平时总分成齐齐整整、起伏不平的三大片,每一片都梳得一丝不乱,而且用不少油脂黏合在一起,两片头发紧紧地贴在脸孔的两边,另一片成直角长在那两片上面。他没有蓄连鬓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他的脸色几乎和头发一样,虽然或许稍微红点儿,它可有点像牛肉——不过你会说,是质量不好的牛肉。脑门子又阔又高,四四方方,显得很迟钝,而且亮晃晃的,叫人很不愉快。他的嘴巴很大,但嘴唇很薄、毫无血色。一双凸出的浅褐色大眼睛激起了人种种激情,就是不叫人信任。可是鼻子却作了补救。据说他的鼻子是挺直的、端正的,要不是外表有点儿像多孔的海绵,仿佛是用一只涂成红色的软木塞很灵巧地做出来的,那么我就会更喜欢它点儿。
去和斯洛普先生握手我始终容忍不了。他身上分泌出一种黏糊糊的冷汗,点点滴滴老是出现在他的额头上。他的亲切友好的握手总是令人很不舒服。
这就是斯洛普先生——这就是突然落到巴彻斯特大教堂区内的那个人。他注定要在那儿承担起以前一直由已故主教的儿子承担的那个职位。沉思默想的读者啊,请你想想看,对于在格伦雷主教慈祥恺悌的庇护下在巴彻斯特成长起来的那些舒舒服服的受俸牧师,那些具有绅士风度的牧师博士,那些得到优厚的待遇、丰衣足食的快活的低级驻堂牧师[67],这儿可来了一位什么样的同事啊!
不过斯洛普先生跟着主教夫妇上路到巴彻斯特来,可不是仅仅来当那些人的一位同事的。他打算即便不做他们的主教大人,至少也是他们中的首领。他打算来获得一批追随者。他打算抓住主教区的财权,把一群饥饿贫穷、唯命是从的教友聚集到他的周围。
在这儿,我们简直不能不把会吏长和我们这位新的家庭牧师进行一次比较。尽管会吏长有许多过失,比较下来我们简直不能不说,结果是对他十分有利的。
两个人都热中于,过分热中于维护和增加他们自己教会的权力。两个人都渴望世界由教士来统治,虽然他们大概连对自己也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两个人都抱怨人对人所保有的任何其他形式的统治。格伦雷博士要是承认女王在宗教事务方面至尊无上的话[68],那也只是承认,这是由于她的加冕典礼的神圣性质所赋予她的如同神职人员的身份。他认为世俗事物根据它们的性质,全都受到精神事物的支配。斯洛普先生对僧侣统治的看法,性质完全不一样。他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毫不在意女王至尊无上这一点。这些话在他听来全是空话,是毫无意义的。他不大重视形式,“至尊无上”“神圣性质”“圣职授予”这种种有名无实的词句,对他全不表示什么重要的意义。让做得到的人去唯我独尊吧。人世间的国王、法官和典狱长,只能对肉体施展他们的影响。精神的主宰,如果具备必要的才能,能够适当地运用它们,就可以享有一个幅员更为辽阔的帝国。他是对灵魂发挥作用。如果他可以使人家相信他,对听他讲道的那些人来说,他就可以变得非常强有力。如果他十分谨慎,不去干预智力出众或生性软弱的人,那么他也许当真是唯我独尊的。这就是斯洛普先生的抱负。
格伦雷博士对于那些多少归他管辖的人在世上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大干涉。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不去注意教士们当中有失检点的行为,以及他教区里不道德的行为或是他家里人的疏忽懈怠,不过遇到没有必要的时候,他素来不急切地这么做。他并没有好奇的毛病。只要他周围的人没有沾染上不信奉国教这种异教徒的倾向,只要他们充分而坦率地承认母教会[69]工作非常有效,他是很愿意那位母亲亲切仁慈,宽大为怀,不希望去惩处别人的。他自己享有世上的种种好东西,喜欢让人家知道他的情况。随便哪一位教区长道友如果认为举行晚餐会是有害的,或是害怕一只中等大小的红葡萄酒壶的种种危险,他会从心底里看不大起那个人,因此晚餐会和红葡萄酒壶在主教区里是很普通的。他喜欢制定法规,由大家绝对遵守,但是他总尽力使他的法令一般人都能办到,而不是上流社会的先生感到讨厌的。这时候,他已经在附近一带的牧师中统治了好多年。由于他维持了自己的权力,又没有变得不受人欢迎,我们可以认为,他是运用了相当的智慧的。
关于斯洛普先生的行为,我可说不出多少话来,因为他的重要的经历尚未开始,不过我们可以假定,他的爱好和会吏长的大不相同。他认为,了解托付他照管的教友们私下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欲望,是他的职责。他要求贫民阶级对规定的行为准则无条件地遵守。如果有人不遵守,他总像他的老祖宗那样,求助于一位埃尔尼菲[70]的大声斥责:“你出去进来都该受罚——你一饮一食都该受罚”等等,等等。对待阔人,经验已经教给他,有必要采取一种不同的行动方针。上层社会里的男子不在乎挨人咒骂,至于女人,如果是用典雅的词句咒骂,她们只有喜欢。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就放弃掉这么重要的一部分信道甚笃的基督徒。跟男人们,说真的,他一般总有些分歧。他们是无动于衷的罪人,使用教士的迷人的声音多半不起作用,可是对女人们,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坚定的还是脆弱的,虔诚的还是放荡的,他认为自己是强有力的。他会用那么多恭维话去谴责一些过失,用那么亲切的态度去进行非难,因此妇女的内心要是闪耀着一星星易受低教派[71]感化的火花,就总抵挡不住他。因此,在许多人家里,他是一位深受钦佩的客人。那些丈夫为了他们的妻子,很愿意接待他,而一旦接待了他以后,就很不容易摆脱他。然而,他有一种笨拙的、谄媚的作风,使那些并不为了自己的灵魂而尊重他的人,全不喜欢他。他不是一个能使自己在一个很大范围内——例如,这时候在巴彻斯特可能会围绕着他的那么许许多多人当中——顿时就受到欢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