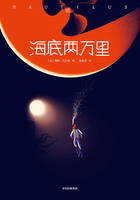
八 动中之动
这起绑架事件发生得极其突然,快得就像一道闪电。我和伙伴们简直都没回过神来。我不知道他们走进这浮动的监牢的时候心中会有什么感觉,但我自己却不禁打了个寒战,感觉皮肤都冰凉了。我们跟谁打交道呢?无疑,这是一群称霸海洋的新型海盗。
狭小的舱盖一关上,我就陷入了一片漆黑之中。我的眼睛习惯了外面的光亮,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感到赤裸的双脚踩在一架铁梯子上。尼德·兰和康塞尔被人抓得紧紧的,跟在我后面。铁梯下面,一扇门打开了,我们走进去以后,门就立即关上,发出响亮的回声。
现在只剩下我们了。我们在哪?我说不上来,也猜不出来。只见一片漆黑,一片绝然的黑暗。过了几分钟,我的眼睛没有捕捉到一丝光线,就是通常在最深沉的夜晚飘忽不定的那种模糊光线也没有。
尼德·兰对这些人的行事方式非常愤慨,他大发雷霆。
“鬼东西!”他叫喊道,“这儿的人待客是在向苏格兰人看齐!他们只差吃人肉了!就算他们吃起人肉来,我也不会奇怪,不过我要声明,我不会乖乖地任人宰割的!”
“安静些,尼德,我的朋友,安静些,”康塞尔平心静气地说,“您先别发火。我们还没有被放在烤盘里呢!”
“对,还没有放在烤盘里,”加拿大人答,“但我们已经在烤炉里了,毫无疑问!这儿这么黑。幸亏我的单刃猎刀还带在身边,我的眼神还可以,用起来没问题。只要这帮强盗有人敢把手搭在我身上……”
“尼德,您别发脾气,”我对鱼叉手说,“发火没有什么用,只会把事情搞坏了,谁知道有没有人在偷听我们说话呢!还是先搞清楚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吧。”
我摸索着走起来。走了五步,我碰到一堵铁墙,是用铆钉铆起来的钢板。然后,我转身撞上了一张木桌子,桌边放有几张方凳。这间监狱的地板上铺着厚厚的麻垫子,走起来听不到一点脚步声。光光的墙壁上没有任何门窗的痕迹。康塞尔从相反的方向走过来,碰到了我,我们回到这舱房的中间,它大约长二十英尺,宽十英尺。至于高度,尼德·兰身材虽高,也碰不到顶。
半个钟头过去了,我们的情形一点没有改变。就在这时候,我们眼前的黑暗忽然退去,转变为耀眼的光明。我们的牢房突然明亮了,就是说,房中突然充满了十分强烈的发光物质,让我一开始难以忍受。我认出来,这雪白而强烈的光就是潜水艇周围磷光似的绚丽电光。我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又睁开,我看见光线是从装在舱顶上的一个半透明的半球体中发出来的。
“终于!我们能看清楚了!”尼德·兰喊道,他手持匕首,摆出防卫的姿势。
“是的,”我回答,同时提出相反的意见,“不过我们的处境还是不甚明朗。”
“先生请耐心些。”康塞尔冷静地说。
舱房突然明亮,正好使我可以仔细查看里面的环境。房中只有一张桌子和五个凳子。看不见门户,想必是密封门。耳朵听不到任何声响,船上似乎一片死寂。它是在行驶呢,停在海面上呢,还是在海底下呢?我无法猜测。
不过,那个发光的球体总不会无缘无故地亮起来。我估计船上很快就会有人过来。如果他们把我们忘记了,是不会让这黑牢亮起来的。
我果然没有想错。不久,门闩响动,门开了,走进来两个人。
一个身材短小,肌肉发达,肩膀宽阔,四肢发达,他有着壮硕的头颅和蓬松的黑发,胡须浓密,眼光犀利,浑身带有法国普罗旺斯人所特有的那种地中海的活力。狄德罗说得很对,他认为人的动作是富于隐喻的,这个小个子正是这句话活生生的例证。可以感觉到,在他平常的语言中,一定充满了各种修辞学上的拟人、换喻和换置等方法。当然我并没有机会证实这一点,因为他对我讲的是一种奇怪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
第二个人更值得详细地描述一番。格拉蒂奥莱 或恩格尔的门徒会从他的容貌里看到一本打开的书。我毫不犹豫就看出这个人的主要特点:自信,因为他的头高昂地摆在两肩形成的弧线中,他那漆黑的眼睛打量起人来带着冰冷的信心;镇定,因为他的肤色苍白而不带颜色,表示他血流稳定;刚毅,这从他眉头肌肉的迅速收缩看出来;最后,勇敢,因为他呼吸深沉,表明他活力充沛。
或恩格尔的门徒会从他的容貌里看到一本打开的书。我毫不犹豫就看出这个人的主要特点:自信,因为他的头高昂地摆在两肩形成的弧线中,他那漆黑的眼睛打量起人来带着冰冷的信心;镇定,因为他的肤色苍白而不带颜色,表示他血流稳定;刚毅,这从他眉头肌肉的迅速收缩看出来;最后,勇敢,因为他呼吸深沉,表明他活力充沛。
我还要说,这个人的样子很高傲,他坚定、冷静的眼光似乎反映出高深的思想。从他整体样貌来看,从他的举止和表情的一致性来看,根据相面学的说法,他应该是个直率的人。
有他在,我不由地放下心来,觉得我们的会谈将很顺利。
这个人有三十五岁还是五十岁,我不能确定。他身材高大,前额宽阔,鼻梁挺直,嘴唇轮廓分明,牙齿齐整,两手细腻而修长,用手相学的话来说,特别“有灵气”,就是说,正好配得上一个富有激情的高尚灵魂。这人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值得赞赏的那类人。他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的两只眼睛,间距略大,因而视野开阔。这一特点在之后得到了证实,使他的眼力比尼德·兰的还要强上一倍。当这个人注视着一件东西的时候,他皱起眉毛,凑拢宽大的眼皮,让眼皮正好圈住瞳孔,使得视野的范围缩小,他就这么看着!这眼光真犀利!远方缩小的物件都被他放大了!他一眼就能把人的心底看穿!在我们看来是模糊的海波,他却能把海底深处看个明明白白!……
这两个陌生人,头上戴着海獭皮便帽,脚蹬海豹皮水靴,身上穿着特殊面料织就的衣服,剪裁贴身合体,动作起来又方便自如。
两人中高大的一位显然是这船上的首脑,他仔细地打量着我们,一句话也不说。然后他转过身,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跟同伴交谈起来。这是一种响亮、和谐、抑扬顿挫的语言,其中元音的声调好像变化很多。
他的同伴不住点头,不时蹦出几个我们完全听不懂的词语。然后他拿眼光打量我,好像直接在向我问话。
我用纯正的法语回答他,说我不懂他的话;但他似乎不懂我在说什么,这情形真是十分尴尬。
“先生讲讲我们的经过吧。”康塞尔对我说,“这两位先生没准能听懂一些!”
我重新讲述我们的遭遇,一字一顿,一点细节都没有遗漏。我说出我们的姓名和身份,然后作了正式介绍:阿罗纳克斯教授,他的仆人康塞尔,鱼叉手尼德·兰师傅。
这个眼睛温和又镇定的人静静地听着,甚至说得上彬彬有礼,十分专注。但他的脸上没有露出丝毫迹象表明他听懂了我的故事。当我说完之后,他仍旧一言不发。
现在只有再用英语试试。也许我们可以用这种现在很通行的语言进行交流。我懂英语和德语,看书没有问题,可是讲得不太地道。但是,现在无论如何要使人家听懂我们。
“来吧,现在轮到您了,”我对鱼叉手说,“尼德·兰师傅,请您把盎格鲁-撒克逊人说的地道英语亮出来。您可得想法儿比我幸运一些。”
尼德并不推脱,他把我讲过的故事又讲了一遍,他说的我差不多都听得懂。内容一样,但形式不同了。加拿大人由于性格使然,说话时很激动。他愤愤地抱怨,说把我们关在这里是蔑视人权,质问人家凭什么法律把我们扣留起来,他援引《人身保护法》的条文,威胁要对非法羁禁他的人提起控诉。他全身激动,手舞足蹈,大声叫喊,最后,他用富于表情的手势,让对方明白,我们快要饿死了。
这可是真话,但我们差不多完全忘记自己饿了。
令鱼叉手吃惊的是,他的话跟我说的一样,好像也没有让对方听懂。这两个人连眉头也没有皱一皱。很明显,他们既不懂得阿拉戈的语言,也不懂得法拉第的语言。
我们所有的语言资源都拿出来了,可是一点用都没有。我犯了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康塞尔对我说:
“如果先生允许的活,我现在用德语来讲一讲。”
“什么!你会说德语?”我叫道。
“就跟普通弗兰德人一样。这不至于使先生不高兴吧。”
“正相反,我很高兴。说吧,好小伙子。”
康塞尔用镇定的语调,将我们的前情后果作了第三次叙述。可是,不管叙述人怎样遣词造句,音调怎样和谐动听,讲德语还是无济于事。
最后,别无他法,我只得极力搜罗我早年所学过的语言,开始拿拉丁语来讲述我们的遭遇。西塞罗 听了,可能要塞住耳朵,把我赶到厨房里去。可是,我总算勉强对付着说完了。但结果还是白费。
听了,可能要塞住耳朵,把我赶到厨房里去。可是,我总算勉强对付着说完了。但结果还是白费。
我们最后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两个陌生人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交换了几句言辞,然后就走开了,连全世界通用的使人安心的手势也没对我们做一下。门又关上了。
“太无耻了!”尼德·兰喊道,他是第二十次发怒了,“怎么!我们给这些混蛋说法语、英语、德语、拉丁语,可是就没有一个人懂得礼数回我们一句!”
“尼德,安静些,”我对火冒三丈的鱼叉手说,“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您知道,教授先生,”我们那好动肝火的同伴答道,“我们难道就活活饿死在这铁笼子里了吗?”
“算了吧!”康塞尔说,“想开一些,我们还可以支持很久!”
“朋友们,”我说,“不要失望。比这更糟糕的情况我们也经历过。你们先别忙,别急着给这船的船长和船员们下什么定论。”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尼德·兰回道,“这就是一帮混蛋……”
“什么国家的呢?”
“混蛋国的!”
“我的好尼德,这个国家在地图上还没有标出来呢,我承认这两个人的国籍很难断定!他们不是英国人,不是法国人,不是德国人,我们能肯定的只有这一点。然而,我倒是认为,这个船长和他的助手是生活在低纬度地带的人。他们身上带有南方人的特点。但他们是西班牙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还是印度人?他们的身型不容许我妄下判断。至于他们的语言,真是完全听不懂啊。”
“这就是不懂得各种语言的麻烦了,”康塞尔答,“或者说,世界上没有统一的语言真不方便!”
“有什么用呢!”尼德·兰答,“你们没有看见吗?这些人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专门就是为了叫好人没法向他们要饭吃!但是,在地球上随便哪个国家,张开嘴,动动下巴,牙齿和嘴唇吧唧一下,这意思难道还不明白吗?不管在魁北克,在波莫图群岛,在巴黎或者世界另一端的城市,这不就是说:我饿了,给我东西吃吗!”
“唉!”康塞尔叹口气,“还真有那么笨的人!”
他话音未落,房门开了,进来一个侍者。他给我们送来衣服,有海上穿的上衣和短裤,是用我不认得的什么材料做的。我赶快拿来穿上,我的同伴们也跟着我穿了起来。
这时候,沉默的侍者,可能是聋哑人,已经铺好桌子,把三份餐具放在桌上。
“这才像话。”康塞尔说,“这是个好兆头。”
“哼!”鱼叉手愤愤地说,“这鬼地方有什么可吃的?无非是海龟肝、鲨鱼里脊、海狗排罢了!”
“且瞧瞧看!”康塞尔说。
饭菜用银罩子盖着,两边对称地在桌布上摆好。我们在饭桌前入座。很显然,我们是在跟有教养的人打交道。如果没有那照耀着我们的电光,我简直要以为自己是在利物浦的阿德尔菲大饭店,或者在巴黎的大饭店里。不过我得说一句,面包和酒完全没有。水很新鲜、纯净,但不过是水——并不是尼德·兰爱喝的。在端上来的肉菜中间,有几种我认得是经过了精心烹制的鱼;但有几盘菜,口味绝佳,但我却说不出名字来,甚至连荤菜还是素菜都说不上来。至于餐具,甚是精美,品位上乘。每一件餐具,匙子、叉子、刀、盘,上面都有一个字母,字母周围有一句题词,我且照抄如下:

动中之动!这句题词用在这只潜水艇上真是再贴切不过。字母“N”大约就是在海底下发号施令的那位神秘人物姓氏开头的第一个字母!
尼德·兰和康塞尔并没有想这么多。他们狼吞虎咽,我立刻也学起他们的样子。此外,我对于我们的命运也放心了,据我看来,很明显,我们的主人没有让我们饿死的意思。
可是,什么事都有头有尾,一切都会过去,就连饿着肚子十五小时没吃饭这样的事也会有终结。现在我们的肚子装满了,又迫切地感到困了。我们跟死亡搏斗了一夜,这也是很自然的反应。
“说真的,我真想睡个好觉。”康塞尔说。
“我也困得不行!”尼德·兰答道。
我的两个同伴躺在舱房的地毯上,不久便酣然入睡了。
我同样被困意所纠缠,可是还是挣扎了一会儿。很多思虑涌上心头,很多问题塞满了我的脑子,找不到答案,很多的景象浮现在眼前!我们在哪儿?是什么奇异的力量把我们带到这儿的?我感到——不如说我以为感到,这船正向海底最深的地方下潜。噩梦不断纠缠着我。我在这神秘的避难所里,窥见一大群陌生的动物,这只潜水艇似乎是它们的同类,它跟它们一样活着,游动着,和它们一样可怕!……然后,我的脑子安静下来,我的幻想融化在朦胧的睡意之中,不久也沉沉地睡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