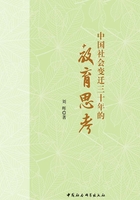
三 建构多元课程体系的几点设想
所谓多元课程体系是针对上述的全国划一、自上而下的指令性“一元”课程体系而言的,其含义是指以各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差异性为基点,具有广泛社会适应性和变通能力的课程制度。笔者认为此种课程体系的建立应首先以普通中等学校为目标,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赋予地方制订课程计划的一定权限。
我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客观上排斥中央制订“一刀切”的课程计划,而要求增大地方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设置课程的主动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地放任自流,形成“一盘散沙”,而是在中央宏观指导下,地方参照国家拟出的普通中学的基础必修课和要达到的基础学力(不是文凭主义的“学历”)标准,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制定切合地方特色的课程。打破自上而下的“越俎代庖”局面,强化地方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将会使学校课程日趋合理,呈现出开放和动态机制,有利于打破升学教育的沉闷状态,培养符合地方需要的适销对路人才。
这方面做法,有许多国家的经验可供我们参考,其中美国可说是典型。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不但各州之间学校的课程设置彼此不同,一州内各校之间的课程也有差异。美国公立中小学的课程,是由州一级政府和州以下的地方政府联合制定的,私立学校的课程可以按照政府的标准,自行制定。这使学校课程与当地情况和学生的需要紧密结合。我国现阶段,可逐步以宏观指导代替指令性课程计划,将课程设置权过渡给由省与地方各部门组成的“课程计划委员会”,并以“学校法”的形式确保地方课程的编订与实施。
与此同时,强化地方各界与学校课程设计的参与意识和学校本身对课程建设的责任感。课程往往是社会各界对教育的期望和要求的中介环节,合理的课程应是政府决策者、教育专家与社会各界广泛交流协商的产物。在国外,参与课程制定的人员是相当广泛的,有政府机构人员、教育顾问、学校行政领导、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社会集团。在我国,选择参与制定课程人员的标准应视各地具体情况来定。普通中学课程的设置需要将基础素质、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人才的统一性与地方经济文化特点对劳动后备军要求的特殊性纳于一体之中,这是影响课程因素的复杂性所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各地对其所辖区内学校的课程必须有比现在更大的发言权,这是建构多元课程体系的关键所在。
第二,调整普通中学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
查阅从1950年到1981年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中学教学计划》,可以发现规定的必修课程几乎占满了学校的课程表[7]。这使开设符合地方特点的选修课的想法化为乌有。因此,压缩统一的必修课,增加选修课,是现实课程体系转轨的实际步骤。
由于“大一统”的思想一直在课程领域居主导地位,选修课问题长期受到忽视。1963年教育部颁发的教学计划首次提出在高三年级设置选修课,但仅有少数学校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1981年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再次确定要在高中开设选修课,迄今为止,这一计划仍停留在部分重点中学的实验阶段,而未在普通中学全面铺开。现在,当务之急是使各地各界认识到加开选修课是为了实现课程体系转移到适应地方发展的轨道上来;与此同时,要探索普中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并尽快推广实施。
关于选修课与必修课的比例,苏联国家教委最近的规定是,“为保证实现统一要求而开设的必修学科应占课时的75%—80%,其余时间用于选修科”[8]。在法国,“从1973年起中等学校中实施10%的自由支配课程。目的是使各学校不至于被动地对待中央规定的课程,而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根据各地特点与学校规模,创造性地提出教育目标”[9]。在美国,“十三个州规定,中学毕业所需要学习的课程中,学生选修比重可达50%,甚至50%以上”[10]。如何根据我们的国情厘定这一比例,是需要广泛试验和深入探讨的。我以为这如同分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一样,应视各地具体情况分步实行。城市与农村中学的必修课、选修课比例应有差别,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的比例亦有殊异。唯有如此,方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各地的差异性,使课程与地方发展特点相吻合。
第三,根据普通中学的不同目标设计课程。
改变普通中学以升学为目标的状况已成为各界人士的共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普通中学担负着为社会输送劳动后备军的重任,这要求普通中学必须紧紧把握当地经济发展特点,调整培养目标和课程结构,办出各自的特色来。条件好的普通中学可以把升学作为主要目标,条件差的普中,特别是农村普中应针对当地特点,以培养促进地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适用人才为主要目标。
据此,可以根据不同普通中学的侧重目标来设计课程。如城市一般普通中学,应加强职业技术、职业咨询、就业指导等方面的课程,内容可遵循当地产业结构,或以工业、或以商业为方向进行设计;农村普中则依据当地农、林、牧、副、渔和乡镇企业的情况,以学生面临的社会生活为目标安排课程。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矛盾;另一方面可以弥补职业教育的不足为地方输送对口人才,还可以提高通普中学的办学社会效益,增强地方对教育投入的信心。
总之,把握影响课程的错综复杂的因素,建设符合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特点的课程体系需要一个长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可以确信,一旦我们冲破了大一统课程体系的桎梏,迈出了全面改革课程的脚步,教育必定会出现新的勃勃生机。
(原载《江苏教育研究》1990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1990年第5期全文转载。)
[1] 《教育部关于实行全日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的通知》(1963年7月31日)。
[2] 见《中国教育报》1986年10月25日。
[3] 见《光明日报》1987年8月12日。
[4] 参阅丹尼斯·劳顿等:《课程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5] 参阅丹尼斯·劳顿等:《课程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6] 张景仪:《农村中学办学的社会效益亟待提高》,《教育研究》1986年第10期。
[7] 参阅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第九卷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38页。
[8] 钟启泉:《现代课程编制的若干问题》,《教育研究》1986年第5期。
[9] 钟启泉:《现代课程编制的若干问题》,《教育研究》1986年第5期。
[10] 《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