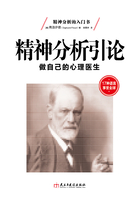
第4章 过失是有意义的
在上次讲演时,我们只是讨论了过失本身,而没有涉及过失与被干涉的有意动作的关系;大家知道,拿某些例子来说,过失好像有意义。假如过失有意义这个说法能在更大范围上成立,那么研究过失意义的研究会比研究引起过失的条件来得更加有趣。
心理过程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首先必须要有一致的观点。
我认为,意义即它所借以表示的“意向”(intention),或是在心理程序中所占据的地位。就我们所举的大部分实例来说,“意义”一词皆可用“意向”和“倾向”(tendency)等词来替代。
到底是因为表现,还是因为有意夸大过失的意义,才让我们认为过失之中存在意向呢?
现在我们仍以口误举例,仔细观察更多的表现,就能明白这些实例都有明显的意义或意向,尤其是那些把自己所要说的话说反了的例子。比如,议会议长在宣布开会时说成了散会,很明显,其意义和意向就是他想要闭会。或许你认为“他自己这么说的”,我们不过是抓住了他的要害。大家最好不要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你以为他要的是开会而不是闭会,以为他的意向就是要说开会的。如果你们这样认为,就忘记了我们原意是要“只讨论过失”,而忽略了过失和它所扰乱的意向的关系,由此,你们就会犯逻辑上“窃取论点”(beging the question)的错误,而随意处理其所讨论的全部问题。
在其他实例中,口误虽不完全表示相反的意思,却仍表示出来一种矛盾的思想,比如“我不愿(geneigt)估量前任教授的优点”中的“不愿”虽并非“不配”(geaignet)的反面,但这句话的意义却与说者应取的态度大相矛盾了。
还有些实例,口误表示的除了本身的意义外还有一个第二意义,因此错句就像是好几句的凝缩。比如那个刚愎的女人说:“我选择的东西他只要吃点喝点就行了。”她的言外之意是说:“他虽然能支配自己的饮食,但是他要什么又有什么用呢?只有我才可以代他选择食品呢?”口误常给人这种凝缩的感觉。
又比如,一位解剖学教授在讲演完鼻腔的构造之后,问学生们是否明白了,学生们回答明白了之后,他却说道:“真不可思议,要知道充分了解鼻腔解剖的人,即使在几百万人的城市中,也只一指可数……不,不,我的意思是屈指可数。”仔细品读就会发现,他的意思是,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只有他一个人而已。
一些口误的实例可以明显看出其意义,但还有一些例子的意义是不易了解的。比如,错读了专有名词,或乱发些无意义的语音等,都是比较常见的实例。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解答“过失到底是否全部有意义”这个问题了。其实如果更仔细地研究这些例子也能揭露一个事实,就是这种错误是很容易看出端倪的;说实话,这些看起来很难理解的例子与前面比较容易懂得的例子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比如,有人问马的主人,马怎么样了,马主人回答:“啊!它可‘惨过’了(stad)——可能只有一个月可活了。”“It may take another month。”其实他想说的是这是一件惨事(a sad busines),但他把sad(惨)和take(过)糅合到一起,结果就成了“惨过”(stad)。
还有一个人在谈及一件引人非议的事时说:“于是某些事实又‘发龊’(refilled)了”。他的意思是要说这些事实是“龌龊”的,结果把“发现”(revealed)和“龌龊”(filthy)合而为一变成了“发龊”(refilled)。
大家还记得有个少年要“送辱”一个女孩的例子吗。我们曾将此二字分解成“护送”和“侮辱”,现在不需要证据便清楚这个分析是可信的了。
从这些实例可以看出,它们即使表达的意思不太明白,却都能解释为是两种不一样的说话意向彼此混合或冲突。不同的是,在前面一组的“口误”中,一个意向排斥了其他意向,说话者把所要表达的话说反了;后面一组则是一个意向歪曲或更改了其他意向,于是造成了一种有意义的或无意义的混合字形。
我想现在大家已经了解了大部分口误的秘密了。如果弄明白了这一层,那么之前不能理解的另一组口误也就自然能理解了。比如变换名词的形式虽并非经常因为两种相似的名词的竞争所致,但第二个意向还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非口误所致的名词的变式也是比较是常见的;这些变式主要是为了某一人名。这种方式有些侮辱人的意味,有教养的人员一般不愿采用,但又不愿意放弃,因此它常被伪装成笑话,一种比较下流的笑话。举一个粗俗的例子,法国总统Poincaré曾被歪曲为“Schweinskaré”(猪样的)。进一步讲,这种讥讽的意向也能够隐匿于因口误而造成的人名变式之后。如果这个假定成立,那么因口误而造成的滑稽可笑的变名便可以这样解释。比如,议会议员称别人是“中央地狱里的名誉会员”(honourable member for Central Hell),会场里安静的气氛立刻就会被打乱,因为这个字眼可以唤起一种可笑而不快的形象。由于这些变式带有讥讽的味道,所以我们能够断定它背后还有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你别被骗了。我这个字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谁乱说,就让他下地狱!”
其他的口误,如把完全无害的字变成粗俗污秽的字也同样适用于这样的解释。
一些人为了娱乐,有故意将无害的字说成粗野的字的这个倾向。有人把它看成是滑稽的表现,但实际上,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例子,就不免会提出疑问,这到底是有意的笑话还是无意的口误。
关于过失之谜,我们似乎已经揭开了一些谜底。过失的发生并非没有原因,它是一项重要的心理活动。两种意向同时发生,或互相干涉,导致了过失的发生,而且这个过失是有意义的。我知道大家心中还有一些疑问,当然,我们必须要先解决了这些难题,这样你们才会相信我所说的。我当然不愿意用草率的结论欺骗你们,还是让我们冷静地依次解决每一个问题吧。
你们可能会有怎样的疑问呢?第一个问题,你们可能会问我这个解释是用来说明一切口误的事例,还是只能说明某些少数的事例?第二个问题,这个答案能否适用于许多种类的过失,如误读、误写、遗忘及做错事和丢失东西等呢?第三个问题,疲倦、兴奋、心不在焉及无法集中注意力等因素究竟在过失心理学中占何种地位呢?另外,过失中的两种意向往往是互相竞争的,有一种常常是明显的,另一种则不一定,那么我们究竟怎样去揣知那种不明显的意义呢?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之外,你们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假如没有,那我可要提问了。我要提醒大家,我们讨论过失,不只是为了要了解过失,而是要进一步去了解精神分析的要义。因此,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究竟是哪种目的或倾向在干涉其他意向呢?而干涉与被干涉的倾向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呢?过失的谜一旦解决,便又开始了进一步的努力。
难道这就是一切口误的解释吗?
我想说,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如果研究一个口误的例子,便能得到这个结论。不过,我们可不能证明所有口误都受到这个法则的支配。但是,即使我们所解释的口误的例子只是一小部分,却也能够有效地说明精神分析的结论;何况这些口误还不只是一小部分的事例。
关于这个解释可否适用于其他种类的过失,我们也能先给予肯定的答复。以后再讨论笔误、做错事等例子时,大家也不会再对此有疑问。不过为了方便叙述,我们先充分地研究了口误之后再来说这个问题。
像循环系统的扰乱、疲倦、兴奋、分心及注意力不集中等某些学者比较看重的因素对我们说来有何种意义呢?假如过失的心理机制如上所述,这个问题的答案则会更彻底。当然我不否认这些因素。说实话,精神分析只是要将过去已经说过的话加入一些新鲜的材料,而对于其他各方面的主张基本上是没有争议的。有时候,之前被忽视现在却被精神分析补加的正是那事件中最重要的部分。那些由于小病、循环系统的紊乱和疲倦等发生的生理倾向,也会引起口误;这在日常生活中是值得相信的。可是承认这些到底能解释什么呢?答案是,它们并非过失的必要条件。即使是在完全健康和正常的情形之下,也能产生口误。因此,身体的因素只算是补充的,只能给产生口误的特殊精神机制提供便利。我过去用过这样一个比喻,用在这里也很合适。这就好比在黑夜里我在一处僻静的地方散步,忽然流氓出现了,把我的金钱、手表都抢去了,而由于黑暗我根本没看清强盗的面孔。我向警察局控诉说:“是僻静和黑暗抢去了我的钱物。”警察局长或许会告诉我说:“从事实上来说,你有些太相信极端的机械观点了。你应该控诉的是有一个没看清的窃贼趁黑夜和僻静胆大作案,是他将你的钱物劫去。在我看来,首要的事是捉贼。因为贼捉到了才有可能取还赃物。”
兴奋、分心、注意力不集中等心理生理的原因,只是几个名词而已,根本算不上解释。也就是说,它们是帘子,我们必须揭开帘子看看才行。我们应该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了兴奋或分心?音值、字的类同、某些字共有的联想等影响因素为过失指出一条可以发泄的道路,因此它们是重要的。但是即使前面有一条路,就能保证我一定走这条路吗?当然不能,我还需要走这条路的理由,让我不得不循着这条路走。因此,这些音值和字的联想正如身体状况一般,只是诱发口误的原因,不能作为口误的真正解释。我讲演时说的无数词语中就有许多字和别的字声音很像,或与其相反的意思或公用的表示有密切的联想,但我却很少用错。
哲学家冯特认为意向本身如果因身体的疲倦导致偏向于联想,便容易引起口误。这看起来有些道理,但却不免与经验相抵触,因为从大多数例子来看,口误并没有什么身体的或联想的原因。
我对你们的下一个问题特别感兴趣:究竟用什么方法来测定两种互相干涉的倾向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被干涉的倾向是比较容易被认识的,犯错误的人知道并且承认它。令人怀疑的是另一种,即所谓干涉的倾向。大家应该记得,我说过这个倾向偶尔也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有认错的勇气,便能在错误的结果之中看出这个倾向的性质。
议长要宣布开会,但他却把意思说反了,而事实上他骨子里是想要闭会。看得清楚明白,根本无须解释。其他实例则不然,干涉的倾向只是让原来的倾向略有改变,而没有将自己的意思充分暴露出来,那么我们究竟用何种方法来探得这个变式中那种干涉倾向呢?
在某些例子中,我们可以采用稳便而简单的方法,即用你测定被干涉的倾向的方法来测定干涉的倾向。我们可以查问,让说话者恢复他原来所要说的字。
“啊!它可惨过(stad)——不,它可再过一个月。”他也可以补充说明干涉的倾向。我们可以问他为什么先说“惨过”呢?
他说,“我本来想说的是‘这是件惨事’。”
就另一例来说,说话者用了“发龊”两个字,他表示他本想说这是一件龌龊的事,可是他控制住了自己,用另一种表示取而代之了。其干涉的倾向正如被干涉的倾向那样清晰可见。
这些实例的发生和解释都并非我或帮助我的人编造出来的,我是有目的选用它们。我们必须问那说话者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错误,看他是否可以解释。如果没有这样问,他可能就会轻易放过而不会去寻找答案。不过一旦追问他,他就会将他所想到的第一个念头说出来。事实上,我们所要讨论的精神分析的雏形就来自这个小小的帮助和其结果。
不过我担心大家才了解精神分析的概念,可能会对它产生一种本能的抵抗。大家不是竭力想要抗议,说犯错误的人告诉我们的话不就是可靠的证据吗?你可能认为他为了要满足你要求解释的希望,而将他所想到的第一个念头告诉了你。至于是不是确实因为这样引起了这个错误,大家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它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不是,他或许还想得到一种别的解释。
显然,你们是太小瞧心理事实了。如果有人拿某一物质去做化学分析,来测定其中某一成分的重量,然后从这个测出的重量得到某一结论,你认为一个化学家会因为害怕这一分离出来的物质可能会有其他重量,而去怀疑这个结论吗?不管是谁都知道,除了这个重量,不会有其他的。所以说,他一定会在这一基础上毫不犹豫地建立进一步的结论。那么关于心理事实,说某人在受盘问时想到这个观念而没有想到别的观念,你们就不愿意轻易相信,总认为他可能还有别的念头,事实上,这完全是你们不愿放弃自己心中的心理自由的幻觉。关于这一点,很抱歉,我不能苟同大家的意见。
现在你们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抗议了,认为:“我们知道精神分析有一种特长的技术,可以使被分析者解决精神分析的问题。比如在餐桌上的那个让请大家起来打嗝以祝主人健康的客人,你说他干涉的倾向是想要取笑,可是这个倾向与这个对主人心怀尊敬的客人的倾向又是互相冲突的。不过,这只是你的解释,你的观察和这个口误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你去征求那位说错话者的意见,他不但不同意他有污辱的意思,而且还会强烈地否认这个意思。为何当别人坚决否认时,你对这个无法证明的解释还抓着不放呢?”
没错,这次你们的辩驳可以说是很有力了。我能够想象那位不相识的客人,他可能是那位首席客人的助理员,也可能是一位年轻的讲师,或者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如果我告诉他,他这样对他的领导有点有失尊敬。那么一场吵闹便会发生了,他会不耐烦起来,生气地对我说:“你管得也太多了,你要是再多说,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要知道你的怀疑足以破坏我一生的事业。我是因为说了两次auf,才误把anstossen说成了aufsatossen。这是梅林格所谓‘语音持续’的例子,背后绝对没有其他恶意。你知道这一点那便够了。”
这确实是一个有力的抗议。我知道我们不应该再怀疑他,可是他在说自己的错误没有恶意的时候,是不是反应太强烈了呢?他完全不必因纯学术的研究而大发雷霆,这一点你们也许会同意,但你们仍会觉得他自己知道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可是他到底知道吗?恐怕这还是一个疑问吧。
你千万不要以为现在已将我驳倒了。
你们可能会说:“这是你的技术问题。假如说错话的人的解释与你的观点相一致,那么你便可以宣告他是本问题的最后证人!但如果他所说的和你的观点不一致,你可以马上宣告他说的话毫无根据,要大家不必相信。”
这的确是个好方法。不过,我可以举一个类似的例子。比如在法庭上,被告认罪,法官便相信他;被告不认罪,法官就不相信。一旦不是这样,法律便不能施行了;即使有时候也存在过失,但大家总该承认,这个法律制度是行之有效的。
你可能会说“嗯,难道你是法官吗?犯错误的人是你的被告吗?难道口误就是罪过吗?”关于这个比喻,大家其实没必要予以驳斥。事实上,关于过失的问题,我们所持的意见是不同的,但我现在还不知道如何去和解。因此,我才提出法官和罪犯的比喻充当暂时和解的基础。
大家应该承认,如果被分析者承认了过失的意义,那么这个过失的意义就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我承认假如被分析者不肯直说,或者根本不见面,那么就得不到直接的证据,我们就不得不像法官审案那样,利用其他证据来进行推断。在法庭中判罪,为了需要,是可以采用间接证据的。精神分析虽然没有这种必要,但也可以考虑采用这种方法。假如你相信科学只会有已经确定证实的命题,那你可能有所误解了。而且如果你对科学做这样的要求,也不太公平。只有那些有权威欲的,想要以科学教条代替宗教教条的人才有这样的要求。事实上,科学作为教条只有极少数明了的原则,主要是那些有不同程度的几率的陈述。科学家有个特点,即可以满足于接近真理的东西,即使最后缺乏有力的证明,他也能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不过,如果被分析者不想解释过失的意义,我们要到哪里去寻找解释的起源和作为证据的资料呢?以下几种都可以作为来源:首先,可以借助那些非过失所产生的相似现象,比如一个人如果因错误而变式和因故意而变式是一样的,都暗含着取笑之意。其次,可借助引起过失的心理情境,犯错误者的性格和没有犯错误之前的情感,过失往往就是反应这些情感。通常来讲,我们以一般原则来寻求过失的意义,最初这只是一种揣测,使问题得以暂时解决,后来通过研究心理情境而求得证据。
有时,还需要在进行进一步研究过失的意义后,才能证实我们所猜测的对不对。以口误为例,虽然我举了好几个例子,但恐怕要说服你们也并不容易。其实,那位要“送辱”某女士的青年是很害羞的,而那位说自己的丈夫要吃喝她所选定的食品的夫人则可以看出是位治家很严的妇女。我再举一个例子,某俱乐部开会,一个青年会员演说时猛烈攻击他人,他称委员会的成员为“Lenders of the Committee”(意即委员会中的放债者)他用Lenders(放债者)代替了“members”(意即委员)。
我们可以猜想出,他在攻击别人时脑子里正活跃着一些与放债(lending)有关的干涉倾向。事实上,有人告诉我这位演说家经常在金钱上遇到困难,那时正想借债。因此其干涉的倾向暗含着这样一种意思:“你在抗议时请慎重一些吧!这些人都是你想要向他们借钱的人啊。”
其实,像这样的间接实例,我可以提供给你们很多。如果一个人很努力还无法记起一个熟悉的人的名字,那么我们就能够推测出他对这个人一定没有什么好感,因此不愿去回忆。假如我们记得这一点,那我们便可以讨论下面几个过失的心理情境了。
Y先生爱上了某女士,但这位女士对他没有什么兴趣,不久后,这个女士和X先生结婚了。Y先生早就认识X先生,并与他在业务上有联系,可是现在他却经常忘记X先生的名字,以至于每当写信给他的时候都不得不向别人询问他的名字。很显然,Y先生是不想记起这位幸运的情敌,要将他永远忘掉。
又如,某女士在和医生谈及一个他们所共同认识的女朋友时,用的是这位女友没有出嫁以前的姓氏,她承认自己十分反对这个婚事,并且厌恶她现在的丈夫,所以忘记了她结婚以后的姓氏。
关于专有名词的遗忘,我们以后再详细讨论,我们现在还是先关注引起遗忘的心理情境。之所以发生“决心”的遗忘可能是因为一种相反的情感阻止了“决心”的实行。不光精神分析家这样认为,其实一般人在日常事务中也常常这样,只是在心理上不肯承认而已。
假如一个施恩者忘记了求恩者的请求,那么施恩者即使道歉也仍会让求恩者感到怨恨或不快。因为在求恩者看来,既然施恩者答应了他的请求,就应该去做,但是很显然,施恩者太忽视他了,而没有去实践。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日常生活中,遗忘有时也可能会引起怨恨,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者和一般人似乎想法一致。试想一下,一女主人看见客人来了,却说:“没想到你今天来了?我早就忘记了今天的约会了。”客人会是什么感觉。
又如,一青年假如对他的恋人说自己已将他们上次所定的约会完全忘记了,会是什么结果。事实上,这个青年是决不会承认的,他会在一瞬间找出各种理由来说明他为何没有践约赴会,为何一直到现在都没给她消息。大家都十分清楚,在军队中,遗忘是不能作为借口来求得宽恕而免于刑罚的。关于这个制度,大家都承认它是公允的。那么,每个人都会承认某种过失是有意义的,并知道这意义是什么了。可是他们为何不将它推之于其他过失并公然承认它呢?这个问题当然有它自己的答案。
遗忘“决心”的意义在普通人心里已经是被认可的了,难怪作家们常用这种过失来表示相类似的意义。大家是否读过萧伯纳的《凯撒与克利奥佩特拉》,可还记得在最后一幕离场时,凯撒因为觉得自己忘记了一件想要做的事情,而感到十分不安。后来,他才想起这件事是没有与克利奥佩特拉话别。作者想通过这个文学的技巧来表明凯撒的自大之感,事实上凯撒并没有这种感觉,也没有这种渴望。由历史可知,凯撒曾带克利奥佩特拉一起去罗马,并且凯撒被刺的时候,克利奥佩特拉和她的小孩子还住在罗马,直到后来,他们才离城逃亡。
这些遗忘“决心”的例子的意义都很容易看得出来,因此对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多大用处。我们的目的是要从心理情境中寻找过失意义的线索。所以,我们现在来讨论一种不是很容易了解的过失,也就是关于物件的遗失。在你们眼里遗失物件是非常令人烦恼的事情,因此很难相信遗失物件是有目的的,然而实际上这种例子非常多。有一个青年弄丢了一支他非常喜爱的铅笔。几天前,他曾收到他的姐夫寄来的一封信,信的结尾这样写道:“我现在即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鼓励你四处鬼混。”
原来这支铅笔是他姐夫送给他的礼物。假如事先没有发生这个事件,我们当然不会说他弄丢东西背后有遗弃礼物的意思。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一个人遗失物件,可能是因为与赠物者吵嘴而不愿记起他,或者因为厌恶旧物,试图找个借口换得一个更新更好的物品。又或者将物件失落、损坏或毁坏,也往往能够达到相类似的目的。一个小孩在生日的前一天弄坏了自己的表、书包等,你能说这是偶然发生的事件吗?
一个人曾经因为丢失物件而感到不安,那么他一定不愿相信这个行为是有意为之的。不过有时我们也能通过丢失物件的情境探知一种暂时的或永远的遗弃之意。下面的例子也许最能说明这个观点。
有一个青年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我和我的妻子之间有很多误会。虽然我知道她有着很好的美德,但我们却缺乏一定的感情,我一直认为她过于冷淡。有一天她散步回来,为我买了一本书,她以为我看到这本书会高兴一些。我很感谢她对我的关心,并答应会读它,可是我把它放在杂物中,就怎么也找不到了。几个月之后,我偶尔会想起这本书,可是依然找不到。大约半年后,我的母亲生病了。母亲的住处和我家相隔很远,但我的妻子却一直坚持去母亲身边看护她。通过母亲病重这件事,我看到了妻子的美德。一天夜里,我怀着满腔感激我妻子的热情回到家,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书桌面前打开了一个抽屉,结果我看到了那本屡寻而不可得的书。”
动机一旦消失,失物便找到了。
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不过我不想这么做。如果你们想知道,可以去看《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年初版),那本书里有很多关于过失的实例。这些实例都可以拿来证明相同的事实。从这些例子中,你们可以看出错误是有用意的,也能了解怎样从发生的情境中揣知或证实错误的意义。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征引,因为我们今天的目的是为了研究这些现象,以更好地掌握精神分析。我现在要说的只有两点:第一,是重复的和混合的过失;第二,以后的事实可以证明我们的解释。
重复的和混合的过失最能够代表过失。假如我们只证明过失是有意义的,那么举这些过失足矣,因为就算是极愚笨的人也能明白它们的意义,即使是吹毛求疵的人也会信而不疑。由错误而导致重复,从中可以看出它必有用意,并非事出无因。而一种过失转化为另一种过失,从中能够看出过失的要素:此要素并非过失的样式和其所用方法,而是利用过失去达到目的倾向。
我给大家举个重复遗忘的例子吧。琼斯写好了一封信,可是这封信放在在桌上好几天也没有寄出去。后来他决心寄出了,可是却忘了写收信人的姓名和住址,结果被退了回来。补填之后,再送到邮局去,结果这次又忘了贴邮票。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其实心里是不太想寄出此信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误取别人的东西之后又把东西弄丢了。一个女士和她的名画家姐夫同游罗马,身居罗马的德国人设盛宴款待这位名画家,并送了他一枚典雅的金质章,可是他并不看重这精致的赠品,这位女士为此而感到很不高兴。她在姐姐到达罗马后便回国了,结果打开行李时,发现自己竟然把那枚金质章带回来了,而她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带回的。她马上写信告诉姐夫,并说自己会在第二天将这枚金质章寄回去。可是到了第二天,金质章怎么也找不到了,以至于她不能如约寄还,于是她才知道自己犯下的过失其实是有用意的。事实上,她想要将这个艺术品据为己有。
我曾经讲过一个遗忘和过失相结合的例子。某人忘记了开会的事情,他告诫自己第二天一定不要忘记,可是当他第二天赴会的时候却记错了时间。有一个爱好文艺和科学的朋友以自己的经验给我讲了一个类似的例子。他说:“几年前,我被选为某一文学会的评议员,当时我想或许我有机会让我的剧本能在F戏院里公演,可是之后我却总是忘记去开会。在读到你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以后,我感到很自责,觉得他们帮不到我,我就不去开会,似乎有点太卑鄙了,于是我决定在下星期五无论如何也要记得去开会。我多次提醒自己,后来真的去了。但令我诧异的是,会场的门竟然是关着的,显然已经散会了。原来我把开会的日期记错了,那天已经是星期六了!”
我本想再举一些这样的例子,不过现在我还是应该继续往下讨论,让大家看一些需要将来去证实的例子。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这些实例的心理情境在当时是尚不可知或无法测定的。因此我们那时的解释也只能作为一种假说,没有太大的说服力。不过后来发生的另外一些事,能够用来证实以往的解释。
有一次,我在一对新婚夫妇家里做客,这位年轻的妻子笑着给我讲述她最近的一次经历,说她在度蜜月回来后的第一天,她的丈夫上班去了,她便邀请她的姐姐一起去买东西。在大街上,她忽然看见了一个男人,于是她碰了姐姐一下,说道:“看,那不是K先生吗?”原来那人正是刚刚和她结婚了几个星期的丈夫,可是她却忘记了自己和他结婚这件事。我听了她的讲述后,非常不安。结果几年以后,确实证实了我的揣测,这个婚姻有一个不幸的结局。
梅特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女士在她结婚的前一天,竟忘记了试穿婚纱,使得裁缝非常着急,她记起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结果她结婚后不久,她的丈夫就离开了她。梅特认为,这位女士遭到抛弃与她忘记试衣有着一定的联系。
我还知道另一个与丈夫离异的女人的故事。这位女士结婚后在金钱往来时签字还经常用她没有结婚前的签字,结果没过几年,她果然又回到小姐的身份了。还有几个别的女人,她们的婚姻结果也不是很好,这和她们在蜜月中遗失了她们的结婚戒指有一定的关系。
我这里还有一个结果较好的奇怪例子。德国有一个著名的化学家,他在结婚时竟然忘记了婚礼,没有到教堂去,反而走进了实验室。后来,他一直没有结婚。
你们可能觉得这些例子中出现的过失有一些预兆的迹象在里面。事实上,预兆确实就是过失,比如失足或跌跤,其他的预兆可以说是客观的事件而非主观的行动。不过大家或许不会相信,要决定某件事是属于第一种还是第二种,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主动的行为通常会伪装为一种被动的经验。
假如我们回顾已往的生活经验,肯定会说倘若当时我们有勇气和决心将一些小过失看成是一种预兆,并在它们还不明显时就把它们看成倾向的信号,那我们应该能够避免很多失望和苦恼。事实上,我们常缺乏这样的勇气和决心,以免有迷信之讥。事实上预兆也不一定都会变成现实,至于什么原因,我们的学说将会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