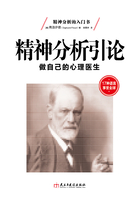
第3章 关于过失
现在,我们不再去假设而要从观察到的事实入手。我们可以选取一些我们经常遇到但却很少有人注意的现象,这些现象并不属于疾病的范畴,即使在健康人身上也时有发生,心理学上将这些现象称为过失行为。比如,口误、笔误、误读和误听等情况,就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当你想要向别人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想好的话说出口时却用错了词;在书写的时候,想写的是这个字,却鬼使神差地写成了另一个字;阅读文章时,读错了某个熟悉的字;听觉器官没有毛病,可是却听错了别人讲的话。
还有一些过失是由于人们暂时性的遗忘所导致的,比如突然忘记了一个熟悉之人的名字,或者忘记了自己所要去做的事情等。这些内容只是被暂时的遗忘,后来多半会自然而然地记起来。
不过,也有一些记忆不是暂时性的遗忘,而是永久性的遗忘,比如把某件东西放错了位置,后来再也找不到了。这种遗忘常常令我们感到惊异懊恼,甚至难于理解。还有一些过失,虽然也有暂时性,但却与此十分相似,比如有些人明明知道某事是不确定的,但有时候却会信以为真,像这样的现象不胜枚举。
像口误、笔误、误读、误听等过失名词在德文中都是以“ver”开头的,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但是,这些在生活中出现的种种过失往往是暂时的,不重要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就好像是遗失了某样根本不必在意的东西一样。因此,在许多人看来,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过失都是不值得研究的。
而我现在却要让大家来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或许你们会表现得不耐烦,并加以反对。你们可能会说:“这世界上值得解释的神秘玄奥的事情太多了,我们花那么多力气去研究这些无关重要的过失根本毫无意义。如果你们能够解释一个耳聪目明的人自称在白天能看见或听到一些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事物,或解释某人为何突然宣称自己正在遭受他最亲爱的人迫害,又或者可以用最巧妙的理由来证明一种就连一个小孩子都会感到荒谬的幻想,那人们可能就会更愿意重视精神分析了。可是假如精神分析只能解释一个演说家为何说错了字,或一个主妇为何弄丢了钥匙等琐碎小事,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那些更加重要的事情的研究上。”
我想说,大家不要急着下定论,这个批评其实是文不对题的。当然,我不能夸口说精神分析从来不做琐碎的事情,事实恰恰相反,精神分析所观察的材料常被其他科学讥讽为是琐碎、平凡和不重要的,甚至被说成是现象界里的废料。大家似乎都这么认为:凡是重大的事情就要有重要的表现。难道说,在某些情况下,重大的事情就不能借一些琐碎的事情表现出来吗?
这道理是很容易说明的。举个例子,假如你是一个未婚青年,对某个女孩子产生了好感,那么你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已经博得了她的欢心呢?难道一定要她明白地告诉你或给你热烈的拥抱吗?当然不是,你一定是从她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或和你握手的一瞬间就知道了。又比如,假如你是一名侦探,正在侦查一件谋杀案,在既无人证又无物证的情况下,你能指望罪犯会给你留下一张有他的姓名和地址的照片吗?你只能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因此,我们不能轻视那些看似微乎其微的符号,它们其实也是有很高价值的,通过这些信号我们或许能够发现重大的事情。你们认为生活中和科学上的大问题更容易引起我们的兴趣,我当然不反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们决定从事于研究重大问题,那也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你可能会不知道怎么着手下一步。就科学工作而言,如果你的面前有一条可以前行的路,那么你照着走下去就行了。
如果你不带任何偏见或成见,一直向前,或许就能借助事情之间的联系(包括小事和大事之间的联系),通过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幸运地从事大问题的研究工作。从这个观点来说,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对正常人也常常出现的小过失失去研究的兴趣。如果我现在问那些不懂精神分析的人如何来解释这些现象,我想他的回答肯定是:“这些小事根本不值得解释。”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难道他认为小事就不值得关注,就不能与其他事情发生因果联系吗?不管是谁,如果这样否认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就等于没有科学的宇宙观。即使是宗教观也不会如此荒谬,因为在宗教的教义中,如果不是上帝所愿,即使“一雀之微也不会无因落地”。假如我们的朋友知道这个道理,他一定不会坚持这个答案,他可能会说如果我去研究这些现象,一定会得到合理的解释。
那一定是由于轻微的机能错乱,或精神的松懈所致,这些情况都是可以找到的。一个人平常说话没有出现问题,但是现在却出错了,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处于疲倦或不舒服的状态;二是很兴奋;三是注意力集中在别处。要证实这些很容易:一个人在疲倦、头痛、周期性偏头痛时常会说错话或常常忘记了使用合适的名词,有很多人在偏头痛发作时甚至连专有名词都记不起来。
人处在兴奋状态时也常会用错字或做错事;注意力分散或集中于其他事情时,也常容易忘记一些没有计划好的事和他想要做的事。我们以布拉特剧本里的教授为例,因为他的精力集中在第二卷书的问题上,他才会把自己的雨伞错拿成了别人的帽子。
我们由自己的经验得知,如果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别的事情上,就很可能会忘记他的计划或信约。
不可否认,这些话很容易理解,可却无法引起大多数人的兴趣,也无法满足我们的期望。还是让我们来细心研究这个解释过失的理论吧。以上所说的这些过失发生的条件是属于不同类别的:常态机能下出现的循环系统疾病和失调是错乱的生理根据;兴奋、疲倦及烦恼等,则可看成是心理生理的原因,这些都容易理论化。疲劳、烦恼和全面的兴奋能够引起注意力的分散,以致人们做事情受到干扰而不能准确完成。如果神经中枢的血液循环有毛病或变化也可能产生相同的结果,从而引起注意力的分散。总之,导致各种过失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机体的或心理的原因而引起的注意力扰乱。不过,这种解释对精神分析的研究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因此我们决定抛弃它。
事实上,当你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后,便会发现这个“注意力”理论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或者至少不能据此推论一切。很多人没有处于疲倦或兴奋的状态,而是一切正常,但也可能发生这种过失和遗忘。除非是因为出现了这些过失,我们才在事后将这些过失归因于他们自己所不肯承认的一种兴奋的状态。事实上,这个问题并非这样简单,因为注意力加强,事情未必会成功;注意力减弱,事情也未必失败。有许多纯粹本能的动作,不需要注意也能成功。比如走路,就算去的地方不明确,但也能到达目的地而不至于走错了路;这至少是我们常见的。
善于弹钢琴的琴师即使不假思索也可以弹成调。他当然可能会犯些偶然的错误,但是如果自动弹琴可以增加错误的危险,那么因不断地练习而使弹琴的动作完全变成自动的琴师就会极容易陷入这种危险之中了。不过,我们知道,有时候许多动作虽然没有给予特殊的集中注意,却往往更容易出成绩,而有时为了成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分心,反而更容易导致错误。你们可能会说那是兴奋的结果,但是兴奋为何不能促进他注意力集中在所期求的目的上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无法了解。因此,如果一个人在重要的谈话中把自己要表达的意思说反了,就很难用心理生理说或注意说去解释了。
关于这些过失还有许多别的不是很重要的特点,也并非这些理论所能解释清楚的。比如,一个人暂时想不起来某人的姓名,令他非常懊恼,可是他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想起那个已经到了嘴边只需有人提起便可立即记起的名字。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有时错误增多,会导致互相连锁,或互相替换。比如,有一个人第一次忘记了一个约会;第二次,他特别努力去记,结果却又发现自己把日期和钟点记错了。又比如有一个人想用各种方法记起一个已经遗忘的字,而思索时竟将那个可为第一个字做线索的另外一个字完全忘掉了,他要是因此追究这个字,又会忘掉其他的字引发连锁反应,如此等等。
排字的错误也是如此。据说,有一次在某“社会民主”报上也出现了这种错误。该报记载一次节宴,说:“到会者有呆子殿下”(His Highnes, the Clown Prince)。第二天更正时,该报道歉说:“错句应更正为‘公鸡殿下’”(His Highnes, the Crow-Prince)。又比如,某将军以怯懦广为人知。有一位随军记者访问将军,在通信中称将军为this battle-scared veteran(意思是临战而惧的军人)。第二天,他道歉了,说昨天的话应更正为the bottle-Scared veteran(意思变成了好酒成癖的军人)。据说这些过错是排字机中的怪物作祟的结果——这个比喻的涵义就不包括在心理生理说范畴内了。
暗示也能让人说错话。以一个故事为例:有一个新演员在《奥尔良市少女》一剧中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本应禀报国王说:“The Constable sends back his sword”(意思是“警察局长将剑送回来了”)。但是在预演时,主角开玩笑,几次将新演员的台词改成了“The Komfortabel sends back his steed”(意思变成了“独马车将马送回来了”)。结果公演时,这不幸的新演员虽一再告诫自己不要说错,结果却还是错了。新演员的失误显然是由于错误的暗示引起的,即他被暗示分了心。
关于过失的特点,并不是分心说所能解释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这个学说是错误的,或许加上某一环节才能使它变得完满。然而有许多过失却可以从另一方面加以考虑。
我们以口误为例。大家应该记得我们之前所讨论的只是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错了话,而我们所求得的答案也只是根据这一点而得来的。
当然除了这个特殊的原因,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原因。这就需要考虑过失的性质了。虽然就生理方面来说,我们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只要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过失的结果又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那么在心理方面,就仍然属于偶然发生的现象。比如,我说错了一个字,我说的方式可以有无数种,可以用无数个别的字来代替想说的那个字,或要想说对也可以有很多变式。那么,在可能存在的许多错误之中,为什么唯独发生了这个特殊的错误呢?是不是只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问题是否有合理的答案呢?
1895年,语言学家梅林格和精神病学家迈尔曾设法研究发生口误的原因。他们通过大量的事例,采用纯叙述的手法,将口误分成了“倒置”“预现”“语音持续”“混合”“替代”五种。现在我们举例来分类加以说明。比如,某人将“黄狗的主人”说成“主人的黄狗”,这就是明显的“倒置”的例子。又如一个旅馆的茶房去给一位大主教送茶水,当他敲着大主教的门,主教问是谁敲门时,茶房竟然慌张地回答说:“我的奴仆,大人来了。”这也是个倒置的绝好例子。
至于语音持续,则是由于已经说出的音节干涉到了将要说出的音节而发生的。例如,在某次聚会中,某人把“各位,请大家干杯(auzustossen),祝我们的主人健康”,错说成了“各位,请大家打嗝(aufzustossen),祝我们的主人健康。”又如,议会的一位议员称另一位议员为“honourable member for Central Hell”,(意即中央地狱里的荣誉会员),他把国会,直译过来就是中央大厅(Central Hall)误说成了中心地狱(Central Hell)。再如,一个士兵对朋友说:“我希望我们有一千人战败在山上”,他错把fortified(守卫)说成了mortified(战败)。这些都是“语音持续”的例子。在第一例中,“ell”这个音是从前面的词“member for Central”持续下来的,在第二例中,“men”一词里m音延续下来构成了mortified。
最为常见的例子还是“混合”或凝缩的例子。比如,一个男子问一位女士,可否一路“送辱”她(begleit-digen);“送辱”这个词是由“护送”(begleiten)和“侮辱”(beleidigen)这两个词混合而成。(但是年轻人要知道,如果他这样鲁莽,便很难成功赢得女人的喜欢。)又如,有人想要表达的是自己是被动的单恋(即情不自禁的单相思),但却说成了自己是被恋,这就是一个凝缩的例子。
比如一个可怜的女人说自己患了一种无药可治的鬼怪病(incu-rable infernal disease),又如某夫人说:“男人很少知道女人所有的‘无用的’性质(ineffectual qualities)的价值。”这些都可称为“代替”。
梅林格和迈尔的这些实例解释并非很完满,他们认为一个字的音和音节有不相等的音值,较低音值的音会被较高音值的音干涉。
显然,这个结论是以“不常见的预现”和“语音持续”作为根据的;就他这种口误而言,即使存在音值的高下也不成问题。最常发生的口误是用一个字代替另一个与其相似的字,它们音节有着类似之处。例如某教授在授课时,说:“我不愿估量前任教授的优点。”这里的“不愿(geneigt)”其实是“不配”(geeignet)的口误。
不过最普通而又最值得注意的口误是把想要说的话说反了,这种口误可不是由于音的类同而混乱的结果。有些人认为相反的词彼此之间有着很深的联系,因此在心理上有很密切的联想。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有一次国会议长在会议开始时说:“各位,现在法定人数已够,因此,我宣布散会。”
任何与说话人有关的熟悉联想,有时也会导致口误。
有一次,赫尔姆霍茨[2]的儿子和工业界领袖及发明家西门子的女儿结婚,宴会时,司仪请著名生理学家杜布瓦·莱蒙讲几句祝词。他的祝词说得相当漂亮,可是在结束时举杯庆祝,他却说:“愿西门子和哈尔斯克百年好合!”西门子和哈尔斯克是一个旧公司的名称,在柏林很有名字,在座的人都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杜布瓦·莱蒙将新娘和新郎的名字说成了一家公司的名字。
综上所述,需要注意文字间的类同和音值,字的联想也要加以重视。不过,这还不够。要想完满地解释错误,就某一类型的实例而言还必须将前面所说过或想过的语句一起研究。依梅林格的想法来看,这些例子都属于“语音持续”,不过起源较远而已。——如果真是这样,我想口误之谜将不得而解了。
不过,在研究上述各例时,有一种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之前所讨论的,是引起口误的普遍条件,而从没研究过口误的结果。仔细分析,其实每一种口误的结果都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口误的结果本身可被看成是一种有目的的心理过程,是一种有内容和有意义的表示。我们过去谈论的只是错误或过失,现在看来这些过失也可能是一种正当的动作,只是它突然出现,代替了那些更为人们所期待的动作而已。
从某些例子来看,过失的意义也是在明显不过了。议长在会议开始时就宣告闭会,我们由此可以推测出他一定认为本届会期必定没有好结果,不如散会来得痛快;因此这个过失的涵义是不难揣知的。又如某女士赞美另外一位女士说:“我一看就知道这顶可爱的帽子一定是你绞成(cufgepatzt)的。”她把“绣成”(aufgeputzt)说为“绞成”,其实是她实在看不上对方的手艺但又不便明说。又如某夫人十分刚愎自用,她说:“我的丈夫让医生帮忙代定食单。医生告诉他根本不需要,说他只要按照我所选定的东西吃喝就行了。”这个过失的涵义也很容易懂。
现在假设大多数的口误和一般的过失都有意义,那么我们过去从未关注过的过失的意义,就应该引起特殊的注意,而其他几点都应该相应退到次要地位。生理的及心理的条件可以略而不谈,把注意力全部用在研究有关过失意义及意向的纯粹心理学研究上,我们目前可用这个观点来对过失的材料作进一步讨论。
在没有讨论之前,还有一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那就是诗人常利用口误及其他过失作为文艺表现的工具。这也证明了诗人认为过失或口误是有意义的,他是故意这么做的。在诗人眼里,口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可能想用口误来表示一种深意,展现主人公的精神世界。
当然,假如诗人确实想要借错误来传递他们的意义,那我们就无须太过重视。错误或许根本没有深意,而只是精神上的一种偶发事件,或只存偶然的意义,不过诗人却仍能用文艺的技巧给过失以意义,来达到文艺的目的。
由此我们也可得知,在研究口误时,求之于诗人或许胜过求之于语言学者和精神病学者。
德国著名剧作家席勒(Schiller)在他的作品《华伦斯坦》第一幕第五场里举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口误例子。在上一幕中,少年比科洛米尼陪伴华伦斯坦的美丽女儿一直到营寨,一路上,他热切地为华伦斯坦公爵辩护而力主和平。在他退出后,他的父亲奥克塔维奥和朝臣奎斯登贝格不禁为他的言语感到大吃一惊。随后,他的父亲和奎斯登贝格有这样一段对话:
奎斯登贝格:天哪,难道就这样吗?朋友,难道我们就让他受骗吗?我们就放任他离开,不叫他回来,不在此时此地打开他那蒙蔽的眼睛吗?
奥克塔维奥:(从沉思中振作起来)他早就已经打开我的眼睛了,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奎斯登贝格:你在说什么?
奥斯塔维奥:这该死的一段旅行!
奎斯登贝格:为什么呢?你究竟什么意思?
奥斯塔维奥:朋友,来吧!我得马上用我自己的眼睛顺着这不幸的预兆来看一个明白——走!
奎斯登贝格:什么?要到哪里去呢?
奥斯塔维奥:(匆忙地说)到她那里去!到她本人那里去!
奎斯登贝格:到……
奥斯塔维奥:(更正了自己的话)到公爵那里去。快跟我走吧。
奥斯塔维奥本要说“到公爵他那里去”,但是由于想着儿子的事,不自觉出现了口误。从“到她那里去”这几个字,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他对于公爵的女儿免不了是有所依恋的。
兰克[3]在莎士比亚的诗剧里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实例,就是《威尼斯商人》一剧中,那幸运的求婚者巴萨尼奥选择三个宝器箱的那场戏。我可以先为大家读一读兰克的短评:
“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二场)中的口误都更好的表达出诗的情感好技术的灵巧。
这个口误与弗洛伊德在他的《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中所引《华伦斯坦》剧中的口误相类似,也足见诗人深知这种过失的结构和意义,并认为一般观众都可以领会。珀霞因受她父亲誓约的束缚,必须纯靠机会来选择丈夫。她幸运地摆脱了那些她不喜欢的求婚者,好不容易等到了她倾心的巴萨尼奥来求婚,但怕他也会选错箱子,于是她想告诉他,即使他选错了,也能博得她的爱情,但是因为有父亲的誓约所以这些话又不能直说。莎士比亚让她在这个内心的冲突里,对巴萨尼奥说出了这样的话:
请你稍等一下!等再过一两天之后,再来冒险吧!因为如果选错了,我就失去了你的友伴,所以我请你等一下吧!我真的不愿失去你(但这可不是爱情)……或许,我应该告诉你怎样做出正确的选择,可是我受誓约的束缚不能这样做,因此你很有可能会选不到我。但是一想到你可能会选错,我便想打破誓约。请不要注视着我,你的眼睛已经征服了我,将我分作两半;一半是你的,另一半也是你的——虽然我应该说是我自己的,但即便是我的,那当然便也是你的,所以一切都属于你了。
她想要暗示他,就是在他选择箱子之前,她已经属于他了,非常倾慕于他,只是这一层按理是不应说出的。于是诗人便利用口误来表示珀霞的情感,这样既能使巴萨尼奥稍微安心,又能使观众耐心地等待选择箱子的结果。”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珀霞在这段话的最后是如何巧妙地将自己说错的话和辨正的话相调和的,如何使它们既不会相互抵触,又能掩饰其错误。
“……既然是我的,那当然便也是你的,所以一切都属于你了。”
一些医学界之外的学者,通过观察而揭开了过失的意义,可以说是我们学说的先驱。
大家都知道,利克顿伯格是一个滑稽的讽刺家,歌德说:“他如果说笑话,那笑话的背后就一定暗藏了一个问题。有时,他还会将问题解决的方法隐示在笑话中。
有一次,他讽刺某人说:“他常将angenommon(动词,有‘假定’之意)读为Agamemnon,因为他读荷马读得太熟了。”这句话可作读误的解释。
在下次演讲中,我们要考察诗人是否会同意对于心理错误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