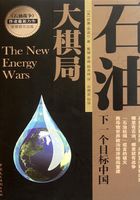
第4章 精心布棋(3)
建立石油帝国
20世纪50年代可谓美国石油巨头的黄金岁月。几大公司屈指可数,要么充当洛克菲勒石油帝国的魔爪,要么助纣为虐。二战后,洛克菲勒家族依托名下的信托基金等机构,有效掌控了当时国际石油的三驾马车——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雪佛龙)、新泽西标准石油(埃克森)、纽约标准石油(美孚)。[1]
这个石油帝国的掌门人就是洛克菲勒四兄弟。
老大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左右着战后的美国对日政策,还密谋了人口控制论。他掌管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世界各地慷慨出资,布局战后学术研究,目的就是为了家族的一己私利。
老二纳尔逊·洛克菲勒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身边的红人,在这位民主党总统的拉美政策上说一不二。后来又摇身一变,投靠到共和党艾森豪威尔总统麾下,位高权重,一手策划了冷战时期的对苏心理战。
老三劳伦斯·洛克菲勒在政治舞台上与兄弟们不分伯仲,且更具商业头脑。他有不少公司,东方航空便是其中之一,没少把波多黎各的廉价劳工运到美国的血汗工厂。60年代末,他还通过风险投资创建了一个小型半导体公司,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英特尔。[2]
大卫·洛克菲勒排行最小,执掌家族的大通国家银行,为洛克菲勒标准石油的全球布局筹措资金,并让大通逐渐成为美国第二大国际银行。
二战以后,洛克菲勒兄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除了主宰石油帝国,他们还通过公司董事会盘根错节的关系,把触手伸进主要军工企业,像麦克唐纳飞行器、孟山都、杜邦、力士火药、核能发展、通用电气、洛克威尔等等。此外,借1919年凡尔赛和谈之机,洛克菲勒和J.P.摩根一起出钱,创建了“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CFR)这个私营智库,豢养了一批精英中的精英。[3]
冷战初期,艾森豪威尔政府中的实权派当属杜勒斯兄弟。艾伦·杜勒斯是中情局局长,约翰·杜勒斯是国务卿,两人的仕途都得益于洛克菲勒帝国。
约翰·杜勒斯曾任职华尔街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是标准石油公司的代理律师,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理事。与洛克菲勒家族联姻后,他升任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之后便平步青云,出任国务卿。[4]
简而言之,洛克菲勒石油王朝运筹帷幄,在战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占尽先机,目的就是扩张其石油帝国,在全球巧取豪夺。
哈佛项目老谋深算
20世纪50年代,在洛克菲勒家族利益的驱使下,美国跃升为世界头号石油消费国,标准石油则控制着开采、精炼、运输等重要环节。但这个石油帝国的幕后老板仍不满足,不甘心像普通公司一样只赚点蝇头小利。
美国法律严禁行业垄断,不过涉及石油产业时,大公司却总能让政府三缄其口。洛克菲勒家族在战后的美国政界法力无边,在共和、民主两党均能畅行无阻,其石油帝国垄断势力无人能及。1950年,石油、洛克菲勒石油卡特尔、美国“国家安全”俨然已是“三位一体”了。由于五角大楼日益庞大的战争机器成为石油产业最大的客户之一,石油就冠冕堂皇地戴上了神圣的光环。既然石油对美国国家安全如此重要,岂能放任自流![5]
社会工程学家于是萌生了一个念头,别出心裁而又阴险恶毒。他们先是将其推销给洛克菲勒等美国“东海岸权势集团”(即华尔街和标准石油)的权贵们,接着又扩大到西方世界,核心就是借助石油来控制社会。他们先在美国小试牛刀,之后其黑手便迫不及待地伸向整个世界。
194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慷慨解囊,资助哈佛大学年轻的俄裔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10万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6]
列昂惕夫在大学期间离开苏联移民到美国。他在战后创建了哈佛经济研究项目,收集行业生产数据,借此建立动态经济模型。哈佛商学院雷·高柏和约翰·戴维斯教授的“农业产业”模型就是该项目的一部分。整个50年代,洛克菲勒家族对他的资助源源不断,后来福特基金会也加入进来。要知道,福特基金会的一举一动和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时遥相呼应,在50年代和中情局更是如影随形。
列昂惕夫雄心勃勃,首次利用IBM计算机研究复杂的经济问题。[7]其研发的模型非常精准,让华盛顿的实权派可以及时判断经济运行态势,避免自身利益受损。对洛克菲勒家族及其朋友而言,该项目还为如何控制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手段。
在洛克菲勒、杜邦、福特等权势精英的眼中,芸芸众生都可以任其摆布,使他们即便被榨干利益仍旧对真相浑然不知。
社会工程学源自运筹学,是两次世界大战孕育出的方法,在战略和战术层面都适用。运筹学最初是研究空中和陆地的防御问题,以便在对敌作战中发挥军事资源的最大效用。一些有远见的高官颇受启发,认定这个方法也可以用来控制整个社会,于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接触列昂惕夫。[8]列昂惕夫的项目起初是为不断拓展的美国经济建模,后来随着计算机功能增强,数据增多,他开始模拟全球经济的运行。[9]
毫无疑问,社会工程学的核心问题是能源。列昂惕夫也开始关注如何管理“有限资源”,这正是洛克菲勒帝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战略的核心。原因不言自明,有能力对石油这一最重要的资源呼风唤雨的,注定只有洛克菲勒石油帝国。
油价居高不下
随着经济模型的完善,预测未来经济的整体趋势和能源需求成为可能。同时,在人为操纵下,美国逐渐从依靠有轨交通变成以汽车为主。但是,标准石油及其盟友壳牌,以及当时的盎格鲁-波斯石油(即后来的BP),这些石油巨头们仍然夜不能寐,因为一旦大量石油突然涌入世界市场,他们精心搭建的石油大厦就会轰然倒塌。要知道,仅当时德克萨斯西部的帕米亚油田就有482公里长,402公里宽。
1948年,标准石油在沙特的子公司阿美石油(ARAMCO),在加瓦尔(Ghawar)发现了世界上储量最大的油田,一夜间世界石油市场地动山摇。到2005年该油田已累计产油550亿桶,尽管质疑不断,但在被发现半个世纪后,它的日产量仍高达500万桶。然而这仅仅是当时新发现的巨型油田之一,1953年在伊拉克又发现了超级油田鲁马利阿(Rumalia)。美国虽然盛产石油,但受此影响开始逐渐倚重石油进口。
好在洛克菲勒帝国及其盟友提前下手,大多数新发现的大油田都没能逃出他们的掌心。
在控制了沙特、科威特的新油田,进而得以号令中东之后,帝国的石油巨头们得寸进尺。他们认为,用中东的廉价石油冲击美国市场有利可图,一是国内开采成本较高,二是很多油田仍属于其他中小石油公司。
20世纪50年代初,世界石油的开采成本相差悬殊。与美国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俄克拉荷马相比,沙特等中东国家的开采成本通常只有它们的1/4到1/5。阿美石油在沙特开采一桶原油的成本是20美分,却能卖到1.75美元。另外,美国财政部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为沙特政府量身定做了“外国税收抵免”协议,保证其石油廉价进口,以便挤垮石油卡特尔以外的其他公司。与此相反,阿美石油在美国和沙特却一分钱的税都不用缴。[10]
石油巨头们说干就干,廉价的中东石油在美国市场遍地开花。
尽管如此,石油大亨们仍有一个梦魇挥之不去。作为当时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世界石油虽然控制在洛克菲勒帝国及其盟友手中,但如果其他石油公司也发现了像加瓦尔、鲁马利阿这样的超级油田,又不肯与洛克菲勒沆瀣一气,那么就会终结美英玩家对世界石油的控制,最终就有可能噩梦成真。
显然,加强对石油的控制迫在眉睫。
石油巨头打造“专家”
作为第一步,美英石油巨头认为需要一个经过科学包装的谎言——石油储量有限并会迅速枯竭。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易于被大众接受,也便于散布,为此专门选定了芝加哥大学石油地球物理学家马里昂·金·哈伯特。此人性格古怪,喜欢被称作“金”先生,曾供职于德克萨斯的壳牌石油公司。
在1956年美国石油学会的年会上,石油巨头授意哈伯特发表了一篇名为《石油峰值》的论文,一场当代最著名的科学骗局就此拉开序幕。
哈伯特结论的前提是——石油是化石燃料,是5亿年前恐龙、藻类等生物体经生化反应生成的。这个前提仅仅是个假设,完全未被证实。哈伯特对此说也未做任何科学证实,但却将之奉为圭臬,进而提出新马尔萨斯主义,即面对即将到来的石油匮乏必须采取社会控制措施。
1989年哈伯特去世前在一次访谈中直言不讳地承认,他用来估算美国石油储量的方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就像竖起手指来测量风速。他说道:
他们要求我做的,就是估计石油的最大储量……我必须知道。我别无选择,只能画出石油峰值的曲线,还要让所有人对此深信不疑。这就是事情的真相。相关曲线都是臆想出来的,我只是大概估算了一下,随手一画,如果觉得数值太高,就把线画低点,反之就画高点。除了根据曲线本身计算某段时间的石油产量之外,根本不涉及任何数学问题……就我个人感觉而言,当时美国石油的最大储量大约是1500亿桶。[11]
如果哈伯特的这套方法听起来缺乏科学的严谨性,那是因为它原本就不是。
哈伯特还承认,化石燃料说让自己的石油峰值论顺理成章。“这个假设提供了强大的地质学基础,让我们的说法听起来不是信口开河。”他还胸有成竹地讲道:“原始生成的石油总量是一定的,再生部分可以忽略不计。可开采的区域仅限于古生物大量沉积的岩床,而且迄今为止所有可能出产石油的地区均被仔细勘探过。”[12]
这一预测耸人听闻,其实1956年全球石油勘探工作才刚刚起步。
大约25年后,美国德克萨斯州德高望重的石油地质学家和勘探工程师迈克尔·霍尔布蒂对这一结论提出大胆质疑,他认为美国国内的石油开采量会不断增加,并为此振臂疾呼。1980年他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
全球约有600个具备开采前景的油气盆地,其中160个已有较好的商业产出,240个刚开始开采,剩余的200个尚未开发。截止1978年,全球共钻井3444664口,73%是在美国,但美国可开采的地质区域仅占世界的10.7%。也就是说,在世界上89.3%的可开采区域,钻井数才仅有27%……大多数油气盆地有待开发。[13]
对此,哈伯特和石油巨头们充耳不闻。
石油峰值论毫无科学依据,却被大肆鼓吹。哈伯特进一步预测,美国石油储量最多不过2000亿桶,1970年产量将达到顶峰,随后不可避免地会沿钟形曲线加速下滑。
为了把伪科学装扮成真科学,哈伯特使用了高斯曲线,这是19世纪德国数学家卡尔·高斯发明的实证性研究工具。但是,为什么要用高斯曲线来描述石油储量,哈伯特不光在论文中只字未提,此后也绝口不谈。哈伯特的曲线并未采用油田实际生产数据,而是他所声称的对所有油田都适用的理想数值。他先估计美国境内的生物沉积量,然后以此为据推导出所谓石油最大储值。[14]
肯尼思·德费耶是20世纪50年代哈伯特在休斯敦壳牌的同事。他说:“哈伯特预测所使用的数学方法并不十分清晰。44年后的今天,我猜测他和很多人一样,也是先得出结论,然后再寻找原始数据加以支撑。尽管和他上百次共进午餐,也有数次深谈,但我始终没有胆量询问他的根本依据到底是什么。”[15]
德费耶一直是哈伯特理论忠实的追随者,后来成为地质工程学领域的著名教授,在精英汇聚的普林斯顿大学授课。他的这番话发人深省。在如此重大的地球物理学问题上,德费耶显然缺乏学术勇气。而哈伯特却在关键问题上对最亲密的同事都讳莫如深,或许他知道自己根本无法阐释。假的终归是假的。
值得注意的是,哈伯特在去世前不久的一次深度访谈中承认,在1956年发表石油峰值论之前,他先把论文送给皇家荷兰壳牌的董事长过目。哈伯特还说:“壳牌老板就扔下一句话,一定要和威克斯高估石油储量的观点分庭抗礼。”[16]
威克斯是美国当时最权威的石油储量专家,他预计美国的石油储量有4000亿桶,而且不断调高预期,这让石油巨头们颇为头痛。如果储量充足,那么维持高油价就没有理由,何况下一步他们还想把油价继续拉高。
显然哈伯特对壳牌老板的话心领神会。于是他提出美国的储量只有2000亿桶,而且预测1970年是石油峰值的分水岭。
还是在1956年的那篇文章中,哈伯特预测全球石油的终极储量为1.25万亿桶。而2008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预计,全球原油储量仍有1.8至2.2万亿桶。从一百多年前开启石油时代算起,目前全球已消耗了1万亿桶,如果按哈伯特1956年1.25万亿桶的“科学”预测,BP如此之高的储量预期从何而来?[17]
哈伯特的预测就真的那么“科学”吗?实际情况显然与此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