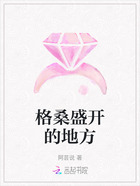
第2章 那年正青春
当大我一届的高考倒计时牌翻到“100天“时,整个高三开始浸在誓师大会的喧嚷里。
而我的成绩也在日复一日的埋头学习中初见成效。
高三誓师大会,我代表高二优秀学生发言。
我攥着演讲稿穿过连廊,蔷薇花架上垂落的紫藤扫过脖颈,像极了那年祝骁替我摘下发梢银杏叶时,指尖的温度。
四月的礼堂飘着细碎的柳絮,突然闯入的穿堂风掀开帷幕,稿纸如白鸽纷飞,其中一页恰好扑在推门而入的军校生胸前的绶带上。我攥着修改到第九版的演讲稿躲在幕后,看着那个穿军校制服的挺拔身影正在调试话筒。祝骁的肩章在追光灯下泛着冷银,话筒突然啸叫的瞬间,他侧头望过来的目光,与我记忆中贴在手机后壳上的照片重叠——那是前世在一起后他赠我的戴着优秀毕业生绶带演讲的旧照。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22岁的祝骁比记忆中更加挺拔,军装衬得他肩宽腰窄,晒得微黑的脸上是严肃的表情。当年大学军训时我们相识,我对他产生好感,但直到大学快毕业才真正认识。现在,命运好似给了我提前相遇的机会。
“《论理想主义者的生存逻辑》?“他捏着纸页轻笑,金属绶带扣折射的光斑晃过我眼睫。那截骨节分明的手腕上戴着军用电子表,秒针跳动的节奏却与礼堂古老的座钟完全同步。
我慌忙去抢稿纸,却见他突然蹲下身掏出钢笔开始在我的演讲稿上涂涂改改,随后他合上笔帽,又从军靴边缘拈起片银杏叶:“上次来母校做国防教育,你躲在树后记笔记的样子,很像侦察兵。“
血液轰然涌上面颊——前世高二的某次社团开放日,我确实蹲在银杏树下偷录过国防科技讲座。摄像机里穿迷彩服讲解弹道学的侧影,此刻正活生生立在面前。
“话筒高度合适吗?“他突然朝我伸手,虎口处那道射击训练留下的疤痕清晰可见。我捏着演讲稿的指节发白,他腕间飘来若有似无的松木香。
他虎口的疤痕蹭过调音键,礼堂突然爆出刺耳啸叫。台下此起彼伏的惊呼声里,祝骁单手扯开领口麦克风,作战靴蹬上控制台的动作利落得像在拆弹。
“备用线路接第三通道。“他转头对我比战术手语,见我不懂,直接拽过我的手腕按在调音台绿色按钮上。温热的触感如微电流窜过,我这才注意到他食指第二关节有道新鲜的灼痕。
当他的声音重新响彻礼堂时,我藏在讲台后的手指正摩挲着被他改写过的那页稿纸。原本生硬的“家国情怀“被替换成遒劲的钢笔字:“真正的理想主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演讲结束即将离场,“小心。“祝骁单手撑住我踉跄的身体,作战服袖口的魔术贴勾住了我胸前的学生卡。当那张卡片翻转着跌落时,他接住的瞬间突然顿住——证件照背面本该空白的区域,赫然是荧光笔涂抹的星云图案。
我慌忙去抢,却听见他低声念出我前天熬夜补完《三体》后,鬼使神差写在边角的句子:“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
“这是...你的生存法则?“他的拇指擦过墨迹未干的“不择手段“,新兵营砂砾般的嗓音里混着奇异的震动。礼堂顶灯突然全熄,应急通道的绿光里,我看见他瞳孔中倒映着从前的自己——那个躲在围栏外,踩着积雪抄录弹道公式的偏执狂。
“上周定向越野训练,我见过一株银杏。“祝骁忽然扳正我发烫的脸,虎口的茧蹭过耳垂,“它从混凝土观测塔的裂缝里长出来,根系把钢筋都绞碎了。“
许久,他俯下身子,与我平视,“你叫什么名字?“
“安宁。“
“安宁,“他重复道,声音低沉,“你和其他学生不太一样。“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当然不一样,我比他实际年龄还大十六岁。“哪里不一样?“
“眼神。“他简短地说,“像见过很多东西。“
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颤。他比我想象中敏锐得多。
接下来的合影中,
祝骁被同学们簇拥在中间,我站在后排边缘。拍照时,我感觉到他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我身上。那一刻,我同时注意到站在前排回头找我的于黎川,他眼里有明亮的光。
晚上回到家,我翻开尘封已久的日记本。17岁的我曾在这里写下无数对于黎川的暗恋心事,对未来的迷茫,对高考的恐惧。现在,我写下新的文字:
“亲爱的日记,我回来了。这次我不会重蹈覆辙。无论是于黎川还是祝骁,都不会成为我的全部。我要考上理想的大学,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爱情,就随他吧。“
合上日记,我望向窗外的星空。这一次,我要把命运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后来,视频网站推送的国防生专访里,祝骁案头摆着镶在亚克力板中的演讲稿,赫然是我当日的那一篇——《论理想主义者的生存逻辑》,只是在她修改的批注旁多了行小楷:“当啸叫响起时,蝴蝶正在风暴中心振翅。“
月考成绩单贴在教室后面的公告栏上,同学们挤作一团寻找自己的名字。我坐在座位上没动,手里转着笔。江晚宁从人群中钻出来,眼睛瞪得溜圆。
“安宁!你考了第以名!“她几乎是跳着回到我身边的,“你怎么做到的?短短一学期就从二十名逆袭到第一名了!“
我笑了笑:“可能是假期真的用功了吧。“
班主任祝老师敲了敲讲台:“这段时间,我们班有几位同学进步显著,特别是安宁同学,从班级中游直接进入了第一名。“她推了推眼镜,“安宁,有什么学习方法可以和大家分享吗?“
全班同学齐刷刷地转头看我。全班同学齐刷刷地转头看我。我深吸一口气站起来,目光不经意扫过第四排靠窗的位置——于黎川正歪着头看我,嘴角挂着那个曾经让我心跳漏拍的笑容。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的侧脸上,和记忆中一模一样。
但奇怪的是,我的胸口没有传来熟悉的悸动。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我斟酌着词句,“就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比如数学,我习惯先理解原理再做题;英语则是多读多听培养语感...“
我尽量说得像是普通的学习经验,而不是来自十年后的认知。但当我提到“知识框架构建“和“刻意练习“这些概念时,祝老师的眉毛越挑越高。
“很成熟的学习理念,“她评价道,“不像高中生能总结出来的。“
我的心跳漏了半拍。表现得太过头了?但于黎川突然开口:“我觉得安宁说得很好,我们是否可以组织一个学习小组?“
“不错的建议。“祝老师点头,“安宁,你愿意牵头吗?“
就这样,我成了高三(7)班学习小组的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