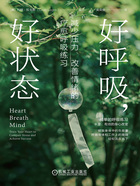
心脑结合
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界普遍的看法是心和脑之间的交流是单向的,心脏对大脑的指令做出反应,而不是反过来。但是多亏了像心理生理学家(也是夫妻)约翰·莱西(John Lacey)和比阿特丽斯·莱西(Beatrice Lacey),哈佛医学院的赫伯特·本森(Herbert Benson)医学博士,心脏数理研究所(Heart Math Institute)的奇尔德(Childre)博士和罗林·麦克拉迪(Rollin McCraty)博士这样的研究者,上文提到的莱勒和罗格斯大学的瓦西洛夫妇,以及朱利安·塞耶(Julian Thayer)博士,还有很多其他这样的先驱们开创性的工作,我们现在才能知道心脏和大脑在进行一场不间断的双向对话,每个器官都影响着对方的行为。
例如,麦克拉迪的研究告诉我们,当我们的心律不稳定、紊乱时,从心脏到大脑的相应神经信号会抑制较高的认知能力。当你处于战或逃的状态时,大脑中控制复杂认知行为(如计划和决策)的前额皮质就会“离线”。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这是有道理的;当你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时,你的身体要确保你不会因为过度分析而瘫痪,从而将生存放在优先位置。可惜,这也阻碍了你清晰地思考、回忆、学习、推理和做出明智决定的能力。
相比之下,处于休息与消化模式的身体,高心率变异性会产生更有序、更稳定的心脏模式,向大脑发送信息,促进认知功能,增强积极感受和情绪调节能力。[1]高心率变异性与平滑、高效的前额皮质活动和执行功能的任务有关,这类任务包括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这意味着,通过增加心率变异性,你可以改善前额叶活动,从而提高自我调节、抑制消极思想、做出客观决定以及记住所学知识的能力。
究其本质,心率变异性是对心脏跳动变化的测定。一般来说,高心率变异性对应着灵活的自主神经系统,能够快速对内外刺激做出反应,并与反应速度和适应性有关。心率变异性低则代表自主神经系统的灵活性下降,难以从压力中恢复,并与健康水平和表现能力下降有关。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那样,心率的变化可以由多种因素引起,包括情绪、压力以及各种身体和行为的变化。但同样的可塑性使心率变异性对日常生活的压力源变得敏感,也使它容易受到呼吸和视觉化的影响。通过提高心率变异性,我们可以训练身体,使其能够灵活地转换到所需的积极状态。比如当你结束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商务会议时,在接下来的一天里你不会因此感到焦虑或怨恨,你的心脏会支配副交感神经系统,让你放松并为下一次的表现重新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