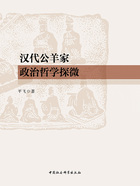
三 汉代公羊家与政治哲学思考
儒家思想的最主要载体是五经,五经当中有一经与孔子的关系最密切,这就是《春秋》。孔子是否作《春秋》曾引发争论,成一千古学术公案,至今众说纷纭。现代人研究孔子,不太注意《春秋》。可是,在汉代,“孔子作《春秋》”是一个基本的文化认同。围绕《春秋》进行解说,本有五家,但流传下来的只有三家,其代表作分别是《公羊传》、《穀梁传》、《左传》。[21]公羊家就是以《公羊传》为源头,并顺着这个解释路径不断衍生而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
唐代儒家学者徐彦在《春秋公羊传注疏》中曾引用戴宏的序言,对先秦至汉初的“公羊学”传授系统作了一个勾勒:“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从子夏到公羊寿[22]这一段传承已经很难具体考证,因为当时主要是口头传授,口说无凭,给后来的研究带来困难,只有到公羊寿才真的将《公羊传》著于竹帛即写定文本,可以真正考究公羊家的也就从公羊寿开始。
可惜的是,公羊寿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的具体事迹也几乎荡然无存;幸运的是,他们毕竟给我们留下了一定程度上反映他们思想的《公羊传》。更幸运的是,一代儒宗董仲舒进一步发挥了《公羊传》的思想,形成了公羊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公羊学不断受到左氏学冲击的时候,又有何休详细解诂《公羊传》,进一步发挥公羊学的思想,还和《春秋》经合在一起,后来升格为十三经之一。无论从留下可供研究文本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当时思想的影响来看,公羊寿、董仲舒、何休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公羊家。今人研究古人的思想,必须以文本为据,因此公羊寿的《公羊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就成为研究的重点,而散见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其他辑佚书中的其他公羊家及其思想也将受到特别关注。考察汉代公羊家,自然注意力集中在公羊寿到何休这一时间段的学者。
公羊寿以后,公羊家最杰出的代表是胡毋生与董仲舒。《史记·儒林列传》载:“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齐地公羊家以胡母生为代表,后继者有公孙弘。《汉书·儒林传》载:“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由于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其独特的政治地位使公羊学更受到学者的重视,所以“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公羊学研究蔚然成风,是为“显学”。赵地公羊家以董仲舒为代表,其公羊学最为有名:“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儒林列传》)其传者甚众:“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又载:“董生为江都相,自有传。弟子遂之者:兰陵褚大、东平赢公[23]、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长史,唯赢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孟为符节令,坐说灾异诛,自有传。”又《汉书·吾丘寿王传》载:“吾丘寿王字子赣,赵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诏使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由此可以看到董仲舒的五个有名弟子——褚大、段忠(《汉书》“忠”为“仲”)、吕步舒、赢公、吾丘寿王,以及再传弟子孟卿[24]、眭孟[25]。从学术传承的角度来看,赢公与眭孟是两个重量级人物。虽然董派公羊家的官位没有达到“天子三公”的品级,但也有不少弟子“学至大官”,直接参与现实政治活动。
眭孟的学术继承人最主要的是严彭祖与颜安乐,两人开出严氏学与颜氏学两个家派:“严彭祖字公子,东海下邳人也。与颜安乐俱事眭孟。孟弟子百余人,唯彭祖、安乐为明,质问疑谊,各持所见。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乐各颛门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汉书·儒林传》)
严彭祖很有大师风范,“廉直不事权贵”,学术传承后继有人,线索分明。《汉书·儒林传》载:“彭祖为宣帝博士,至河南、东郡太守。以高第入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权贵。或说曰:‘天时不胜人事,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亡贵人左右之助,经谊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终。援琅邪王中,为元帝少府,家世传业。中授同郡公孙文、东门云。云为荆州刺史,文东平太傅,徒众尤盛。云坐为江贼拜辱命,下狱诛。”
颜安乐很有穷人骨气,“为学精力”,学术传承又开出两派。《汉书·儒林传》载:“颜安乐字公孙,鲁国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贫,为学精力,官至齐郡太守丞,后为仇家所杀。安乐授淮阳泠丰次君、淄川任公。公为少府,丰淄川太守。由是颜家有泠、任之学。”
同一个学者同时就学一对师生是常有的事,所以公羊家的传承也并非是一条线垂直向下的,而有错综交织,贡禹开始就是如此:“始贡禹事嬴公,成于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广[26]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传。广授琅邪管路,路为御史中丞。禹授颍川堂溪惠,惠授泰山冥都,都为丞相史。都与路又事颜安乐,故颜氏复有管、冥之学。路授孙宝,为大司农,自有传。丰授马宫、琅邪左咸。咸为郡守九卿,徒众尤盛。宫至大司徒,自有传。”(《汉书·儒林传》)
以上的传承是清楚的,但后来的传承有些就不太具体。《后汉书·儒林列传》载:“丁恭字子然,山阳东缗人也。习《公羊严氏春秋》。恭学义精明,教授常数百人,州郡请召不应。建武初,为谏议大夫、博士,封关内侯。十一年,迁少府。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当世称为大儒。太常楼望、侍中承宫、长水校尉樊等皆受业于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骑都尉,与侍中刘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谘访焉。卒于官。”丁恭到底师从谁就不得而知,周泽也是如此:“周泽字都,北海安丘人也。少习《公羊严氏春秋》,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具体老师不可指,但属于严氏学却一致。
丁恭的老师不清楚,但学生又分明,如楼望、承宫[27]、樊倏[28]、钟兴。[29]其中,樊倏的公羊学很有影响,世号“樊侯学”:“初,倏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侯学’,教授门徒前后三千余人。弟子颍川李修、九江夏勤,皆为三公。勤字伯宗,为京、宛二县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称。安帝时,位至司徒。”(《后汉书·樊倏传》)樊倏有一个学生叫张霸[30],对公羊学颇有研究:“初,霸以樊倏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其子张楷[31]也颇有名气。
在东汉时期,李育与何休都是著名的公羊大师,但具体师承难以确定。《后汉书·儒林列传》载:“李育字元春,扶风漆人也。少习《公羊春秋》。沈思专精,博览书传,知名太学,深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记荐育于骠骑将军东平王苍,由是京师贵戚争往交之。州郡请召,育到,辄辞病去。常避地教授,门徒数百。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建初元年,卫尉马廖举育方正,为议郎。后拜博士。四年,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再迁尚书令。及马氏废,育坐为所举免归。岁余复征,再迁侍中,卒于官。”李育著《难左氏义》非陈元、范升之徒,又针锋相对以《公羊》义难左氏学权威贾逵,当时很有影响。
何休更是公羊学巨子,如果没有何休的解诂,也许《公羊传》就会亡佚。《后汉书·儒林列传》载:“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以列卿子诏拜郎中,非其好也,辞疾而去。不仕州郡。进退必以礼。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又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党禁解,又辟司徒。群公表休道术深明,宜侍帷幄,单臣不悦之,乃拜议郎,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何休的老师是羊弼,可羊弼受业于谁又不得而知。
有汉一代,公羊寿首次将《公羊传》著于竹帛,董仲舒三年不观于舍园,何休“十有七年”不窥门,三者实是公羊家的三大巨星。从公羊寿到何休,公羊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大就大在公羊家不仅在学术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派别,成为今文经学的代表和重镇,而且公羊家多数都参与政治,有实际的政治实践与政治经验,在汉代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实际的作用,对汉代良善政治建设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政治上的影响,其实,这都与汉代公羊家研究的主题和内容有关,而这个主题和内容主要是政治,当然包括政治哲学。考察汉代公羊家及其文本,不难发现,对政治的哲学思考是汉代公羊家的一个主要任务,而勾勒出汉代公羊家政治哲学的实质系统和形式系统是我们的一个任务。
哲学的本性是追问,把问题逼出来,并试图给出答案。面对着汉代公羊家政治哲学这个主题,首先要考究的是,汉代公羊家是面对针对什么来展开对政治的哲学思考的,又是根据什么来对政治进行哲学思考的。这个问题的破解就是探讨汉代公羊家政治哲学的历史文化根基。公羊家面对针对什么来思考,必须深入公羊家所熟悉的历史与所生活的时代;公羊家根据什么来思考,必须深入可选择的文化传统与思想资源。离开汉代公羊家政治哲学的历史文化根基来考察,难免今人古代化。一统的汉代社会与分裂的春秋社会形成鲜明的历史对比,丰富的诸子学说与删定的五经元典提供可选的思想资源。汉代公羊家面对活的历史而思,继承活的传统而思,历史的道德法则与政治法则就不能不引起关注。
接着要考究的就是,公羊家是怎样对政治进行思考的,特别是怎样对政治进行哲学思考的?与以前的思想家又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的破解就是探讨公羊家对政治的哲学思考方式。汉代公羊家面对历史而思,依照传统而思,不断形成了以“原道、宗经、征圣”为表征的经学思维方式。这种经学思维方式表现在对政治的思考上,则是“王”化孔子,托孔为王;“经”化历史,托经为王;“文”化实史,托鲁为王。“假托性”的主旨是王化、经化、文化,表明公羊家要对现实历史生活中的政治行为进行道德诊断,阐发出政治的应然道理。孔子素王之“素”,《春秋》当新王之“新”,托王于鲁之“托”,无不渗透着公羊家对“政治的善”与“善的政治”的独特哲学思考。
然后要考究的就是,公羊家对政治的哪些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思考,并思考出了什么?其核心理念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破解就是探讨公羊家政治哲学的主体内容。
第一个主题是政治的一统秩序问题。公羊家对“王道”“大一统”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主张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来建设,深入地探讨了政治的文化灵魂问题,高标了儒家一统政治。
第二个主题是政治的伦理基础问题。公羊家充分发挥了孔子“政者正也”的思想,在正名、正始、正心、正德上进行了别具一格的探讨,对王道、君道、臣道也作了分析,高标了儒家伦理政治。
第三个主题是政治行为的权衡问题。公羊家重视对经权、文实的讨论,既强调权的必要,认可实的价值,又始终强调权道与文不与,交织着政治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高标了儒家权道政治。
第四个主题是政治领域的敬畏问题。公羊家重视天人关系思考,对《春秋》灾异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而且推广到直接谈论汉代的灾异与政治,表达了对政治敬畏的独特思考,而汉代帝王也常逢灾异就下罪己诏,不断推动善政建设,高标了儒家灾异政治。
公羊家通过对政治哲学问题的探讨,构建了一个由一统政治、伦理政治、权道政治、灾异政治合成的王道政治,并以此为基础对政治发展历史进行价值审判,凸显政治的善与善的政治。在分析这个政治哲学结构的形成过程中,不断揭开神秘的面纱,也就能理解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真谛。
[1] 任剑涛:《政治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2] 现实生活的实际思考是复合的,学科理论的预设划界是明确的,而且随着学科的分化与研究的细化越来越明显。任剑涛指出:“亚里士多德把古典政治学具有的两面学术性格凸显了出来:一方面,政治学在谈应然;另一方面,政治学又在谈实然。当政治学谈应然的时候,严格说来,它表达的是古典政治学里面的政治价值观、政治希望、政治理想。而政治学在谈实然的时候,它所表达的是政治操作过程中存在的诸实际制度的运行状况。注意,这就是古典政治学对政治现象的分类研究,对诸政治制度安排方式比较分类的一个描述。前一方面指出了政治的意义;后一方面指出了政治的实际从事方式。这样,我们才可能判断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政治生活,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实际上政治学包办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的理论尝试——古典意义上的政治学,在它阐述政治的意义的时候,实际上就等同于政治哲学;在它阐述实际的政治操作方式的时候,实际上就等同于政治科学。”(任剑涛:《政治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2页。
[4] [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上册),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5] 任剑涛:《政治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6] 詹姆·古尔德等主编:《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0—61页。
[7] 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8] 李天然:《译者前言》,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6—177页。
[10] 为了避免繁复,文中凡引古籍,使用夹注或随文注明出处。
[11] 余英时曾指出:“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在两千多年中,通过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种种制度的建立,儒学已一步步进入国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4页。)其实,其他各家也非常重视对政治秩序的思考,这是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
[12] 周桂钿:《政治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11期。
[13]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牟宗三认为:“是以实现政权之为政权,政道乃必须者。此道即政权与治权分开之民主政治也。依是,无论封建贵族政治或君主专制政治,皆无政道可言,以其皆不能恢复政权之本性也,皆不能实现政权之为集团所共同地有之或总持地有之之义也。依是,唯民主政治中有政道可言。”(同上书,第19页)又,“行施治权必依一定制度而设各部门之机关,又必在其措施或处理公共事务上而设一定之制度,凡此制度皆随治权走。此为隶属、委蛇或第二义之制度,而维持政权与产生治权之制度(即宪法,政道),则为骨干、根源或第一义之制度。讲政治以第一义之制度为主,此则属于政道者。而第二义之制度则属于治权或治道,因而亦属于吏治者,不属于政治者。属于治权或吏治之第二义制度,中国以前甚粲然明备,而唯于第一义之制度,则无办法,此即前文所历述之对于政权、政道之反省甚为不足也。”(同上书,第20页)这是当代的民主政治理念,显然不可能在古代提出。
[14] 牟宗三认为:“这种治道之不足处,不是治道本身的问题,乃是政道方面的问题。假定相应政权有政道,民主政治成立,使政权与治权离,则此种治道当更易实现,且反而使自由民主更为充实而美丽。”(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15]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6] 周桂钿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儒家哲学为主要代表的。儒家讲内圣外王,内圣是仁义道德、心性修养,外王就是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讲德治、仁政、王道,因此可以说是追求善的政治哲学。”(周桂钿:《政治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11期。)其实,内圣也不纯粹是个体的心性修养,也是政治哲学的组成部分。
[17] 萧公权指出:“君主既为治乱的关键,所以秦汉以后两千年的政治学说多致意于‘君道’之一端。如何格君心?如何匡扶主德?如何教海储贰?这些都是中国政理中的主要问题。我们先哲述君道的学说,详尽周密,深切精确,恐怕是任何欧洲思想家所不能企及。但话又说回来,专制天下的政理既针对专制天下的政体而提出,在这里政体消灭以后也定然要失去其实际上的应用价值。”(萧公权:《宪政与民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79页。)
[18] 宋儒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总列两目为“帝王为治之序”与“帝王为学之本”,后者又细分“尧舜禹汤文帝之学、商高宗周成王之学、汉高文武宣帝之学、汉光武明章唐三宗之学、汉魏陈隋唐数君之学”五个子目。内圣治己又分列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其中“格物致知之要”又分为四,即明道术(天性人心之善、天理人伦之正、吾道源流之正、异端学术之差、王道霸术之异)、辨人才(圣贤观人之法、帝王知人之事、奸雄窃国之术、险邪周上之情)、审治体(德刑先后之分、义利重轻之别)、察民情(生灵响昔之由、田里休戚之实);“诚意正心之要”又分为二,即崇敬畏(修己之敬、事天之敬、遇灾之敬、临民之敬、治事之敬、操存省察之功、规警篇诫之助)与戒逸欲(总论逸欲之戒、沉酒之戒、荒淫之戒、盘游之戒、奢侈之戒);“修身之要”又分为二,即谨言行、正威仪。又列“齐家之要”四目十四子目,即重妃匹(谨选立之道、赖规警之益、明嫡腾之辨、惩废夺之失)、严内治(宫闹内外之分、宫闺预政之戒、内臣忠谨之福、内臣预政之祸)、定国本(建立之计宜蚤、论教之法宜豫、嫡庶之分宜辩、废夺之失宜监)、教戚属(外家谦谨之福、外家骄益之祸)。(真德秀:《大学衍义》,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版。)
[19] 明儒丘濬《大学衍义补》列“治国平天下为纲”12目119个子目:1.正朝廷(总论朝廷之政、正纲纪之常、定名分之等、公赏罚之施、谨号令之颁、广陈言之路);2.正百官(总论任官之道、定职官之分、颁爵禄之制、敬大臣之礼、简侍从之臣、重台谏之任、清入仕之路、全栓选之法、严考课之法、崇推荐之道、戒滥用之失);3.固邦本(总论固本之道、蕃民之生、制民之产、重民之事、宽民之力、憨民之窃、恤民之患、除民之害、择民之长、分民之牧、询民之虞);4.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贡赋之常、经制之义、市朵之令、铜褚之币、山泽之利、征榷之课、傅算之籍、膏算之失、嘈挽之宜、屯营之田);5.明礼乐(总论礼乐之道、礼仪之节、乐律之制、王朝之礼、郡国之礼、家乡之礼);6.秩祭祀(总论祭祀之道、效祀天地之礼、宗朝飨祀之礼、国家常祀之礼、内外群祀之礼、祭告祈祷之礼、释奠先师之礼);7.崇教论(总论教伦之道、设学校以立教、明道学以成教、本经术以为教、一道德以同俗、躬孝悌以敦化、崇师儒以重道、谨好尚以率民、广教化以变俗、严族别以示劝、举赠溢以劝忠);8.备规制(都邑之建、城池之守、宫网之居、囿游之设、冕服之章、玺节之制、舆卫之仪、历象之法、图籍之储、权量之谨、宝玉之器、工作之用、章服之辨、青隶之役、邮传之置、道涂之备);9.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定律令之制、制刑狱之具、明流赎之意、详听断之法、议当原之辟、顺天时之令、谨详漱之议、伸冤抑之情、慎青灾之赦、明复仇之义、简典狱之官、存钦恤之心、戒滥纵之失);10.严武备(总论威武之道、军伍之制、官禁之卫、京辅之屯、郡国之守、本兵之柄、器械之利、牧马之政、简阅之教、将帅之任、出师之律、战陈之法、察军之情、遏盗之机、赏功之格、经武之要);11.驭夷狄(内夏外夷之限、慎德怀远之道、译言宾待之礼、征讨绥和之义、修攘制御之策、守边固围之略、列屯遣戍之制、四方夷落之情、劫诱窃默之失);12.成功化(圣神功化之极)。仅从次目录就可以看到,外王事业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宗教、民族、民俗、历法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内容,包罗万象。(丘濬:《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
[20] “‘礼’在中国,乃是一个独特的概念,为其他任何民族所无。其他民族之‘礼’一般不出礼俗、礼仪、礼貌的范围。而中国之‘礼’,则与政治、法律、宗教、思想、哲学、习俗、文学、艺术,乃至经济、军事,无不结为一个整体,为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名。”(邹昌林:《中国礼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21] 《汉书·艺文志》:“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四家加上《左传》一家就是五家。
[22]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夏比孔子小44岁,当生于公元前508年,传《春秋》学当在公元前430年左右,到汉景帝时近三百多年,其传竟只有五世,所以此传授系统只要稍作时间推理就显得不合情理。徐复观疑戴宏此说源于对《汉书·艺文志·春秋辑略》的误解。班固的说法本自刘歆,刘歆《让太常博士书》目标之一是“申左”,欲立《左传》为学官,所以刘歆在此辑略中突出《左传》“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之旨,以批评“末世口说流行”即五经博士以后的汉儒离开事实根据只凭口头解说的弊端,反对“空言说经”的汉代公羊学末流,为《左传》立于学官张本。戴宏“大概”误刘歆“口说”为“口传”,虚构上述传授系统为公羊张目,以神公羊之说,以便与《左传》争胜。(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199页。)
[23] 《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前书》齐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平赢公,赢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彭祖为《春秋》严氏学,安乐为《春秋》颜氏学,又瑕丘江公传《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比较《汉书》与《后汉书》,第三辈公羊家弟子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赢公,可赢公到底是董仲舒的弟子,还是胡毋生的弟子,或者是两位先师的共同弟子,前、后汉书制造了一个“历史之谜”,有待考证。如果认定“赢公守学不失师法”是真的,这个问题更有考证的必要。同时,与《汉书》还有区别的是,孟卿、眭孟也不是同学关系,而是师生关系。就事实本身的是非而言,也有待考证。只是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公羊家政治哲学,而不是公羊家的传承,在此暂且悬置,待以后专文考证。不过,《后汉书》以《汉书》据,抄错或笔误也有可能。
[24] 《汉书·儒林传》:“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父号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繁杂,及使喜从田王孙受《易》。”这段文字本来是介绍孟卿的儿子孟喜,但可清楚地看到孟卿的学术特长与学术传承。
[25] 《汉书·眭孟传》:“眭弘字孟,鲁国蕃人也。少时好侠,斗鸡走马,长乃变节,从嬴公受《春秋》。以明经为议郎,至符节令。”
[26] 《汉书·疏广传》:“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征为博士、太中大夫。地节三年,立皇太子,选丙吉为太傅,广为少傅,数月,吉迁御史大夫,广徙为太傅。”
[27] 《后汉书·承宫传》:“承宫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为诸生拾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遭天下丧乱,遂将诸生避地汉中,后与妻子之蒙阴山,肆力耕种。禾黍将孰,人有认之者,宫不与计,推之而去,由是显名。三府更辟,皆不应。”
[28] 《后汉书·樊倏传》:“倏字长鱼,谨约有父风。事后母至孝,及母卒,哀思过礼,毁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黄门朝暮送饣亶粥。服阕,就侍中丁恭受《公羊严氏春秋》。建武中,禁网尚阔,诸王既长,各招引宾客,以倏外戚,争遣致之,而倏清静自保,无所交结。及沛王辅事发,贵戚子弟多见收捕,倏以不豫得免。帝崩,倏为复土校尉。”
[29] 《后汉书·儒林列传》:“钟兴字次文,汝南汝阳人也。少从少府丁恭受《严氏春秋》。恭荐兴学行高明,光武召见,问以经义,应对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迁左中郎将。诏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诸侯从兴受章句。封关内侯。兴自以无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训太子及诸王侯,非大功邪?’兴曰:‘臣师于恭。’于是复封恭,而兴遂固辞不受爵,卒于官。”
[30] 《汉书·张霸传》:“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也。年数岁而知孝让,虽出入饮食,自然合礼,乡人号为‘张曾子’。七岁通《春秋》,复欲进余经,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饶为之’,故字曰‘饶’焉。后就长水校尉樊倏受《严氏公羊春秋》,遂博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学焉。”
[31] 《汉书·张楷传》:“楷字公超,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宾客慕之,自父党夙儒,偕造门焉。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黄门及贵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过客往来之利。楷疾其如此,辄徙避之。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者,辄还乡里。司隶举茂才,除长陵令,不至官。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连辟,举贤良方正,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