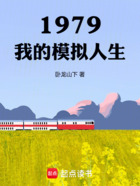
第45章 当头一棒
就这样,清凉甜美的冰棍,成了这个炎炎夏日里刘庄大队最受欢迎的“时髦货”。孩子们盼着卖冰棍的婶子经过家门口,大人们在田间地头休息时也愿意花几分钱买根解解暑气。一时间,“李婶子家卖冰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大队,甚至连邻近的公社都有所耳闻。
冰棍生意渐渐走上了正轨,每天都能带来稳定可观的收入,虽然数额不大,但在当时已属不易,李志华和王秀芬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虽然每次赚的钱换算下来也就不到一块,多的时候能有一块出头,数额并不算惊人,但在1979年的农村,这已经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稳定收入了。
要知道,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里辛苦一天,也才挣七八个工分,折合下来不过四五毛钱。
李方旺虽然也需要定期去县城取货,但大部分时间还是解放了出来。
……
时间一天天过去,婶婶王秀芬的冰棍生意做得是顺风顺水,越来越熟练。她每天出门,傍晚时分准时带着空箱子和一兜零钱回来,脸上的笑容也越发灿烂。冰棍带来的稳定收入,让这个家的生活肉眼可见地改善着,也让王秀芬在村里的“知名度”和自信心都大大提升。
然而,与冰棍生意的顺利形成对比的是,瓜子生意并不顺利。
按照计划,第一批一百斤生葵花籽很快就收了回来。张大山叔叔也是尽心尽力,带着几个妇女同志,在自家院子里支起大锅,反复试验火候和咸淡。
虽然味道始终达不到那种让人上瘾的程度,但比起最初家常的味道,确实又精进了不少,至少在村里人尝起来,觉得“嗯,比自家炒的好吃多了”。
第一批炒好的瓜子用油纸简单包成小包,定价也确实比集市上便宜了一毛钱,五毛钱一斤。李志华和李方旺都觉得,这价格实惠,味道也不赖,肯定能像冰棍一样受欢迎。
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李方旺亲自上阵,带着几包瓜子,先在自家的三队开始推广。乡亲们看到是李方旺来了,又听说是队里搞的新项目,都挺给面子。关系好的,像张广飞家,二话不说就买了一斤。其他相熟的邻居,多少也买个半斤或者几两尝尝鲜,算是捧个人场。
可当李方旺走到那些平日里交情一般,或者家境确实比较困难的乡亲家门口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瓜子啊?闻着挺香的……不过家里还有前两天刚炒的花生呢,就不买了。”
“五毛钱一斤?是比集上便宜点……可家里实在没闲钱买这个零嘴吃……”
“方旺啊,你这瓜子是好,可这东西不顶饿啊,还是留着钱买点盐巴实在。”
大多数人都是笑着摆手,客气地拒绝了。任凭李方旺说得天花乱坠,他们最多也就是捏几颗尝尝,真要掏钱买,却都犹豫了。
李方旺不死心,又骑着车跑到了一队和二队去推销。结果大同小异,除了少数几户家里条件稍好或者好奇尝鲜的人买了一点,大部分人家都是敬而远之。
一天下来,李方旺累得够呛,可带出去的一大袋瓜子,只卖掉了不到十分之一。剩下的瓜子沉甸甸地压在自行车后座上,也压在了他的心头。
接下来的几天,情况并没有好转。婶婶王秀芬也尝试着在卖冰棍的时候顺带推销瓜子,效果同样不佳。偶尔有人买上一小包,也多半是看在冰棍的面子上,或者禁不住孩子磨。
这与冰棍销售的火爆场面,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
李志华看着库房里堆着的那几十斤卖不出去的炒瓜子,急得直搓手:“方旺,这……这是咋回事啊?按说这瓜子味道也不差,价钱也便宜,咋就卖不动呢?”
妇女主任孙桂芳和负责炒制的张大山等人,也有些泄气。辛辛苦苦炒出来的东西卖不掉,大家心里都不好受。
李方旺没有急着下结论,他知道问题肯定出在哪里,但他需要亲自去验证。
接下来的两天,他没有再出去推销瓜子,而是在大队里,尤其是在傍晚纳凉或者农闲的时候,仔细观察着乡亲们的日常生活。
很快,他就找到了答案。
正如他之前隐约感觉到的那样,问题出在了“替代品”和“购买力”上。
他发现,虽然很少有人家会特意去炒瓜子,但是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农闲时炒花生!
花生也是自家地里种的,或者跟邻居换一点,成本极低。炒熟的花生,香脆可口,同样是打发时间、招待客人的好零嘴。
对于手里余钱极其有限的农民来说,既然有免费或者成本极低的花生可以吃,为什么还要花五毛钱去买功能几乎一样的瓜子呢?
五毛钱,在这个年代,可以买好几斤红薯,或者扯上半尺布了!大家宁愿把这点钱花在更实在的地方。
而冰棍则完全不同,冰凉解暑,这是花生、瓜子甚至井水都无法完全替代的独特体验。而且,糖和冰块,都是相对稀缺的,普通农户家里根本无法自制。正因为其独特性和稀缺性,乡亲们才愿意偶尔花几分钱去购买那种难得的清凉和甜蜜。
想明白了这一点,李方旺心中豁然开朗,但也有些哭笑不得。
自己还是想当然了。
李方旺现在猜测,瓜子大王大概率不是在村里卖的,而是在县里,甚至是市里卖的。
县城、市里的居民,虽然也未必富裕,但比起农村,他们的现金收入普遍要高一些,购买零食的可能性也更大。而且,城镇居民家里没有地种花生瓜子,想吃零嘴基本上就只能靠买的。这时候,瓜子就有市场了。
李方旺拿起一颗瓜子,在手里掂量着,默默思忖,“真正有潜力的市场,应该是在县城,甚至更远的地方。”
……
夜幕降临,李家小院里,昏黄的油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王秀芬满面春风地回到了家。
她一边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一边麻利地收拾着今天挣来的零钱,脸上的笑容比傍晚的彩霞还要灿烂。
“当家的,方旺!今天卖得可好了!一队的王婆婆家办喜事,一下子就跟我这儿订了二十根糖水冰棍呢!还有啊,二队的张木匠,说他家娃儿馋得不行,以后每天都给我留两根奶油的!”她兴奋地分享着今天的“战绩”,仿佛有说不完的喜悦。
李方旺笑着听着,心里也替婶婶高兴。
然而,坐在桌边默默抽着旱烟的李志华,脸上却不见多少笑容,反而眉头紧锁,神色间带着几分忧虑。
王秀芬察觉到了丈夫的异样,脸上的笑容也收敛了一些,关切地问道:“他爹,你这是咋了?遇上啥愁事了?是不是养鸡场那边不顺心?”
李志华吐出一口烟圈,摇了摇头,拿起王秀芬特意留给他的一根糖水冰棍,慢慢地吃着,冰凉的感觉似乎也无法驱散他心头的烦闷。
“养鸡场那边挺好的,鸡蛋卖得不错,鸡苗也长得壮实。”他叹了口气,看向李方旺,“是瓜子的事。”
王秀芬一听,也想起了那堆在库房里卖不动的瓜子,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担忧地问:“瓜子……还是卖不出去?”
李志华点点头,神色凝重:“今天下午,我去队里转了转,好几个人都跟我打听瓜子的事呢。明面上是关心,可那话里话外的意思啊,都是担心这瓜子砸手里,亏了本钱。毕竟,当初买生瓜子可是挪用了队里养鸡场卖鸡蛋的钱,虽然不多,但也是集体的钱啊!”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了些,带着几分无奈和气愤:“尤其是刘记富和刘铁柱那几个!我听人说,他们俩这两天没少在背后嘀咕,说什么‘瞎折腾’、‘就知道听年轻人的,早晚把集体的钱败光’!还说当初就不该同意搞这个瓜子项目!我看啊,他们就是巴不得这事儿黄了,好看我的笑话!”
李志华越说越气,手里的冰棍棍儿都快被他捏断了:“现在瓜子卖不出去,队里不少人心里都开始犯嘀咕了。到时候,别说搞别的了,就连养鸡场那边,都可能有人跳出来说三道四!”
王秀芬听着丈夫的话,心也跟着揪了起来。她知道丈夫这个队长当得不容易,村里的人情世故复杂得很,一步走错就可能被人抓住把柄。她放下手里的钱,担忧地看向李方旺:“方旺啊,这可咋办啊?要不……要不咱们把那些瓜子降降价?或者干脆成本价处理了?先把本钱收回来再说?”
李方旺一直安静地听着叔叔的讲述和婶婶的担忧,脸上的表情却异常平静。他早就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瓜子在村里卖不动,必然会引发一些人的担忧和非议,而刘记富、刘铁柱这样原本就心怀不满的人,更会借机煽风点火,制造舆论压力。
他放下手中的碗筷,看着眉头紧锁的叔叔和一脸焦虑的婶婶,缓缓开口,语气沉稳而自信:“叔,婶,你们先别着急。”
他拿起桌上的一颗瓜子,轻轻嗑开,将瓜子仁放在手心:“瓜子卖不出去,不是因为东西不好,也不是因为价格贵,而是因为咱们找错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