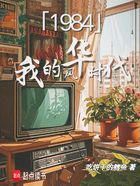
第15章 这个作者是懂政治的
听云楠说买电视机,云建功瞪着大眼珠子凑了过来:“二哥,你睡迷糊了吧?”
“三儿,你把脏手从我身上拿开”,一想起云建功抠脚丫子一幕,云楠差点吐了出来。
“都别闹了”李嘉丽制止两人争吵,全神贯注的听着收音机的报幕。
“下面请大家欣赏黄梅戏《女驸马》,表演者:马栏。”
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提到86版西游记,唐僧母亲的演员一定会有深刻印象,那种清新脱俗的美,秒杀一众整容脸。
“黄梅戏这老掉牙的玩意儿,咿咿呀呀难听死了,哪有《东北的冬》好听,不听了,我抽根烟去。”
“老三说的对,我也喜欢《东北的冬》这种歌,接地气。”
云建业趿拉着棉鞋也跟出去抽烟,反倒是李嘉丽缓缓闭上眼睛,听的津津有味。
黄梅戏这种传统曲调只能满足老一辈的欣赏需求,确实很让现在的年轻人产生情感共鸣。
云楠好像想起了什么,脸上浮出一丝兴奋。
不过要是改编成流行歌曲,在保持传统黄梅戏音乐特色的基础上,将现代音乐进行融合,肯定别有一番韵味。
再说创作难度也不是很大,只要初心不改,我致敬一下慕容姑娘不就完了吗?
云楠想起前世上大学时候,教《古代文论》的讲师一到课间就放《黄梅戏》这首歌,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喜欢,倒是现在便宜了云楠。
春节期间,云楠每天三个饱两个倒,别提多滋润了,足足胖了5斤。
辽省文坛一哥《鸭绿江》杂志社却是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气息,与春节喜气洋洋格格不入。
大初五杂志社全员上班,怨声载道再正常不过了。
主编樊城垂头丧气的看着财务报表。
《鸭绿江》杂志创刊于 1946年,其前身为《东北文艺》。繁荣时期被誉为文学期刊的“四小名旦”之一,在东北乃至国内整个文坛都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胖胖的老莫曾经也在《鸭绿江》发表过文章。
主编樊城也是个能人,1981年为响应国家号召,主动带领杂志社进行市场化改革,实行企业化运营,完全自负盈亏。曾一度创下50万销量的壮举。
可随着国内文学热的兴起,新老杂志社雨如露春笋般崛起,竞争压力过大,这个声名远扬的老牌期刊便越发萧条,去年月平均销量仅万余。
当时杂志3毛5一本,樊城一算,上个月又亏了。
好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死撑着也用不了多久了。
他随手拿起旁边放着的《BJ文学》翻了起来。
“这篇《星星》倒是写的不错,如果结尾能够再光明些,不失为一篇佳作啊”,樊城又翻了翻,“作者叫余桦,没听过,应该是个新人,真不错。”
许久,他无助的靠在椅子上,拳头轻轻捶打额头:“哎,还是青年后备力量不足啊,你看看人家《星星》这篇文章写的多生动,读者怎么可能不喜欢。
文章没问题,市场也没问题,问题就出在杂志社身上。
社里这帮老编辑还是老脑筋儿,文学本来就是多元化的,博众家之所长,总是喜欢用那些革命、斗争的样板文学,文章空泛,一点也不接地气,读者能喜欢吗?
为什么我们就没有优秀的青年作家。”
文字编辑办公室,一个行动迟缓,戴着老花镜,满头白发的老者拿着铅笔一字一句的校对文章。
“张老师,这篇文章您怎么给毙掉了?我觉得写的不错。”
张继忠是小说组组长、文字编辑。
老张缓缓抬起头,又无奈的晃了晃脑袋:“小许,你自己看看这个作者写的什么玩意儿,充满了腐朽思想,难道我们要向大众传递资产阶级思想吗?
再说一个年轻女孩,不好好读书,跑去当模特。这就是不正之风,我能让它发表毒害群众吗?”
“张老师,时代在变革,你不能总用老眼光看待事情。
这篇小说通过不同年龄的女孩成长经历,塑造了国家复兴之路,更是深刻剖析了改革过程中人们需要经历的转变,很有引导性,可以说是艺术价值很高。
而且文笔洗练含蓄,人物塑造的细腻生动,看得出作者很擅长人物形象塑造,真的很不错,您再考虑考虑?”
张继忠一挥手推开了文章,“我说不行就不行。”
阿兰咬了咬嘴唇,满是不理解的转身出去。
“这破杂志社我是呆够了,好像一群清朝遗老遗少了,老顽固。”
“阿兰,你来一下。”主编樊城喊她。
阿兰有些心虚:“樊主编,您...您有事吗?”
樊城在门口停了半天,饶有兴致的看着眼前的小姑娘。
“把你手里的文章给我看一下。”
“主编,其实这篇小说写的新颖......”
樊城笑了笑,没说什么回到办公室。
“《你不可改变我》,很有意思的名字,看来作者的个人风格很强烈。”
半口杀猪刀?
樊城看到这个笔名差点眼把珠子瞪了出来。
“朋友给我介绍令凯时说:“她是个古怪的女孩。”
开篇第一句话,樊城被死死抓住眼球,他感受到作者的与众不同。
屋子里静悄悄的,很快他便沉迷文章之中,无法自拔。
文中“我”是一个秉持传统观念的人,然而“我”的好朋友,一个16岁特立独行的令凯,她抽烟、会把头发剃得很短,还是青年宫三画室的模特儿,这让“我”感到意外和担忧。
此时樊城脑子里勾勒出一个叛逆少女的形象。
“我”试图劝说令凯改变,但她却认为自己有能力平衡学业与工作,并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文章最后定格在令凯在沙滩上拍牛奶广告,而“我”在街对面远远地看着令凯,一辆汽车疾驰而去,阻断了“我”的视线,也寓意着“我”和令凯对生活态度的不同选择。
“啪”,桌子上的茶杯盖都被震掉了,“此子绝非常人。”
叙事手法很高明,看起凌乱散漫,却提高了文章的层次感;结构上也不是传统文学的起承转合;文学表达上更是彰显了时代精神和人物内心感受。
文章却无处不在表达时代的变革与冲突。并且还向人们强调了自我价值选择的自由度,这种人生态度值得去讨论。
这与传统文学的写作简直就是大相径庭,让人耳目一新。
这绝对是一种全新的写作模式,简直太棒了。
樊城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转圈圈来消化情绪。
“这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神人,以前没听说过。”
态度鲜明、主旨清晰,将改开时期的不同思想激烈交锋浓缩成两个女孩交往过程展现出来,笔法很老练。人物代入感极强,很容易引起大众的反思与共鸣。
樊城实在没忍住,爆了句粗口:“写的真特喵的好。”
文学就在在批判和尝试中不断创新,永远畏手畏脚是写不出好东西的。
“就是文章流露的某些价值观有点太激进了。”樊城有点犹豫。
还有尺度也是个问题。
改开初期,内地人们思想还特别保守,可想而是这种文章出来,将在社会上引发怎样的舆论思潮,弄不好得被吐沫星子淹死。
有玩埋汰的,扣你个腐朽资产阶级的帽子都可能。
樊城享受过文坛璀璨,也见识过它的肮脏。
他现在有些踌躇不决,无论从笔力、人物形象、时代变革的论述,《你不可改变我》无疑是篇好文章。但作为杂志社主编,他不得不考虑现实问题。
鸭绿江经不起更大的风浪了。
“改革开放、特区发展多好的题材啊”樊城默默地念叨着。
“等等。”
他想起来什么事,赶紧翻出1月份的《京城时报》,看了半天,呼吸声越来越沉重。
“槽,原来这个作者是懂政治的。”他面红耳赤,难掩激动。
“老人家刚刚南巡,文章的态度是积极地,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篇文章最起码核心价值观是正确的,完全契合国家发展的主旋律,宣传改开的伟大成果嘛。相对之下,其他的那些只能算是瑕疵。
《伤痕》小说如果放在78年之前,枪毙十次算是人道主义。但最后不还是开创了新的文学流派。
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
从政治角度去看,《你不可改变我》已经赢麻了。
这相当于高考前押中了命题作文,一飞冲天也绝不是没可能。
你再有意见,敢对国家发展规划评头论足吗?
除非你想唱铁窗泪!
激动后的沉寂,他越想越不对劲儿。他从抽屉里翻出戒了很久的烟,香烟很干、很硬,抽一口呛的直咳嗽。
如果说当初靠着《伤痕》小说,创造出伤痕流派,那这篇小说从文学价值上来讲,高出不只是一个层次,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真想和这个作者当面交流一番。如果能把里面的小问题改一改那就更好了。
樊城靠在椅子上,脑子里突然萌生出之前张继忠与阿兰的对话,不由的愤恨起来。
“看来社里不是没有好文章,是特喵的有人挡我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