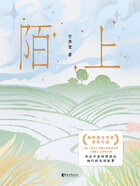
楔子
芳村这地方,怎么说呢,村子不大,却也有不少是非。
比方说,谁家的鸡不出息,把蛋生在人家的窝里;比方说,谁家的猪跑出来,拱了人家的菜地;比方说,谁家的大白鹅吃了大田里的麦苗,结果死了。这些,都少不得一场是非。人们红了脖子赤了脸,也有因此两家结下怨的,总有十天或者半月,相互不理。孩子们也得到叮嘱,不许去那一家,不许跟那家的孩子玩。可是,孩子们哪里管那么多!认真记了两天,到了第三天傍晚,大孩子们一招呼,早忘了大人的告诫,又兴头头地去了。
算起来,芳村也只有百十户人家,倒有三大姓。刘家,是第一大姓,然后是翟家,然后是符家。其他的小姓也有,零零碎碎的,提不起来了。
据说,刘家的祖上,曾经在朝里做官,名重一时。方圆百里,有谁不知道芳村的刘家?当然了,那时候,芳村或许并不叫芳村。究竟叫作什么,就只有去问老见德了。老见德是村子里的秀才,最会讲古。后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刘家的祖上被罢了官,这一支就败落下来了。另一支呢,却渐渐枝繁叶茂。读书的,必定高中;做官的呢,仕途通达;经商的也有,种地的也有,不论如何,都算得上芳村的好人家。有人就说了,这是老刘家坟地风水好。那棵大柏子树,华盖似的!也有人说,枕着大河套,那襟抱!再没有不发达的。
除了刘家,便是翟家了。这个翟家有点奇怪。芳村有两个翟家,大翟家和小翟家。大翟家住村南,小翟家住村北。大翟家人多,院房大;小翟家人少,院房小。也不知道,这两个翟家,祖上有没有瓜葛,有何瓜葛,后来如何劈了户,分了院房。有说原是一宗的,兄弟两个,各自分枝伸杈,开花结果,后来两支闹了纠纷,再不往来了。也有说是两回事,一家是芳村土生的,另一家是外路迁来的,两方为了争长短,打了一架,败了的一方随了翟姓。也有人把这事去问老见德,究竟也没有问个分明,便不了了之了。总之是,大翟家和小翟家,竟像是完全不相干的,不通庆吊往来,见了面,和气倒是和气的,只是,却与一般村人无二了。
符家呢,在芳村,同刘翟两家相比,算是小姓了。符家大多住村子的东头。怎么说呢,符家院房不大,却出读书人。冬闲时节,天冷,夜正长,人们烤着炉子,说闲话,说着说着,就说起了符家。有心的人,还能够扳着指头,一个一个地数一数,列一列,竟都是有名有姓的。听的人不免惊叹起来,问真的吗,老天爷,真的吗?数说的人就有些不悦,以为没有得到信任。听的人察其颜色,为自己的无知内疚了,赶忙教训满地乱跑的孩子,光知道疯玩——看不好好念书!
芳村的人们,孩子生下来,往往只有小名儿。民间说法,小名儿越是低贱,越好养活。自古都是这样的。猫啊狗啊,小臭子死不了,小盆子破碗子,就那么随口一叫,说不定,就叫开了。到了念书的时候,父母才想起来,得有个大号。可这大号,也只有教书先生专用,下了学,还照样是二蛋二蛋地叫。等这孩子辍了学,那大号就渐渐被忘记了。后来,娶妻生子,顶门立户,欠了人家肉铺的钱,小黑板上面依然写着,二蛋,某年某月某日,五块四毛。有时候,村里的大喇叭喊,刘秉正,刘秉正,来拿信,来拿信。人们就愣一愣,一时不知道这刘秉正是谁。就连他本人,也只顾在田里埋头薅草,听了半晌,才忽然想起来,一拍脑袋,原来那个刘秉正就是他自己,慌忙扔下锄头去了大队部,涨红着一张脸,很为自己庄严的大号难为情了。
符家的那些念书的弟子,当然个个都有大号了。在芳村,他们是坏枣、笨梨、小嘎咕,说着芳村的土话,在外面,他们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撇着城里人的洋腔,过着城里人的生活。只是有一样,符家的这些读书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竟把自己的姓都慢慢改了。改作什么呢,把上面的竹字头省掉了,写作付。这件事,本来也没有人在意。家里外面,完全不相干的。偏巧有一回,符家外面的一个孩子,给家里寄钱。拿着单子去取,结果没有成功。人家说名字与身份证上的不符。符振华,付振华,当然不是同一个人了。这件事让做父亲的很不高兴。这还得了!姓氏都更改了,还有祖宗王法没有了!然而,看在一沓厚厚的钞票的面子上,慢慢地也就把自己劝开了。这件事,被芳村人闲话了一阵子,也便没有人提起来了。怎么说呢,终归不是什么大事。
认真想来,芳村的街道,竟都没有名字。人们喜欢分了方向:东头的,西头的,南头的,北头的。比方说,立秋家生了个胖小子。有人问,哪个立秋?说话的把下巴朝西面点一点,说哪个立秋,西头的立秋嘛。这个中心点,自然指的是大队部。大队部这一条街,算是大街了。而大队部的十字街,当然是芳村最繁华的地方了。小卖部、磨坊、药铺、烧饼摊子……要什么有什么。
小卖部,那时候,叫作供销社。一个白地红字的大牌子,上面写着,芳村供销社。很威风了。可是,人们总不那么叫。人们叫作社。人们说,去社里买半斤盐。社里新来了瓶酒,远没有本地烧烈性。社里的柜台极高,小孩子们,只能央大人抱着,看一看里面的橘子糖还在不在。还有那种黑枣,简直能把人的牙甜掉,却不能够多吃,吃多了,便拉不出屎来。还有那种陀螺,染着五彩的颜色,比哥哥自己做的,不知道要好看多少倍。小孩子们被大人抱着,一双眼睛,简直是不够使了。待到大人不耐烦了,索性就把孩子放在柜台上,任他们看个够。里面的人就说话了,不能放孩子,这柜台不能放孩子。是反对的意思,却也不怎么认真。公家的社,怎么就不能了?倘若是夏天还好,若是冬天,那水泥台子凉冰冰的,贴着孩子的屁股,也不觉得冷。旁人看了,倒哧拉一声笑了,说,大人的脸,孩子的屁股。芳村的孩子们,开裆裤要穿到好几岁,方便。尤其是冬天,厚墩墩的棉衣裳,十分笨重,尿紧的时候,往往就来不及了。
柜台高了,柜台里面的人,就显得格外神气。很多孩子的理想,便是长大了到社里当售货员。大人们听了,便笑,以为是在说梦话,也不当作一回事。
磨坊就在供销社旁边。机器轰隆隆响着,说话听不清,都得扯着嗓门喊。磨坊里的人忙活半天,出来透口气,倒把人们吓一跳。白头发,白胡子,浑身白,连眉毛睫毛都是白的了——简直是雪堆出来的人!
芳村这地方,把医生不叫医生,叫作先生。药铺里的先生,在村子里,是有身份的人物。这一辈子,谁敢担保不生病呢?
这一家药铺,是刘姓,算是祖传了。一家三代,都懂医,有世家的意思。尤其是看小孩,据说很灵验。名气很大。方圆几十里,谁不知道芳村的刘家药铺呢。当然了,也不光是看小孩。大人们头疼脑热,也都来这里抓药。可偏偏是,刘家药铺的先生性子极慢,芳村人叫作“肉”,最是能够磨折人的脾气。又爱酒。常常是,都日上三竿了,药铺的门上还挂着锁。有性急的人,就只有去家里找。果然是头天夜里喝了酒,还醉在炕上。女人一趟一趟地叫,一面安慰着来访的人。总得要等他慢慢醒了酒,在被窝里吃过早饭,然后,趴在炕头上吸上一锅烟,才打算起床的事。脾气急的人,转磨一般,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孩子呢,病着,天又冷,哭咧咧的,一声长,一声短。哭声像一只小手,揉搓着大人的心。然而,有什么办法呢,先生就是这样的“肉”。好在,芳村的人,也都习惯了。
烧饼摊子生意不大好。有谁平白无故的,买烧饼吃呢?除非,家里来了客。芳村人,把客不叫客,叫且。待且是大事。吃什么呢?饺子吧,太费事。炖菜呢,菜里总得见些肉,才像话。不如就吃烧饼吧。换上半箩烧饼,再搅上一锅糊汤,顶多,挥霍一下,索性飞上两个鸡蛋花,热热闹闹的,也算顿待且的饭吧。
可平日里,人们吃得最多的,是饼子。玉米面饼子。平常人家,做得粗糙。玉米糁子,拿沸水搅了,团一个,往锅里的箅子上放一个。旁边须得准备些凉水,手不停地蘸一蘸,为了降温。女人们的手,简直是铁手,不怕烫呢。也有讲究的。拿一个锅圈撑着,把饼子贴在锅壁上,叫作贴饼子。这样贴出来的饼子,有一面呈金红色,又脆又香,小孩子们尤其喜欢。刚出锅的热饼子,掰开了,涂上猪油,撒上些细盐,极香。奢侈些的,会把过年留下的腌肉拿出来,肥多瘦少,夹在滚烫的饼子里,咬一口,命都不要了。
当然了,也有六指家的馒头车子,在村子里走街串巷。六指吹着一只牛角,呜呜呜,呜呜呜,人们听见了,就知道是馒头车子过来了。六指家的馒头又白又胖,据说拿硫黄熏过,有淡淡的味道,上面一律点着大红的胭脂,十分俊俏。有人不买,却要凑过去,把馒头簸箩揭开,指着那胭脂,跟怀里的孩子赞叹,大白馒头,胭脂红——
豆腐七十使的是木头梆子,帮帮帮,帮帮帮,也并不吆喝,人们只听见这梆子声,便知道,是做饭的时候了。
芳村人,做饭总是大事。见了面,也一贯喜欢向人家打听,晌午吃吗饭?
也有摇拨浪鼓的,是走庄串户的货郎。推着独轮货车,一路走,一路摇,拨朗朗,拨朗朗,拨朗拨朗朗。女人们听见了,赶紧把做鞋做衣裳的碎布头拿出来,换上两根针,换上一绺花花绿绿的丝线。她们褒贬着那丝线的成色,非让那货郎再搭上一枚顶针。小孩子们也跑过来,最令他们牵挂的,是一种江米糖球,又酥又甜,能把人香个跟头。他们的母亲为了顶针正和那货郎争执不下,就顺坡下驴,把攥得热乎乎的顶针当啷一扔,伸手抓了一个江米糖球,塞给孩子,说算了算了,小气鬼!这个时候,那货郎也只有叹一声,由她去了。
芳村这地方,最讲究节气。
过年就不用说了。
在乡下,过年是最隆重的节气。
过年之后,往后数吧。
正月初五,俗称破五。为什么叫破五呢?民间的说法,自从大年三十开始,屋子里、院子里,那些个花生壳啊,鞭炮屑啊,都不能动,不能清扫。扫了,就把一年的财运扫跑了。任凭人们踩上去,擦擦擦,擦擦擦,是喜庆的意思了。到了初五这一天,一大早,通常是男主人,就起来了。起来做什么呢,起来点炮。点炮做什么?点炮把“穷”吓跑。传说,“穷”这样东西,最怕鞭炮。人们一大早起来,噼噼啪啪点上一阵子鞭炮,然后赶紧挥起扫帚扫院子,是要把“穷”赶出去。谁家起得越早,点炮越响,越是吉祥。因此,初五这一天,也叫“五穷日”。这一天早晨的鞭炮,竟同大年初一有一比。
初五过后,是初十。
民间传说,正月初十,是老鼠嫁女的日子。这一天晚上,小孩子们往往一放下饭碗,就慌忙往豆腐七十家跑。磨坊的院子里,老椿树下,有一个磨盘,想是废弃不用了,一直搁在那里。小孩子们你挤我,我挤你,争着要趴在那磨眼上往里看。据大人们说,从磨眼里,可以看到老鼠嫁女的情形。老鼠嫁女,一定也是同芳村一样,很热闹很排场吧。磨眼里黑洞洞的,没有花轿,没有鞭炮,没有唢呐。什么也没有。心急的孩子跑去问大人,说是得要半夜十二点呢。等着等着,便失去了耐心。第二天,问起来,果然有讲得有声有色的。没有看到的便十分懊悔,发誓明年再不肯早睡了。
正月十五,芳村是没有花灯的,却唱戏。
有支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请闺女,叫女婿,外甥狗儿,你也去……是哄小孩子的时候经常唱的。拉着孩子的两只小胳膊,一送一收,一收一送。孩子觉出了趣味,咯咯笑起来了。
也不单是闺女女婿。七大姑八大姨,远亲近戚,早在年前就说好了的。过年时的腌肉还特意留着。腌豆腐也有。灌肠丸子、卷子花卷,也都在瓦罐里冻着。饺子呢,是留给闺女的。这地方的风俗,出门的闺女,要吃娘家大年初一的饺子。还有一只鸡,埋在枣树下的雪堆里。趁着过十五,得赶快炖了它。
戏台子就搭在十字街上。是芳村的戏班子。方圆几十里,谁不知道芳村的老来祥,不知道老来祥的戏班子?戏台子上,披红挂绿,咿咿呀呀地唱。戏台子下面,人们有立着的,有坐着的,袖着手,一开口,哈出一团白气。孩子们跑来跑去,锐叫着,手里举着糖葫芦,脸蛋子冻得通红。姑娘们穿着新衣裳,决不肯一个人孤单单地在街上走过,去看戏呢,更不肯了,一定要有几个女伴,挽着手,勾肩搭背,眼睛瞟着戏台子,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一张脸却忽然飞红了。妇人们则要从容得多了,嗑着瓜子,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说家常。也有人指着戏台子上那正在唱着的花脸,叫葵花葵花,看你公公,倒挺卖力气——葵花就笑骂一句,有些难为情了。上了年纪的人,往往是格外认真的。河北梆子、丝弦,百听不厌。听着听着,就入了戏,全然忘记了,那个楚楚可怜的小旦,满头珠翠,竟是自己的东邻,两家刚刚闹了纠纷,为了那只跳窝的白翎子鸡。
正月十六,游百病。这一天,人们要到大河套,把百病扔在那里。要是天气晴好,村路上都是来来往往的人。阳光软软地泼下来,笑语喧哗。路旁的杨树,虽然依旧是光秃秃的,却总让人感觉有什么马上要毛茸茸地拱出来。早春二月,一霎眼,就到了。
二月二,俗称小年。这一天,新媳妇要给本院的小孩子们送新鞋。一人一双,全是出自新媳妇之手,就有展示女红功夫的意思了。心灵手巧的新媳妇,自然是难不倒的。新鞋子结实漂亮,舒适合脚,少不得赢得一片叫好,巧媳妇的口碑,自此在村子里慢慢流传。眼拙手笨的新媳妇呢,便十分忐忑了,偷偷地央求姐妹们,在娘家延挨着,横竖不肯早回来,或者,越性装了病,也是有的。为此,芳村的女人们,从小就被反复告诫,针线一定要好。否则,将来怎么做人呢?还要扳着指头,举出一串案子来,东家的三嫂、西家的二娘,都是活生生现成的。
这个节气,还要吃一种食物,叫作“闲食”。把窖里藏的大萝卜拿出来,在擦床上,细细地擦成丝,加在面粉搅成的糊里。往铛子里倒上油,薄薄地摊开。吃闲食须得蘸汁,酱油、醋、蒜泥、麻油,萝卜淡淡的香气。那种滋味,怎么说呢,是二月二的滋味。
过了二月二,年就算过完了。
年过完了,却留下了很多鸳鸯账。比方说,东家的姑娘说婆家,觉得那一家的小姑子多了。大姑子多了婆婆多,小姑子多了是非多。老话儿有老话儿的道理。比方说,西家的小子相媳妇,一眼便看中了,模样脾性样样好,只是有一样,那姑娘原来瞒了年纪,属相便不合了。鸡猴不到头。这怎么得了!当然也有称愿的。郎情妾意,花好月圆。很多时候,鸳鸯账也是糊涂账,一笔一笔的,只等这一年的光阴里人们慢慢勾画。
芳村有句俗话,寒食寒食,不脱棉衣没廉耻。
寒食节的时候,大地颤巍巍地醒过来了。阳光明亮,让人不由得眯起眼睛。远远地,麦田里仿佛笼着一层薄薄的雾霭,走近一看,却又不是。空气里湿润润的,夹杂着泥土的腥气,还有粪肥淡淡的味道,让人忍不住鼻子痒痒。也不知道是谁,忽然就打了个痛快的喷嚏,一面自言自语,咦,谁想我了这是!
寒食节,村路上来来往往的,是上坟烧纸的人。
到了耕牛遍地走的时候了。人们都忙起来了。
麦子浇过一遍水。
麦子浇过二遍水。
浇过三遍水的时候,麦子开始抽穗了。
浇四遍水的时候,麦子开始灌浆了。
麦芒毛刺刺的,抚在手掌心里,麻酥酥的痒。有性急的孩子,禁不住诱惑,采上一大把,塞进母亲的灶膛里。麦穗烧得黑乎乎的,搓开来,麦仁儿却是嫩绿的,白色的汁水,有一股微甜的清香。
麦田飞芒炸穗的时候,端午节到了。
端午节,家家户户包粽子。粽子叶是早就泡好了的。还有黄米,还有红枣。黄米是自家田里种的,红枣是自家树上结的,粽子叶是买来的。粽子包好了,在大锅里,煮上一夜。这个时候,得烧些好柴了。玉米轴、棉花秸、豆秸,都是好柴。风箱呱嗒呱嗒响,香气慢慢弥漫开来,孩子们便不肯去睡,被大人哄劝着,方才不放心地合上眼。第二天一大早,不等催叫,便早早起来了。村子里到处弥漫着粽子的香气。孩子们被母亲打发着,提着粽子,去东家送三个,去西家送五个。这家的粽子缠着红线,那家的粽子缠着绿线。虽说是一样的粽子,滋味真的是不一样呢。
粽子还没有吃完,是非就来了。谁家的媳妇小气,只给了婆婆三个粽子;谁家的媳妇,竟然一个都没有给。这闲话传到媳妇耳朵里,便认定婆婆在外宣讲了她的不是。于是立在院子当中,打鸡骂狗,把大白鹅撵得嘎嘎乱叫。东屋的婆婆便坐不住了,也并不出来,只拍打着炕沿,哭起了死去的那个狠心的老东西。做儿子的从外面回来,一进门,见了这种情形,便明白了一二。劝一劝这头,哄一哄那端,都不奏效,倒越发不可收了。婆婆数说着这一世的艰难,一定要从儿子出世说起。屎一把,尿一把,都是忘不了的。媳妇呢,朝着芦花鸡就是一脚,啐道,咯答答咯答答,就怕别人听不见。托生个母的,谁个不下蛋,哪个不养崽?芦花鸡受了委屈,飞快地跑了。婆婆的哭声更曲折了。做儿子的把门一摔,闹吧,闹!丢人现眼!索性躲出去了。
出门看见本院的光棍儿二爷,正想诉一诉烦恼,却见二爷也是一脑门儿的官司,因想起了二爷冷锅凉炕的光景,便把嘴边的话咽下去了。
田野里黄澄澄的,金子一般。
七月十五,也叫作鬼节。芳村这地方,要给死去的亲人上坟。一年中,上坟统共有三回,寒食一回,七月十五一回,十月初一送寒衣,也是一回。大年初一清早也要上坟,却仅限于家族中的男人。祭日或者周年,就不算了。一年当中的上坟,最隆重的,要数七月十五了。
通常是,一进七月,女人们便开始准备了。从集上买来黄表纸,买来香烛,买来金色银色的锡箔。女人们忙着裁纸、印票子、捏锡箔。金元宝银元宝,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很繁华的景象。
这时节,庄稼地正深。玉米吐着缨子,棉花结出累累的青桃子,谁家的谷田里立着一个草人儿,害得麻雀们叽叽喳喳,疑神疑鬼。女人们提着香烛纸马,一路上说着家常。到了坟前,把坟头的草清一清,就开始烧纸了。香烛点起来,纸灰飞舞。女人们跪在坟前,不免要跟亲人叙一叙家里的光景。老大家新添了孩子,大胖小子,小老虎一般。老二呢,刚娶了人,南头狗臭家的四闺女。添丁进口的大事,跟你说一声。说着说着,又想起了种种不如意,终于忍不住,哭起来。数说亲人的狠心、自己的不易,仿佛所有的委屈烦难,都要在亲人面前诉一诉。旁边的姊妹妯娌听了,连忙止住悲声,百般劝慰。地上的那一个,却越发伤心起来。旁边的人渐渐听出来了,话里话外,绵里藏针,有些锋芒,竟然是对着自己的。便也越性坐下,拉开架势,一唱一和起来。这个时候,就很为难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劝不是,不劝呢,也不是。只好任由她们哭。哭吧,人生艰难,哭一哭,抒发出来,总是好的。
回到家里,却绝口不提坟前那一段了。快晌午了,大家忙着包饺子。擀面杖在案板上碌碌碌碌响着,有些喜庆的意思了。蝉在树上低唱。阳光明亮,一院子的树影。
三伏不了秋来到。
秋庄稼成熟的时候,八月十五就到了。
河套园子里的苹果熟了,还有梨,还有葡萄。枣是自家院子里结的。还有石榴。石榴有两种,酸石榴和甜石榴。不小心把嘴笑裂了,露出里面亮晶晶的牙齿。一样儿挑一个模样整齐的,摆在盘子里,上供。当然,月饼是万不可少的。社里新进的月饼,一斤五枚,用油渍渍的草纸裹了,还有一张油纸,有大红的,也有梅红的,拿麻绳扎起来,十分鲜明好看。小孩子家,最喜欢里面的青丝玫瑰。中秋夜,一群孩子,一人举着一枚月饼,一面咬,一面唱:月亮娘娘白又胖,纺线织衣裳。
正是秋忙的时节。人们忙里偷闲,节气总是要过的。把月饼给孩子们分了,自己拗不过,把递到嘴边的月饼小心地咬一口,半晌,皱眉道,不好——太甜了。小孩子心中纳罕,怎么,竟有不爱甜的!却也不放在心上,疑惑一阵子,又跑去玩了。
一村子月光流淌。
月亮娘娘白又胖,纺线织衣裳。
秋庄稼都收起来了。场光地净。粮食进仓的进仓,入窖的入窖。大白菜也种上了,萝卜也种上了。秋天就要过去了。秋天一过,冬天就来了。
冬闲,天短夜长。人们手里总有活计,纳鞋底子、纺线、织布、捻玉米粒。手里忙着,嘴上也不闲。东家长,西家短。一不留神,是非就生出来了。
十月初一,往往就有了第一场雪。女人们就打点一下,缩着脖子,到坟上给亲人送寒衣了。日子浅的,就多哭上一阵子。年月深的,便哭不出来了。一面烧,一面叮嘱,天冷了,记着穿寒衣呀。
天寒地冻,天上飘着雪粒子,打得人脸上生疼。坟头上的枯草,在寒风里簌簌响着。不知是哪里飞来的乌鸦,嘎地叫一声。许久,又是一声。
就闲下来了。
只等着过年。
到了年关,又是一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