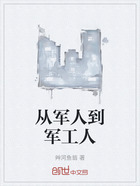
第6章 美丽的传说我的家
在悠悠岁月长河中,历经数千年的时光沉淀,重庆这片土地上龙文化始终蓬勃兴盛,孕育出无数绮丽动人的神话,宛如繁星般点缀在历史的浩瀚夜空。犹记儿时,于静谧的夜晚,父亲那低沉而温和的声音缓缓道来一个古老传说,虽已时过境迁,记忆有些许模糊,可那故事里所蕴含的,人们对于龙凤呈祥这一美好愿景的深深期许,却如同一颗种子,在我的心底生根发芽,从未被时光磨灭。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时期,江州(重庆的古称)的大部分巴人都住在长江北岸,而江对面南岸的两山之间,藏着一个超大超神秘的湖泊,这里住着一群恶龙!这群家伙每天都不安分,上蹿下跳、兴风作浪的,动不动就搞出狂风暴雨,江水跟着就像发疯了一样暴涨,泛滥成灾,可把巴人们折腾惨了,大家都苦得直摇头,却又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在大家苦不堪言的时候,有一个立志治水的英俊少年叫大禹,他心里琢磨着,要治水,非得先把这群恶龙给收拾了,给老百姓除害不可。说干就干,大禹跑到天宫,认认真真学了三年艺。这一学可不得了,艺成下山的时候,师傅太乙真人还送给他一根超厉害的神鞭,据说这神鞭是用哪吒打死的东海龙子身上抽出的龙筋做的,威力那叫一个大!
带着满身本领和神鞭,大禹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江州。一到地方,二话不说,直奔群龙的老巢,噼里啪啦就和恶龙们大打出手。这一仗,那场面简直绝了,从湖里一路打到天上,又从天上哐哐斗到地上,天地都被他们搅得惊天动地、昏天黑地的。大禹的功夫可不是盖的,几百个回合下来,恶龙们被打得死伤一片,节节败退,实在扛不住了,只能灰溜溜地跨过长江,大败而逃。打这以后,长江南岸的那个湖,就有了个霸气的名字——“龙门浩”。
那群残兵败将似的恶龙,爬上长江北岸,瞅见个高大的城门,跟不要命似的一股脑冲了进去,冲进了江州城。城里的老百姓哪见过这场面啊,吓得够呛,生怕被神仙打架波及,纷纷拖家带口逃离家园,出城去躲灾。后来呢,那个和“龙门浩”隔江遥遥相望的城门,就被大家叫做“望龙门”啦。
恶龙们进城之后,慌慌张张地翻上山脊,一回头,妈呀,大禹还在后面紧追不舍呢!它们撒腿又跑,穿过一条热热闹闹的街巷,朝着嘉陵江边奔去。这条街巷后来就成了有名的“来龙巷”。
群龙一路狂奔慌不择路,沿着嘉陵江岸跑到一个深山沟里。这时候它们又累又饿,还吓得要命,瞅着眼前的深沟,实在没辙了,根本跨不过去,眼看就要陷入绝境。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一条年老体弱的老龙站了出来,眼瞅着大禹越逼越近,为了救大家,一咬牙,“扑通”一声跳进沟里,大喊着让同伴们踩着自己庞大的身躯跨过去。最后,群龙脱险了,老龙却牺牲了自己,被活活踩死在山沟里。再后来,老龙的骨头神奇地化成了一座桥,大家为了纪念它,就把这座桥叫做“化龙桥”。
群龙继续夺命狂奔,跑到一个土湾的时候,又被一道高高的土坎挡住了去路。它们急得不行,拼了命地往上爬。这时候,一条怀着宝宝的母龙体力严重透支,在翻土坎的时候,“噗通”一声,生下了一条小龙。这,就是如今咱们熟悉的“小龙坎”。
实在没地儿跑的群龙走投无路,只能又从嘉陵江折返回去,朝着长江方向找活路。结果在长江边上的王家大山,还是被大禹给追上了,双方二话不说,在山脊上展开了终极对决。
这场大战,那叫一个惊心动魄啊,从白天一直打到黄昏,几个时辰过去,龙群被大禹手里神仙给的神鞭打得服服帖帖,彻底没了反抗的力气,只能俯首认输。
王家大山朝着长江的那一面是个斜坡,背面是个悬坡,剩下的九条龙再也无心恋战,连滚带爬地从山顶沿着斜坡逃进了长江,在江心朝着东海方向变成了九个滩涂。打这以后,王家大山就改名叫“九龙山”,长江里的那九个滩涂,自然就成了“九龙滩”。
再看看获胜的大禹,虽说打赢了,可自己也体力透支,累得够呛,浑身伤痕累累。但大禹始终没忘治水的使命,咬着牙背起几十米长、几千斤重的神鞭,又踏上了整治水患的漫漫长路。
凌晨的时候,大禹走到缙云山南麓一个堰塘边的参天大树下,又冷又饿,全身疼得像要散架了一样。他顺手摘了些橙子和酥梨,靠着树干一屁股坐下,心想吃点喝点,歇一会儿再赶路。哪知道劳累过度,伤口突然发作,大禹忍不住“嗷”的一嗓子,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一头栽进堰塘里,奄奄一息的昏死过去,眼瞅着就要不行了。
就在这危急时刻,神奇的事儿发生了!一道金光唰地从天而降,原来是树上的九只金色凤凰被树下的动静惊到了。凤凰们赶紧查看大禹的伤势,接着二话不说,飞到缙云山的悬崖绝壁上,叼来一枝千年灵芝草,把大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后来呢,大禹得救的这个地方,就叫做金凤;凤凰给大禹疗伤的那个堰塘,就是后来的九凤瑶池。
伤好后的大禹,履行治水的神圣使命,他拿着神鞭继续大干一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终于把堵塞的长江给疏通了,汹涌的江水乖乖地流向东海,困扰大家几百年的水患就这么解决了,沿岸的老百姓从此过上了安稳幸福的日子,能安居乐业啦。而那段被劈开的狭窄河道,就是咱们现在壮观的长江三峡。
这个故事于我而言,至今仍能依稀记得个大概,或许是后来我与九龙山有了一些特别的缘分,对九龙半岛的山水逐渐熟悉起来,那些记忆也在不知不觉间被悄然留存。
回想起 2006年,我通过自己的积蓄,还有来自亲朋好友的支持,以及银行按揭的助力,终于购置了人生中的第一套商品房。它坐落于被长江温柔环绕的九龙半岛的九龙山顶,就在闻名遐迩的涂鸦艺术街黄桷坪的上方。这栋楼的位置十分优越,地势是区域的制高点,采光极佳,居高临下,整个半岛都纳入眼底。周边原生态植被郁郁葱葱,繁茂地生长着,清新的空气使人心旷神怡。令人惊喜的是,这里距离热闹繁华的杨家坪商业步行街仅仅 1700余米,在享受宁静的同时,也不失生活的便利。
住宅的右面半山腰处,是铁路中学,继续往下探寻,铁路小学和铁路幼儿园也映入眼帘,这里是铁路职工的子弟学校,社区的周边,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铁路中学的右下方,重庆电力专科学校静静地坐落于此;沿着山势往下,山脚便是充满艺术氛围的四川美术学院,这所艺术院校的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西南美术专科学校,是当时的全国五大美院之一。在美院右前方的江边滩涂上,是重庆的能源供应基地之一的重庆发电厂,发电厂里有两座高达240米的亚洲最高烟囱,是重庆最具特色的工业地标之一。2015年重庆发电厂搬迁。2023年底,发电厂旧址改造建成重庆美术公园,高耸入云的双子烟囱变身灯光秀,90米以上主要以360°环绕LED格栅屏为主,90米以下则采用大流明户外工程投影机实现烟囱的360°环绕投影,以“一环一轴多点”为架构,以烟囱艺术为主体,营造多层次、多场景、多维度的夜景灯光,将光影艺术融入重庆夜境,璀璨夺目的灯光秀美不胜收。
住宅的左边山脚的江边,是1952年7月建成通车的成渝铁路的重庆火车南站,成渝铁路是新中国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起点站在长江北岸的市中区菜园坝,沿着山脚半岛的江岸缓缓延伸,像一条蜿蜒的巨龙,承载着无数的故事和希望,一路驶向西北方向川西平原的成都。在距离火车南站千余米的长江北岸,有一座香火旺盛的佛教寺庙——龙凤寺。龙凤寺庄严肃穆,青烟袅袅,仿佛在与尘世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它正对着传说中的长江九龙滩,九龙滩又遥望着鹤皋岩上的抗战兵工山洞,仿佛在岁月的长河中默默对视,见证着历史的变迁。
居于九龙山上的广厦城社区,十余载岁月悠悠而过。每日晨光熹微之际,我便携着对新一天的期许,踱步至“五龙庙”公交车站,搭乘那几分钟一班的233路公交,踏上上班的旅程。待暮色沉沉、倦意染上肩头,420路公交便如同温暖归巢的指引,载我从“锦龙路”缓缓归向家中。周末的闲暇时分,403路公交则成了我通往繁华杨家坪商圈的纽带,从“龙江路”启程,融入那热闹欢腾的人潮,采撷生活的缤纷。而华灯初上的夜晚,“龙吟路”静谧悠长,我常于其间悠然漫步,任思绪与月光一同流淌。
这一方天地,承载着诸多烟火声色。长江之上,轮船汽笛悠悠长鸣,似在诉说着水运的往昔与今朝;成渝铁路上,火车呼啸而过,滚滚浓烟裹挟着奋进的力量,声声汽笛仿若时代的强音。美术学院和电力学校的校园之内,莘莘学子的朗朗书声,宛如春日里最蓬勃的乐章,奏响知识的颂歌。就连发电厂烟囱里缭绕而出的烟雾灰尘,亦在时光沉淀中,化作记忆里一抹难以磨灭的旧痕。
岁月悄然流转,儿时听父亲讲述的那些故事,因时光久远,细节已渐次模糊,可扎根心底的对乡土文化的眷恋,却从未淡去。这块名为“龙凤呈祥”的重庆九龙坡,每一寸土地都饱含着历史底蕴,每一隅角落都氤氲着人文气息。我于此间栖居,在岁岁年年的朝夕相伴中,心中那份炽热的认识与深沉的热爱,如酒愈醇,愈发浓烈难舍。
翻开地图探寻重庆,不难发现诸多以龙、凤命名的地名,在过往,以龙、凤等蕴含祥瑞寓意之字取名的人亦不在少数。然而,在那段特殊的历史阶段,由于社会环境、文化思潮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种命名习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966年,那是一个特殊时代的开端,社会上涌起了“破四旧”的浪潮。在这一浪潮之下,许多事物都经历了改变,一些地名陆续被替换。就像曾经的两杨路,变成了长江路;朝天门码头,也被改称为红港。在这样的氛围里,改名成为一种流行趋势。不少原本依据周易五行、三才五格以及经典古籍所取的名字,被换上了更具时代感的字眼。
当时,我的父母也难免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而我即将踏入校园,他们觉得我名字里那个有着封建色彩的“龙”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似乎不太合适。经过一番考虑,他们最终决定把“龙”字换掉,希望能顺应当时的时代潮流。
小时候的我,天真懵懂,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还很浅显。当父母提出要给我改名字的时候,我的心里满是抗拒,小小的内心深处藏着对旧名字的眷恋,实在是极不情愿做出改变。父母看出了我的不乐意,便哄我说,名字呀,不过是一个代表个人的符号罢了,等以后长大参加工作了,要是还想改,依旧可以再改回来的。
那时,“破旧立新”的口号正盛行,父母也受到了这股潮流的影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的名字就被改成了“苏立新”。后来,很多地方都陆陆续续恢复了原来的地名,可我的新名字却一直沿用至今。在发表文学作品的时候,我偶尔会用“苏龙”作为笔名,仿佛通过这个名字,能找回一些童年时的影子。还有一些亲戚长辈和老街坊邻居,他们依旧习惯称呼我为“苏龙”,每一次听到这个熟悉的称呼,往昔的温暖与亲切便瞬间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