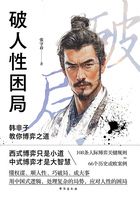
第6章 二柄:管人的两个把手
1 赏罚之权不可分割
原文
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故田常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此简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简公见弑。子罕谓宋君曰:“夫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世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则是世主之危甚于简公、宋君也。
作者智解
虎之所以能使狗屈服,是因为有爪牙。假如虎放弃爪牙给了狗,虎就反服从于狗了,所以,领导不可把赏罚权给下属。人主,是靠刑、赏来制住臣子的,如果放弃刑赏,叫臣子来用它,则君主反而受制于臣了。从前,齐国的田常向国君请求来爵禄,发给群臣,于是齐简公失去了对臣子的德惠(恩惠),而田常开始专权,最终田常弑了齐简公。
子罕对宋国君说:“赏赐,是老百姓喜欢的,这个应该您自己来做;杀戮刑罚,是老百姓厌恶的,我请求来当这坏人。”于是,宋国君失去了刑罚,而子罕有了惩罚人的权柄,最终宋君被劫持。田常使用德,于是简公被杀;子罕握有刑,于是宋君被劫。现在各国,作为人臣但是拥有赏赐、刑罚权力的,其国君面临的危险将比齐简公和宋君还大。
延伸论据:秦始皇——领导授权给下级的利弊
以上内容是说君主不能把赏罚的权力给下属,这作为控制和管理臣子的办法,固然有道理,但也不是没有副作用。
当君主手握所有权力的时候,就不怕臣子们篡权了,但是臣子们的权重也受损了。臣子向任何一个部门提出配合和协作要求,都不会得到重视,后者一定要等大领导亲自在这项事务上发言或发文。大领导就要兼任各种机构的挂名负责人,如果他想让这个机构的行政效率提高。简单说,大领导独握赏罚权柄,会使得整个组织的行政效率低下。
秦始皇可谓是躬操一切大权,把自己累得要死不算,下面的大臣也都是待命充位,唯皇帝之命是听,但也不理睬来自其他各个方向的信息和指令了。秦始皇这么做,就是因为他很喜欢读韩非子的书。把压力都给了大领导,需要他的决策正确,但是,他也难以协调各部门的关系。简单说,臣子太没权了,行政效能也会下滑,所以授权和监察又是必要的。
2 下级不能跨岗交往
原文
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
作者智解
人主要想禁止各种奸事,就要综合审定一个人说的和做的。人臣陈说什么,国君按他说的话,授给他事做,然后责求他的业绩是否达到。达到事情应有的标准,就赏,没有达到这些标准,就罚。这样,群臣中说大话而做事小的人,就罚。至于说得小但是做得事大的,也罚,因为这也是名实不符。(这实际上就是下属提出考核目标,上下级就考核的事项和标准达成共识,然后到期考核和奖惩。)
从前,韩昭侯醉卧,睡着了。负责管帽子的人怕他冷了,就给他盖了件衣服。韩昭侯醒后,发现了,就把这个管帽子的杀了,然后把管衣服的也杀了。杀管衣服的,因为他失职;杀管帽子的,因为他越职。所以,明主管理臣子,臣子不得越官而有功,否则就处罚。大家都守着自己的官职事务,这样群臣之间就不能结为朋党了。
(越职,也就是一个人是A官职,但是做了B官职的事,这里之所以要禁止,是因为他兼有B官职的权力,可能互相沟通,从而徇私舞弊。如果A官职管公章,B官职管账簿,这两个岗位上的人相结合,就可以贪污挪用公款了。管帽子的岗位,和管衣服的岗位,俩人互相帮忙干活,俩人越来越好。如果未来一起害韩昭侯,韩昭侯就没跑了。所以,不能越职。
之所以把岗位划分开,除了因为一个人干不完,也是为了把权力分割、分散。比如,汉朝最大的官是三公,分别是司徒、太尉、司空,这样就把丞相一个人的权力分成了三块,分掌不同的维度。做一件大事,需要不同维度的三公同意,这样就无法一个人为所欲为了。)
3 君主的两个心腹大患
原文
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故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矣。故子之托于贤以夺其君者也,竖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桓公虫流出户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
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则群臣为子之、田常不难矣。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
作者智解
君主有两个患害:一是选用了贤能的人,这个人就会凭自己的能力劫持国君(架空国君);二是选了无能的人,又办不成事。
如果君主喜欢贤能的人,群臣就会假装是贤能的,掩盖自己的本性。群臣的本来面目显示不出来了,君主也就没办法知道谁好谁坏了。
也就是说,君主喜欢什么,群臣就假装成什么样。所以,越王好勇,则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为了减肥和讨好);齐桓公喜欢美味,易牙就蒸了自己的儿子献上。国君暴露了自己厌恶什么,群臣就会隐匿自己身上这些差的部分;国君暴露自己喜好什么,群臣就假装擅长这个。于是,易牙顺着齐桓公的所欲获得赏识,最后侵夺齐桓公的权力,导致后者被饿死,蛆虫从尸体上爬出了门,也没人收葬。为什么呢?是因为国君把自己的底细借给了臣子,臣子借之为害。
臣子的本性,未必是爱国君,只爱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罢了。如果人主不掩盖自己的本情(喜好),不藏匿自己所厌恶的方面,那么人臣就缘之讨得信任,然后侵夺君主。如此,田常那种弑君的事就不远了。所以说,去掉君主所好所恶,不显露,这样群臣就能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了,则国君不被蒙蔽。
(韩非子认为,君主不能把自己喜好什么、厌恶什么,透露给臣子,免得臣子趁机欺世盗名来骗得领导的信任和宠爱。秦始皇很信奉韩非子的这个观点,生怕身边的人把自己的情况泄露出去,乃至自己去了哪里,都不许泄露。
关于这个隐秘、保密的话题,在《主道》篇中已经谈过,在本段中韩非子则说得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