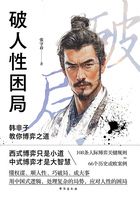
第3章 爱臣:上级靠什么引领下级
1 下级太尊贵的后果
原文
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将相之管主而隆家,此君人者所外也。
作者智解
爱臣,指受宠爱的臣子、近臣。对爱臣太亲,必然危及自己。人臣太贵(尊贵),必然取代主子的地位。正夫人和妾没有等级差别,妾生的孩子一定会危及太子。兄弟互不服气,会内斗而危害社稷。臣听说,千乘之国的国君不戒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偷着吸走他的人民,颠覆他的国家。万乘国君不加以防备,必有千乘之家(指卿家族)在其侧,吸走他的民众,颠覆他的国家。所以,奸臣繁殖产业,君主就要败亡。将相迷惑主子,掌握国家的大权,这是人君一定要提防和排斥的。
延伸论据:王良驾驭马——可以把权力分给他人吗
韩非子认为,爱某一个臣子,太亲,必然危及自己,所以君主应该使用平衡术,叫下面多个臣子互相牵制。如果偏爱某个臣子太多,风险就太大了。
按理说,爱,是儒家强调的美德,韩非子为什么反对呢?因为韩非子在本节认为,权力具备不可拆分性。《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有一个造父的故事,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在这个故事中,韩非子先说道:如果国君和大臣一起行使法令,那么事情就办不好,法令就不能贯彻。他举了造父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造父善于驾驶马车,可以来回周旋,开得随心所欲,这是因为他独自掌握着辔头和马鞭。但是马遇到跑出的野猪被惊到了,马车一下子翻倒在沟里。造父也管不住马,因为这时候辔头和马鞭的威严,已经因野猪的烦扰而被削弱了。
王良也善于驾马,他的特点是不用鞭子,而是拿着草料奖励马,从而叫马听从他的指挥。但是马车到了园囿,里边有大量肥美的草,马就停下来吃草,根本不听王良的了。因为王良的奖励手段,已经被草地的草给分掉了。
(言下之意,马鞭、草是造父和王良的权力来源,权力不可丧失,权柄不能丧失。)
韩非子又说:王良、造父都是天下善于驾驶的,但是如果叫王良拉着左边的缰绳而叱咤,造父拉着右边的缰绳而叱咤,马也走不好。所以,人主和臣子,不能共同分享权力来治理。必须独断,独自握着法令和赏罚。
韩非子的意思是权力不可拆分,主张君主专制,而不是君臣共治。他还曾经引用申不害的话说:“独视叫作明,独听叫作聪。能独断的,才可以做天下的主人。”说的也是权力不可拆分的道理。(申不害是战国中期韩国的相国,思想与韩非子接近,后人统称之为申韩之术。)
如果权力不可拆分这个道理是正确的,那么上级给下级太多权力,下级就可以反噬上级(可以看曹操的例子),所以儒家讲的伦理、爱就不能作为博弈策略。
在权力的博弈中,通过不同的策略,可得到零和博弈,也可以是非零和博弈。零和博弈,即一方所失去的,就是另一方所得到的。二者的收益之和为零。非零和博弈,包括正和博弈和负和博弈。通过博弈,双方收益之和为正数,即正和博弈,也就是双赢。双方收益之和为负数,就是负和博弈,即双输。
要想实现正和博弈,一方面是双方的策略和资源相互整合、升级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其他社会资源、人际关系促进、吸收、融合、转移的结果。比如,劳资双方可以是零和博弈,因为一方多拿点,另一方就要少一点,但如果搞出股票期权的方式,只要把企业的业绩和利润做上去,那么双方利益都会增加,这就是正和博弈。
权力博弈不一定是零和的,也可以是正和的。上下级之间权力合理地组合、配置,就可以获得双方权力都增加的效果,即双赢。现实中,有的公司管理搞得好,有的不好,就是这个区别。韩非子在后面谈了君臣分工,君道是执“腰”,臣道是做事(《杨权》),意味着上下博弈可以是正和的。
虽然韩非子强调权力不可分割,君主要防范臣子,但他也主张君臣要良好配合,这是对韩非子和博弈理念的全面认识。
2 上位者的优势是哪四样
原文
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诸外,不请于人,议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则终于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识也。
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此类也。
作者智解
世间万物最宝贵的是身体,最尊贵的是君位,最持重的是君威,最隆盛的是君权,这四样好的东西,不需要向外面去求,只要把握住了法和术的技巧,就能拥有它们。所以说,人主不能运用自己的尊贵威势,就会沦落到边缘地位,这是人君一定要意识到的。
从前,商纣王亡国,周天子地位下降,都是因为封出的诸侯太多太强大。晋国被分裂为赵、魏、韩三国,齐国被田氏篡夺,都是因为群臣太富。燕国、宋国的国君被弑,也是这类原因。
延伸论据:灭三郤——怎么理解权力的赢者通吃
韩非子认为,臣子势大,就可能杀了君主,篡夺权位,所以不能给他们封邑,不能叫他对人有隶属权,不能有武装。意思是,君臣相杀,是负和博弈,要想避免,就必须合理配置权力。
可是,为什么韩非子在谈权力配置时,往往强调削弱下级的权力呢?这要了解他的时代背景。
在韩非子所处的战国时代之前,是春秋时代。春秋时代是分封制,诸侯国君把一些城邑封给卿,卿家族于是有势力。我们借助一个晋国的例子来说,晋国有八家卿,其中三郤家族,经济实力就非常旺,号称五大夫三卿,“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发展到春秋后期,就形成了六卿专权,政在私门。
在三郤时代,看见卿家族越来越富大,晋厉公又急又眼红,眼中仿佛长了钉子。晋厉公决定,灭掉八家卿族,先从三郤这三家开始。
于是这一天,在厉公指使下,胥童带领八百甲士埋伏在三郤家附近,其他人则假装成打架,闹到三郤的衙门,让三郤给断案。三郤一出来,就被他们杀死了。
混乱还没有终止。胥童继续发难,在朝堂上逮捕了执政官栾书和上军佐中行偃,他们也是晋国的八家卿中的。
胥童的意思是,栾书等八卿,家族产业也很大,也要灭掉。
晋厉公却下不了决心了。他说:“一朝杀死三个卿了,我不忍再多杀了。”于是,放了栾书。
栾书回家以后,先是战战兢兢,杯弓蛇影,后来干脆发动政变,趁晋厉公出游,抓住了晋厉公,随后处死了他。
卿这些贵族,有封邑和民众,是构成和君主对抗的一方。
在晋厉公的博弈案例中,体现了互动性。不论是同时出手还是先后出手,一方会有策略选择,另一方也会有。更常见的是重复博弈。根据对手的策略,选择自己的策略,以及这些策略能形成的多种平衡点。这些平衡点中,对双方都相对最优的一种或多种,被称为纳什均衡(美国人约翰·纳什研究发明的)。纳什均衡指的是所有参与者在考虑到其他参与者采取策略的前提下,选择自己最合适的策略的状态。
这有点绕。通俗地说,博弈思维的特点就是你得考虑着对方(同时或随后)怎么出招,从而决定自己(第一次)的策略选择,所以这一策略不是当下状态中的最佳选择,而是考虑了对方的反应后的最佳选择(从当下看,则未必是最佳选择,但人不能光顾着一切对自己有利的)。
实际上,对方的响应策略不会仅仅一种。分析晋厉公的案例,一旦对三郤出手,对方的卿阵营会有两个策略可供选择:一是认了,表示支持晋厉公,从而向晋厉公争取分到三郤的土地;一是反击,复立三郤的儿子们为贵族或者杀死晋厉公。
晋厉公虽然是先出手者,但以对方的两种可能策略为前提,他需要权衡,他可选的策略有二:一是杀掉三郤,再杀掉其他五家,避免他们反杀我;一是只杀掉三郤,但把三郤的部分土地分给其他五家卿以安抚。
需要权衡的就是,这两种中的每一种与对方的两种反应策略碰撞后,各自会得到什么结果。这些结果,对双方都是相对最优的,就是纳什均衡。能指向纳什均衡的策略,就是各自的最优策略。
现实中很少仅博弈一次,更多是多次重复博弈,所以需要把多次重复博弈的结果价值也计算进去。比如,晋厉公的策略一——杀光八卿,以及卿族的策略二——杀掉晋厉公,显然给本方带来的利益最大,但经过未来的重复博弈,胜利方难免又遭受损失(比如子孙被复仇者杀死),这样逆算到第一次博弈,对第一次博弈结果的得分进行扣减,于是其得分就不高了。
这样一比较,晋厉公的策略二和卿族的策略一,其执行结果是国君和五家卿分享三郤土地,对于博弈双方,都是相对得分最高,形成纳什均衡,相应的策略是各自的最优策略。既然是各自的最优策略,指向纳什均衡,双方势必都会选择这么做。
但是,晋厉公和栾书都没有选择最优策略,结果是晋厉公被杀死,栾书也被下一任国君免职,到孙子一代时栾氏被灭族。也许他们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博弈分析。
没有这种在分析对方采取的诸种策略的前提下,选择自己在诸策略中的最佳策略,就不是博弈思维。不考虑这些,就把博弈理解为单方面的伤害、侵害了,是字面上的误解罢了。
有人说,我不用想,我就等着启动之后,见招拆招。这其实也不是博弈思维。
3 让下位者有钱,但不能有权
原文
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尽之以法,质之以备。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谓威淫。社稷将危,国家偏威。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借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从,不载奇兵;非传非遽,载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者也。
作者智解
所以,明君管控臣子时,使用法的度量,来叫臣子尽力尽才,构建形势上的防备,从而使臣子只能忠诚。所以,不要搞什么赦免死罪,宽赦减刑。赦免死罪,刑罚上饶恕别人,君主的威就散了,社稷就要危险。(这里的意思是反对儒家的仁义,强调信赏必罚,该处死的,不能侥幸放过。)
大臣的工资虽然高,但不能给他城市做封邑,他的党羽虽然多,但不能让他当众人的主子(权力名分,也就是说,给下属高的待遇可以,分给利益也可以,但是不给他各种行政权和影响力)。大臣不能私自开设朝堂,不能跟国外搞私交,他家的府库不能私下借贷给别人(因为讨买人心),外出不能后面跟着武装配车,不能载着兵甲,否则杀无赦。这是明君用来防备不测的办法。
延伸论据:公子夺权与萧何自污
“他家的府库私下借贷给别人”,指臣子对外收买人心。在韩非子看来,财富如果用于消费,那可以鼓励,但财富成为权力的来源,则必须禁止。权力的来源,并不是空虚的神授或者委任状,而是财富、人脉和影响力。拥有这些,就拥有权力,所以韩非子提示要控制这些权力的来源。
所以,下属用个人财富去收买人心,是领导最忌讳的,这可以看公子鲍和萧何的例子。
宋襄公的遗孀襄夫人看上了一个叫公子鲍的贵族。公子鲍是现任国君宋昭公的庶弟,长得一表人才。襄夫人想跟他私通,他不肯,襄夫人就急了,拿自己的钱送给公子鲍。公子鲍用这些钱,施舍小米,周恤饥民,人气值扶摇直上,国家六卿中有五个都支持他。襄夫人干脆向宋昭公下了毒手,遣人把他杀死在去打猎的路上。
宋昭公被杀死,于是公子鲍当了国君,是为宋文公。
这就是私下借贷给民众,从而收取民心,然后夺权的例子。
刘邦当了皇帝后,叫萧何做丞相。一天,萧何过来提合理化建议,说:“臣有一个建议,现在长安土地不多,城外上林苑里的空地和废地倒很多,不如让民众进去开垦,收获的时候粮食归百姓,留下秸秆不收,给野兽吃就好。”
上林苑本是秦朝的皇家苑囿,里边很多珍禽野兽。
刘邦听了,勃然大怒,立刻叫道:“相国这是收了商人的贿赂,跟我要上林苑的地啊!”
刘邦又腾地站起来,喊道:“传廷尉过来,把相国抓起来,给我好好查他受贿的事!”
于是,萧何被下了监狱。萧何本来要干好事,替老百姓谋生计,却把刘邦气个半死,要罗织他罪名,好好治罪。
萧何被抓进御用监狱。过了几天,卫尉(禁卫军首领)王将军看刘邦心情不错,就上前说道:“陛下,不知相国有什么大罪您把他关起来了?”
刘邦说:“当然罪大了。我听说从前李斯给秦皇帝当相国,有好事就归于皇帝,有恶事就归于自己。现在萧何收了商人的贿赂,替民众跟我要地。他自己自媚于民,所以我得系械他,好好治罪。”那意思是,萧何自媚于民,也就是在收买人气。萧何本来在战争时期就管理关中地区,在当地很有人气,现在又收买人心,是打算在这里夺我的权吗?他搞这善行,这不是跟我争民心吗?
卫尉忙劝刘邦,说萧何不会有这动机。于是刘邦当天就把萧何放了。萧何出来,光着脚前来谢罪。刘邦也很感叹,说:“相国不要谢罪了。相国替民众请上林苑,我不许,我不过就是个桀纣这样的主子,而相国还是贤相。你没罪,不用谢罪。我故意把相国关起来系械,是要让百姓听闻知道我的过错。”
说是这么说,但还是含着讽刺和提醒萧何的意思,不要跟我抢民心。
这就是韩非子说的“大臣家的府库不能私下借贷给别人”,避免为自己家邀请政治名誉。所以,下级做好事太多了,乃至盖过上级,也是危险的。有人说,功臣不能做善事,因为本来就名望很大了。有的时候,他还要故意做坏事,也就是自污。自污方能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