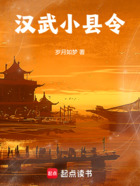
第25章 汾水之畔
汾南乡!
位于平阳县正东侧三十里外的汾水南岸,是由汾水西流南拐后形成的一片水草丰美,土地肥沃之所。
“浮桥?”
行至汾水旁,王发便眉头一皱,疑惑的瞅着霍仲孺。
“方圆百里内,这是唯一的一座大型浮桥!”霍仲孺很是自豪的笑道:“这座渡桥有六十余年的历史,是平阳侯府花费上千两黄金修建,可以说,东来西往的人和货物基本都会从这里过!”
“过了桥就是汾南乡。”
王发眉头一皱,身为一个见惯了横江大桥的他来说,这种桥他第一次见其实还是大为震撼。
一眼望去,舟船紧密排列在江面上,上下游用缆索锚碇,船面上用木板相连,木板之间用绳索相连,岸边还有升降的码头来适应水位的涨落。
并不是双行道,而是单行道,两侧的码头上都聚集着一群等待过河的商队和人,等一边的人过完之后,再过另一边的人。
“这桥的维修费用应该会很高吧!”王发皱眉道。
通行效率就不用说了,舟船为底浮于水面,以绳索相连侵入水中,每天面对水流的浸泡和腐蚀,想不坏都难。
“每年县衙修缮这座浮桥的费用最少有三百两黄金,若是遇到洪涝,费用更高。”霍仲孺回道。
“所以,这座桥是收费的?”王发再问,因为他通过车窗已经看到,每一个过河的人,都在向守桥的吏员缴纳费用。
“不多,过一人两钱,过一车四钱,过一畜五钱,过一满载货车十钱,另有舟船横渡,算上码头每天收益差不多八金左右。”
“这是县衙的财政收入。”霍仲孺十分了解的解释道:“这并不算是赚钱的勾当,一年下来抛开吏员的食禄,维修的花费,历年以来维持收益没有超过五十金,尤其是遇到洪涝灾害的年限,基本上收益都倒贴进去了。”
“八金!”王发微微沉思,认真的盯着浮桥渡口。
每天收益能达到八金的话,一金一万钱,那可是八万钱!
根据前身的记忆来说,这个阶段的货币十分杂乱
这算是一个超大型的码头了,有浮桥供车马通行,又有摆渡运送大宗货物,是个相当有潜力的地方。
“那是什么地方?”王发疑惑的看向码头大门处的一座房间,房间门口有数十人提着钱袋子,似乎是在换钱。
“那属于少府署兑钱的地方。”霍仲孺顺着王发的目光看去,对答如流的回道:“建元元年朝廷行三铢钱,三铢钱与四铢钱等价,与八铢钱三兑一,与半两钱一兑三。”
“建元五年,朝廷罢三铢钱,再行半两钱,元光三年朝廷再行四铢钱至今,现市面上所流通的货币有轻铢郡国币,中铢郡国币,汉半两钱,汉三铢钱,汉四铢钱,汉八铢钱。”
“啊!”说着,霍仲孺也是叹口气的顿了顿,也是十分痛苦的道:“总而言之呢,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司隶七郡如今所强制规定,境内一律使用四铢钱。”
“但是昔日所流通的郡国币,半两钱,三铢钱,八铢钱皆有,且各郡国币铸币时偷工减料,半两钱少一合两合皆为常事,有些甚至少三四合。”
“斤两上做不了假,轻重一称,同等重量兑换,一斤去三合,侯国会把重量轻的货币收回去重铸为四铢钱。”
“所以,少府署专门在交通要道上设立兑换钱币的官署,以方便去假存真,尤其是这种收过路费的桥梁,是极为重要的钱币兑换官署。”
“呼!”王发深吸一口气,早就听闻西汉初期的币制混乱,但他没想到竟然混乱到这个程度。
虽说这个浮桥来往人很多,而且还收费,但也只是一座桥而已,竟然专门设立了货币兑换官署来兑换货币,那难以想象,整个大汉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地方。
这可是货币啊!
而更让他意外的是,平阳侯国竟然拥有铸币权!
这再一次刷新了他的认知,也让他对平阳侯国有了新的认识。
“少府署是在县衙管理之内,那这兑换货币也是归县衙管理?”王发眉头紧皱的问道。
“这!”霍仲孺不明白这位在想些什么,为何压根不关心赌约的事情,反而问这些问题,但还是回道:“不能算是,却也算是,因为平阳县和平阳侯国不可分割,等同于平阳县也拥有铸币之权,诸如熔铸八铢钱,三铢钱,半两钱这些,都是县衙根据全县的货币情况来熔铸。”
“多了就熔,少了就铸,总之,熔铸多少县衙说了算,朝廷不管这些,只需要上报具体熔铸的数量就行。”
“基本上,县衙是不存在缺钱的问题,左右就是黄铜重量和形状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还是粮草的问题,按照朝廷的规定,平均每个里要保持圈养五十匹战马,五十匹驮马,五十匹耕马,五十匹种马。”
“因为实在是消耗不起,这个标准一降再降,已经从五十降到了三十,而且部分乡里从散养变成了圈养,战马的品质也有所下降。”
“而谷物也是如此,朝廷这几年的赋税不断增加,尤其是在豆类作物的种植数量也逐年增加,已经到了和粟米相持平的程度,若是给人吃还好,但这些豆类都是作为战马的精料。”
“一年下来,食邑户能有整整一个月的空仓期,也就这几年没有大灾难,稍微遇到大灾,平阳县早就民不聊生了。”
霍仲孺有意的扯在了粮食的问题上,而粮食问题,那与之切实相关的一定是春耕问题。
“原来如此,那为何夏县丞非要征发田役来给曹家种地?”王发眉头不由一皱,疑惑道:“既然县衙有钱,为何不以工代振,雇佣靑壮来给曹家种地,反而要用征发田役的方式来给曹家种地?”
“这,以工代振?”霍仲孺不由疑惑。
“对啊,以工代振,你县衙出钱,给曹家宗族种地,县衙支付工钱,曹家的地也种完了,食邑百姓也就没有怨言了。”王发随口质问道:“食邑户虽是食邑,但那也是大汉的良善之民才能被称为食邑户。”
“又不是刑徒,官奴,为什么要征发徭役种非官田,公器私用?”
“反正你县衙想铸多少钱就铸多少钱,稍微提高一点工钱,恐怕不用县衙征发徭役,也有大把的靑壮跑去给宗族种地吧。”
“一个靑壮劳力的工钱,一天也就十钱左右吧,按照夏飞的预期,三千人十一天种完,总共花费三十三万钱!”
“春耕是最累的苦力活,一个靑壮劳力早出晚归六七个时辰的劳作,总共挣一百一十钱,这不算是多吗?”
“这……”霍仲孺语塞了下来,不知该如何回答的答非所问道:“一个靑壮劳力在平阳县,日工钱八钱,稳定的月工钱在两百五十到三百钱之间。”
“但是,宗族那边还是出牛马帮忙田役耕种,这是免费的。”
“呵!”王发冷呵一声,沉声道:“所以呢,二月末至三月初,是河东一带最佳种植时间,六七月成熟,但是河东七月之后便是暴晒,迟半个月成熟,粮食就会减产。”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