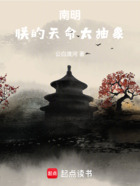
第33章 主本是佛,佛本是道
佛教自巴拉特(天竺)从阿拉干山区传入东南亚便成席卷之势。
穆兰教因为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与中土商贸而传入麻六甲苏门答腊吕宋。
以自上而下趋势奠定风下之地的宗教冠冕。
风上之地偏离航道,佛教在避开与穆兰教的争锋,从上自下,再又自下而上。
战胜天竺教、泛灵崇拜,彻底成为政教相融的特殊存在。
洪沙瓦底自蒲甘王朝初始,就大修寺院佛塔。
大光的大金塔,蒲甘的阿南达寺,阿瓦的马哈穆尼寺都闻名天下。
东吁郡也不例外。
繁盛不及大光勃固蒲甘阿瓦,坐落同古城外的山脊上,亦然有上百座寺院。
其中最大的一间寺院。
晚课结束,七八个僧侣赤脚走过廊道,进入斋房。
风上之地多为上座部佛教,过午不食,他们当然不是来此吃斋的。
互相双手合十拜礼。
寒暄片刻后,为首的老僧侣直接转入正题:
“明军已经攻破平满纳了,明国白文选击溃一万洪沙军后,继续追击莽白大部军队。”
“从锡唐河右岸杀到左岸,又破敌两万。”
其他人念了几声阿弥陀佛。
“如此,算上永贵侯的两万兵马,莽白的二十万大军已经折损四分之一。”
“莽白即使能收拢部分溃兵,也差不太多。”
“东吁郡他已经不敢留了,只能在同古城南面百里的皮尤河、锡唐河交汇处,依仗水师扼守。”
“同古城的一万兵马也调走半数,只剩些老弱病残的奴隶。”
几人互望,都从彼此眼中看到蠢蠢欲动。
老僧侣叹了口气:“明国太子几番想与莽白签盟,谁想莽白冥顽不灵,着魔般想要和明国太子争斗。”
有人附声:“没错,不过称臣纳贡而已,五千万斤大米虽然多了些,下洪沙又不是拿不出。”
“莽白自己弑杀两个兄弟,这会儿又念及国仇家恨起来。”
“洪沙瓦底自古以来,不就是中土的属国吗,勃固一带也曾是大明的大古剌宣慰司。”
另一人厉声抨击道:
“他自己野心勃勃想要做整个洪沙的王,短绠不可汲深井,不是运气好,他如何能做王。”
“拢兵二十万,搞得下洪沙生灵涂炭,和莽应里一样穷兵黩武,即便能胜过明国,我东吁一国也要亡国了。”
“老蒲甘侯虽是伪王,却善待百姓,宽厚佛教,这才是他父亲他隆王的做派。”
莽白屠村掠民,早就搞得下洪沙民怨滔天。
各族土司村落都被收刮抢掠了一番。
就连地位特殊的寺院也没放过。
不是他手握大军,抢的十室九空,各郡早就反。
甚至就在洪沙军北上后,躲进山林里的土司头人已经开始勾结暹罗阿拉干。
“我们身为东吁王室,不能帮虎吃食。”
老僧侣环视几人。
他们都是同古城周边寺院颇有威望的僧侣。
但更特殊的是他们持戒出家前的身份。
是东吁偏远王室子弟。
说偏远,只传了五代的东吁王族也远不到哪去。
都是莽应里的子孙。
莽应里极武穷兵,北讨大明,东伐暹罗,西征阿拉干。
弄得天下皆反,众叛亲离而亡。
他们的父辈彼时割据一郡之地。
直到良渊王崛起上洪沙,阿那毕隆统一天下,他隆王迁都。
他们这些争天下失败的王室后人就只能在东吁郡出家为僧。
“蒲甘老侯爷是良渊王的幼子,阿那毕隆、他隆王的兄弟,他隆王死后,本来王位就该归他。”
几人不是良渊王一脉,王位和他们根本就没关系。
但身为僧侣,蒲甘侯为王给寺院包税权和土地,是十分符合他们的利益。
更关键的是。
人事权。
他们作为争夺天下失败的侯王后人,这一代还能在寺院里做个不事生产的僧侣。
下一代就要沦落成阿赫木旦。
蒲甘侯为王许诺的出家自由和荐举官员,太合他们心意了。
甚至有机会重新回到东吁中枢,做侯王总督。
“如今平达力的孩子都年幼,他隆王唯一的儿子莽白更是弑杀兄长,违背天道佛理,更该让蒲甘老侯爷来做东吁王。”
老僧侣微微颔首:
“说甚伪王,我洪沙国世为中土藩属,蒲甘老侯爷为明国和黔国公亲自册封的东吁王,反倒是莽白不愿受勃固王位,自封东吁王,才是真正的伪王。”
“明国的太祖皇帝和我们一样是僧侣,明国的永历皇帝更是家信佛教。”
“明国太子的叔父曾言自己是伽蓝菩萨转世,自己的弟弟永历皇帝是罗汉转世。”
“明国君臣就是来我洪沙瓦底,兴盛佛教,再复中土。”
李定国白文选焚烧寺院,劫掠百姓,搞得怨声载道。
朱慈煊拉拢佛教寺院僧侣时,自然要释放善意。
这也不是胡说。
朱慈煊叔父朱由楥病故前最后的遗言。
就是以伽蓝罗汉之言让瞿式耜辅佐永历。
有一个僧侣迟疑道:“明国太子不是信奉的西方天主吗?他也是佛陀转世?”
其他人纷纷注目怒视。
这是在说大明统治洪沙瓦底是有名与义。
扯有的没的干嘛。
他们不知道明国太子重用欧洲人和天主教奴隶吗。
老僧侣伸手一按,并不在意:
“无妨。”
“拉乃法师,你可知道中土的道教,和圣人老子李耳。”
拉乃法师微微躬身:“可是诸葛孔明的教派?”
诸葛武侯在西南的影响力是不用多说的。
中土十几次天下大乱,巴蜀汉人南迁,把武侯崇拜带入云滇。
杨慎,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国朝养士百五十年的那个。
被朱慈煊天祖父嘉靖帝大礼议逮捕,充军滇南永昌。
寄情山水,浏览地理。
记录永昌城外有村曰旧汉,言语衣服类蜀人。
而等到大明征服西南,设立三宣六慰,有不少汉人将士留守滇西滇南土司。
又跟武侯攀亲戚。
盖因麓川有不少孟卯勐养孟定之类的土司,孟为大姓。
汉人为了抬身份,鄙夷蛮人。
就说孟姓土司是孟获的后人,自己身为诸葛武侯的后裔要高一筹。
不少掸族人书读的少,也跟着起哄崇拜诸葛武侯。
东吁郡同古城虽在下洪沙,但靠着麓川高原西麓,还是听过些许武侯故事。
前几代东吁王想征服麓川,也曾传入佛教僧侣。
彼处也不少以武侯道教排斥。
老僧侣点了点头:“既知武侯道教,却不知,道教有本经书,言道教圣人曾东出中土,去天竺教化蛮夷,点化佛陀成佛。”
众僧皆是一愣。
有这说法?
中土真是世界文明的起点?
他们也不在意。
他们吃三净肉,连荤腥都不禁。
洪沙瓦底的佛教也有派别之争,但不在于佛经理论,而是寺院戒律。
譬如要不要打伞,出行用不用棕榈叶遮头,袈裟是左袒还是右袒。
所以佛陀是自悟还是被道教圣人点化,不干他们事。
老僧侣双手合十:“尔等又不知,我曾在马都八听闻西方传教士有言。”
“西方圣人曾游历天竺,从学佛陀座下,习得死而复生的秘术。”
“如此而言,主本是佛,佛本是道。”
“三教普度众生,教人向善,皆为一体,明国太子信天主,亦然是我佛座下转世。”
“不然何以佛教洪沙,红月赐其甲,刀枪不入,失魂得神力,觉醒擒象。”
众僧被老僧侣这一套一套的,弄的目瞪口呆,脑子混成一团。
拉乃法师反倒率先清醒:“明国君臣既都是佛陀转世,我们这些供奉神佛的僧侣理应归顺大明。”
其他人也迅速醒悟。
圣人们都是两千年前的人,关他们何事。
老僧侣的话就算全是荒悖虚假的,也无所谓。
反正是找借口,造反莽白,投奔明国。
“同古城守军副将,联系我,愿与我等里应外合,拿下同古城献于明国太子。”
老僧侣解释道。
莽白放弃驻守同古,副将也不愿意坐着等死。
主将手握五百可战之兵,方才联系僧侣召集人手协助。
“我们都是王室子弟,持戒出家,也有奴隶和阿赫木旦,联系山中的掸族人克钦人,也有两千人手。”
莽白不仅在勃固大光勃生三郡大开杀戒,连自己封邑的小土司也没放过。
靠近同古城的头人首领都早已心生反意。
拉乃法师及时出声:“我这就起身连夜进同古城王宫,联系我姨母彬牙公主。”
彬牙公主乃是他隆王妾室,生下卑谬侯莽温。
两月前莽白投莽温入大金沙江,便将其囚禁在同古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