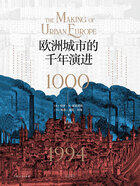
前言(第一版)
城市化的研究必须遵循多学科的视角。在此,我们不敢妄称完全做到了这一点。首先,此项研究涉及经济史和社会史。至于其他相关学科,我们强调两个学科,其他三个则没有过多的强调内容。人口统计学为研究大部分城市居民和其他受到城市化影响的人口尤其是相对远久的年代提供了最可靠、最系统的数据资料。地理学有助于我们适时将空间感和历史感结合起来,在社会科学家偏向理论化时,又提供了很好的具体标准。相比之下,我们较少涉及欧洲城市政治、文化与设计领域,这反映了知识和篇幅的局限性,但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我们也有所认识和理解。
这项综合性研究在各方面的跨度颇大。时间纵横千年、空间囊括从爱尔兰到君士坦丁堡、从直布罗陀到乌拉尔山一片广袤之地。关于时间起止和分期将在后文介绍,我们首先来看地理划分。当我们对整个欧洲大陆进行分析时,其边界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中世纪欧洲实际上不包括阿拉伯人、拜占庭人、土耳其人的领地以及斯拉夫人地区,那时它们还没有与西方贸易往来频繁。只有当远距离贸易加强东南西北四方联系之后,欧洲才逐渐发展成为接壤海洋与高山的一块陆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欧洲的定义具有实用性特点,取决于欧洲城市间的联系。同时,我们将致力于厘清这块大陆是如何随着城市网络的推进而演变。然而,以城市为范畴,我们所指的欧洲小于其边界所包括的范围,这等于我们没有赋予欧洲以它应有的外围边界。书中所举实例和引证属于以斯特拉斯堡为中心、半径为1000公里的范围,径过纽卡斯尔、华沙、那不勒斯和巴塞罗那。在分析中,我们涉及了这个范围以外的地区,但对其没有作专门的系统性研究。而倘若将之排除,则无法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如我们研究了芬兰与马其顿独特的城市历史,但基本忽略了安达卢西亚、乌克兰的城市史。
细致的读者无疑将在我们的解释和评价中发现亮点。我们热爱和赞美城市,尤其是欧洲城市及欧洲人的创造灵感。我们惊叹于城市持久的生命力,尽管它们也很脆弱、常陷险境。一次又一次地,城市抵挡住天启四骑士1的铁蹄,或从失败中崛起。城市不断经受考验,其进程不时被迫中断:从北欧海盗的烧杀戮掠、黑死病、伦敦大火,到当今列宁格勒保卫战、考文垂空袭、格尔尼卡轰炸、德累斯顿屠杀和斯科普里战争。同时,城市还面临更多不易觉察的威胁。城市为保持特有品质的生活,就必须对抗财政剥削,以及来自文化统一和大众富裕阶层的腐蚀力量;城市不得不接纳突如其来的难民潮,控制或反对建筑者和土木工程师耗费巨大而又无益的建设。城市环境可能经常遭受污染,到处充斥着暴力、浮华与冷漠。然而,同样在城市,各种巨大的能量和强烈的意识在歌颂过去的同时,也在形塑未来。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城市民众决不仅仅是缔造城市的劳动者和其灾难的受害者。城市化给许多人带来了机遇,激励人们向上,使大多数人过上了体面、安稳的生活。最后,我们还指出,每一个时代包括工业化和当今时代的城市化均带来了进步。
然而,在我们的研究中存在一个较微妙的学术或方法论的问题。尽管我们接受的是美国学术训练,并置身于英美社会科学界的主流,但同时也深深受到法国历史学派、尤其是年鉴学派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及同仁的思想的影响,强调研究的结构和情势,以及研究视角的多学科性。我们关注普通人群、日常生活,拉长时间跨度考察城市变化及持久的模式,这些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布罗代尔的成果。当然,我们据此做出的诠释仅为一家之言,若有纰漏,绝不能归咎于法国高卢的学术大师或其他任何学者。
因环境、兴趣和特长之故,本书两位作者的分工时有变动。但在整体上及某些章节完全是两人合力为之。每一章凝聚了我们的共同劳动。我们共同履行责任及编辑工作。
有关早期版本的一些部分被我们作为报告,参加社会科学历史协会(the Social Sciemce History Association)、欧洲研究讨论会(Council on the European Studies)、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国际经济史协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欧洲城市史研究会(European Study Group in Urban History)以及在德国巴德洪堡、宾夕法尼亚大学、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北卡罗来纳州大学举办的演讲和研讨会。从会议讨论和与会者所提出的批评中,我们受益匪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我们与学生共同探讨。于此,感谢他们对本书的修改所提供的帮助。根据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提议,这项研究开始于1977年。在研究、撰写、修订的全过程,蒂莉始终给予了积极的援助。他的意见不仅引人深思,而且极具建设性。
大西洋两岸的众多学者亦一直提供支持,常激励我们反复斟酌、突出论点或充实文献。在此虽列出一系列不完整的名单,但远远不足以表达我们由衷的感激之情。我们衷心感谢莫里斯·艾马尔(Maurice Aymard)、阿尔·巴尔(Al Barr)、多拉·克劳奇(Dora Crouch)、皮埃尔·德永(Pierre Deyon)、罗伯特·迪普莱西(Robert Duplessis)、玛莎·豪厄尔(Martha Howell)、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安德鲁·利斯(Andrew Lees)、富兰克林·门德尔斯(Franklin Mendels)、爱德华·彼得斯(Edward Peters)、查尔斯·罗森堡(Charles Rosenberg)、唐纳德·维塔利亚诺(Donald Vitaliano)、苏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e)。同时感谢伦斯勒理工学院B. J. 考夫曼(B. J. Kaufmann)和凯西·基南(Kathy Keenan),宾夕法尼亚大学埃塞尔·库利(Ethel Cooley)、帕特·戈尔曼(Pat Gorman)、琼·普隆斯基(Joan Plonski)和瓦莱丽·赖利(Valerie Riley)出色、耐心的秘书工作。书中线图由伦塞勒理工学院教学媒体分院绘制,贝亚·丹内格尔(Bea Danneger)、汉斯彼得·孔茨(Hanspeter Kunz)参与其中。最后,感谢伊丽莎白·萨特尔(Elizabeth Suttell)、珍妮特·马兰茨(Janet Marantz)帮助我们进行全书的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