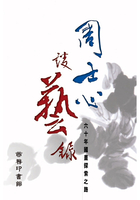
國畫欣賞
(一)人物畫
國畫中以人物畫發端最早。古時統治者以天道鬼神的觀念,來維繫人心;春秋戰國儒家學者推行禮教;秦漢帝皇篤信方士,訪道求仙之舉盛行;到魏晉南北朝時,佛教傳入中國。而人物畫最能推行教化活動,直接受當時思想潮流的影響,所以大都屬於鬼神道釋經史故實等畫。戰亂時期有記載戰績、表揚功臣等繪畫;太平盛世時則有帝皇行樂,以及貴族遊宴和風俗等畫,範圍甚為廣泛。
現尚存於山東武梁祠石室之人物畫雕刻,寫推行禮教和春秋戰國時代的故事,都能以簡單的筆觸,充分表現出人畜事物的情狀。其餘尚有殘存的漢代壁畫,繪有人像及鬼神,可說是現在能目見的最古人物畫了。
從前的寺院,同時供奉神仙與佛像,是道釋不分的,直到唐朝中宗的時候,為了尊重道教,方始不再在供奉佛像的寺院內,繪塑宣揚道教的壁畫或神像,另於道觀畫天師真人、雲龍符籙等畫。但是當時仍有很多畫家是兼擅佛教和道教人物畫的。
敦煌石窟為歷代修建增繪而成藝術寶庫,此中壁畫歷魏、晉、六朝、隋、唐、五代,以迄宋元,蘊藏之富,天下無雙;大都屬於佛教故事畫,部分也描寫當時的風俗,作者都不具名。這些畫有出於當時名手,也有出於庸俗的工匠之手,因此敦煌壁畫有重要的歷史價值;若論壁畫藝術的品質,卻大有高下。
人物畫家以三國東吳的曹不興最為著名,他的藝術造詣到達最高的境界,當時人稱他的人物畫:「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就是讚美他畫藝的精妙。相傳曹為東吳大帝孫權畫屏風,不慎在畫絹上誤畫墨點,即隨勢改為一蠅,孫權看見欲用手去彈蠅。曹畫寫生之妙,可見一斑。
自此以後,人物畫家有大名留世者,大都學他的畫風,如晉朝的衞協及他的弟子顧愷之;隋代的展子虔、董伯仁;唐代的閻立德、閻立本、吳道子、周昉、孫位;五代的顧閎中、周文矩等,都受曹畫的影響。
流傳到現在的卷軸人物畫,吾人尚可以看到的有:顧愷之的「女史箴橫卷」、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張萱「搗練圖」、「虢國夫人遊春圖」、孫位「高逸圖」、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李唐「吳中三賢圖」等,不獨體態生動,比例正確,臉部表情尤為傳神,決不似現代中國人物畫中所常見的那種木然無情的臉譜,因此有人說:「人物畫今不如古,山水畫古不如今。」這真是確論。
(二)山水畫
山水畫的派別大致可分北宗與南宗,一般認為北宗畫祖是李思訓,南宗畫祖為王維(字摩詰)。但是推源求本,在李王之前,畫人物而享有盛名的顧愷之,已有完全的山水畫了。也許更有在顧愷之以前的山水畫,但大都是人物畫中的背景,如敦煌北魏壁畫中的山川樹木那樣,可以說僅具山水畫的雛形而已。相傳顧愷之有「雪霽望五老峯圖」,從背景畫中脫胎而出,成為獨立而完全之山水畫,顧氏且有山水畫作法的著述。又隋代之展子虔亦在李王之前。現在傳世之作有「遊春圖」,此圖以風景為主,亦無「水不容泛,人大於山」的畫病。到唐朝的李思訓,專工青綠金碧山水,因為技法上更趨成熟,故後世推為北派的宗師。唐代以後,畫北宗山水的,如宋代之趙幹、夏珪、馬遠、馬麟;元代之趙松雪;明代之唐寅、戴進、吳偉等,均能一脈相傳。而唐開元王摩詰不僅是偉大的詩人,而且也是一位山水大畫家,他創破墨法山水,以他天賦獨厚的秉質來作畫吟詩,因此當時人稱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他的著作除千古流傳的名詩外,尚有「山水畫訣」一卷,其觀察山川樹木自然的現象極為精到,後世學畫的人奉之為典則,並視王維為山水畫南宗之祖。
明董其昌有謂:「文人之畫自王右丞(王維)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寬為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米芾)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山水畫的淵源大致如此。
(三)花卉畫
國畫中的花卉畫,於畫學中佔有重要位置,且素來為人愛好。大致描寫自然花木,沒有時間上限制,千百年來雖古猶新,又這種迎風帶露、充滿生意的姿態,最得人喜愛。
書畫本屬同源。最古象形字中,如園、果、花、木等字,即是簡單的圖案畫。秦漢時代的宮殿建築物上均有用花草的圖案作為裝飾;其中在漢代的銅器上,像鏡鑑一類的花邊是非常精緻的。到魏晉南北朝的時候,還沒有一位專畫花卉而著名的畫家,所畫花卉大都限於在佛像、建築、器皿上,作花邊裝飾點綴之用。直到中唐邊鸞、刁光胤、膝昌祐等輩出,花卉畫始露頭角,但仍是屬於發展時期。及至五代,江南徐派創沒骨法,方始建立了花卉畫南宗的基礎。後蜀黃筌創鈎勒填彩法,亦能獨步一時,後來的人將之推為北宗的祖師。學花卉畫的人,非徐即黃,幾乎不脫這兩家門戶。此外尚有融合南北兩派而成的鈎花點葉派,以及從沒骨法中化出的大寫意派,如文人畫中之八大、石濤等,都能不拘成法,而加以變化創新,自成一家,並有一定的成就。
一位外國美術評論家說:中國畫家以柔軟的筆觸,控制了恰到好處的水分,在非常容易透背的棉料紙上,用半透明顏料,熟練而具有絕對把握的手法,一着筆,即活生生地將花朵表現出來。此一恰當的描述,也恰好說明了花卉畫沒骨法的畫法。
(四)四君子畫
梅、蘭、菊、竹畫,原來屬於花卉畫科的。後來因為這四種植物的性格,不同其他平凡的花木,文人專好畫之,逐漸成為另外一科稱「四君子畫」。
中國人視梅花為國花,因梅花品格高尚,不畏風雪,有堅毅純潔的特點。蘭花具有幽雅的香氣,並且生長在山谷中,像隱士那樣,不與俗人為伍,有一種清逸淡泊的氣質。菊花能忍霜耐寒,古人將之比擬人品,所謂黃花晚節香,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雅興,一向為人樂道。竹有瀟灑的姿態,直節空心,就如虛懷若谷的君子風度。
古人將梅、蘭、菊、竹人格化,並用精煉的技巧去描摹它,成為鈎勒填彩法。宋初徐崇嗣畫梅,完全用色點染,此乃繼承他祖父徐熙所創的沒骨畫法;陳常以飛白法寫梗(即用禿筆蘸濃墨以輕快之筆調鈎出枝梗),而用色點花;同時期雀白創水墨法,全用深淺不同之水墨漬染而成,用這種方法畫梅,畫得最好的是華光長老。到南宋,揚補之更創圈成白花頭不着色法,趙孟堅、釋仁濟等爭相效法,成為一派。元朝人專尚寫竹,畫梅大家惟王元章繼承揚法而負盛名。
畫蘭亦有鈎勒填彩和寫意兩法。宋末趙孟堅、鄭思肖等文士遣懷寄興,多好畫之。鄭思肖,號所南,畫蘭花極精妙。有人問他:「為甚麼你畫的蘭花,都是露根的?」那時宋朝已亡,他說:「土地都沒有了,要它生在哪裏呢?」鄭思肖是一位布衣,愛國的心卻是熱忱無比的,他的名字據說就是不忘趙宋的意思,後世人尊敬他的人格,他的畫價值很大。元朝李息齋、明朝文徵明都是寫蘭名手。其餘畫蘭的人不少,但都不能與以上各家相擷抗,不足述矣。
不知畫菊在甚麼時候開始。但聞宋代畫菊花的人很多,如趙昌、邱慶餘、黃居實諸家均有「寒菊圖」。元朝人畫菊者少。明代沈石田、陳白陽、周少谷、文徵明、陸包山等都擅寫菊,尤以陳白陽寫菊之法最為清逸有致。
民間傳說漢末關壯繆為畫竹始祖,惟此說殊不可靠。曲阜顏氏樂圃藏有漢代竹葉碑,石碑的陰面刻有竹枝,竹幹由左向上,傾側向右,作背風勢,幹用實筆,葉片隨勢佈滿全石,作雙鈎法,此為可見之最古之竹畫,雖不能知為何人所作,亦可證明漢時已有甚為完善之畫竹方法。據《宣和畫譜》載,墨竹創自中唐玄宗,五代有李頗墨竹一卷。歷來畫竹分寫意和鈎勒兩派。宋代寫意以文與可、蘇東坡最為著名;鈎勒着色則以崔白、吳元瑜為最。蘇東坡有一次做監試官,一時興來,隨手以朱筆在試卷上寫竹一枝,看來頗有風致,後人稱之為朱竹,乃成畫竹別格,至今仍有人仿效。元朝人畫竹的風氣更盛,享有大名者,幾佔當世著名畫家三分之二,如高房山、李息齋、柯九思、倪雲林、顧定之、楊維翰,吳仲圭、趙松雪夫婦及其子仲穆等,皆有名之士。明代則有王孟端、姚公綬、沈石田、文徵明,夏仲昭等,亦能繼往開來,卓然成家。
有人笑倪雲林寫竹而不似竹,他說:「余之竹,聊寫胸中逸氣耳……他人視以為麻為蘆,僕亦不能強辯其為竹。」此足證士大夫之寫竹,適一時之興趣,聊以寄託也。古人稱着色之竹為畫竹,稱水墨之竹為寫竹,言「寫」而不稱之為「畫」者,就是此意。
宋代備重理學,畫家們也受了這種思想的影響,在繪畫方面不着重於實用價值,而注意在筆情墨趣之間。宋代所以流行此種文人畫,完全是時代的產物。到了元代,又因被異族統治,有節操的文人,不願與當政者合作,就寄情書畫以逃世,於是畫四君子畫的人更多,並成為一種清逸簡淡的畫派。
(五)筆法
能對國畫之作法稍有了解,更能增加欣賞的情趣。國畫除畫面本身的美外,還應包括優良的書法、曼妙的詩詞、上佳的紙質和印章、精緻的裝璜、歷久不變的顏料和印泥,甚至書題款字的位置,都有一定的規矩,缺一不足,在在均須千錘百煉,是屬於一種整體綜合的美。
注意國畫的人,皆知南朝謝赫所定的繪事六法:一、氣韻生動;二、骨法用筆;三、應物象形;四、隨類賦形;五、經營位置;六、傳移模寫。其中以氣韻生動最為難能云云。大致藝術進境到相當成熟階段,先代畫家即會將積累之經驗,提煉成精簡的原則,以供後人效法並充實,藝事方能進步。
國畫除顏料紙硯而外,最重要的工具,即是毛筆。國畫用筆之法有:皴、刷、點、拖、斡、渲、捽、擢,稱為八法。學畫的人要精通八法,方能得心應手。中國毛筆採圓錐形狀,吸收水分多少,隨心所欲;選料有狼毫、兔毫、羊毫、雞毫、鹿毫——有淨純製品,亦有配合製品,須看畫面需要不同的筆觸,而選用各種不同的毛筆,始能收揮灑之效。
(六)墨法
論國畫,常常聽說「用筆用墨」這句話,那就是用筆和用墨的方法。故除了上述筆法之外,還有墨法。畫一切水墨畫,應知用墨之奧秘,掩映向背,蒼老潤秀,全在墨色也。水墨畫既不用色彩渲染,單單一種墨色要分出層次,方能稱為佳作。古人稱:「墨分五色」,即焦、濃、重、淡、清也。品質低劣的墨,濃重尚可,稀化到清淡階段時,就顯得色澤灰暗,毫無神氣,不可用也。至焦墨之成,即將濃墨留在硯池中二三小時,就能濃縮成較為高級之墨色,將它用於畫面最重要處,有畫龍點睛之妙。
古人說:「人品不高,用墨無法。」說明畫家在繪畫技術之外,尚須注重修養。往往因為人品的高潔,墨色自會沖和淡逸,雅韻欲流。有時甚至因為畫家的人格而看重他的作品,即使繪畫的一般技術差些也沒有關係。這又是在六法、八法以外的一法。相信甚多人會奇怪,有些名畫寥寥數筆,價值卻甚為可觀,道理在此。
(七)賞鑑
古代名畫皆有著錄可稽,並記流傳歷史。惟唐以前畫迹,僅能在著錄中見其名稱,千餘年來,經過天災人禍的刧難,大都已不在人世流傳,因此偶有發現,得到的人有愛逾生命者,輕易不敢出示,以防為有勢力者奪取,但仍有被人用計策騙取,以假易真,或偷盜的事件發生。
從前有專做假畫的人,用香灰水染紙,借真本臨摹,一點一畫,面貌酷肖,自稱風雅。而對古畫並無鑑別能力的人,往往以高價購來贋本。以上之偽作方法尚是下乘者。甚至有許多大畫家,在沒有成名前作「假畫」,以謀取生活,他們的功力不弱,意境筆墨有超過真本者,甚至完全出於杜撰,如欲斷定它們的真偽就很難了。
加上現今的收藏家,除了收藏古畫外,有些還兼收古代畫家用的圖章、印泥,和宋元時代的舊紙或舊絹,連極有名的宋代澄心堂紙到現在還有人收藏着。如果有人利用這些原舊的紙絹印章作假畫,加上名畫家本身精湛的功力,這種假畫是很難被人識破的。
現代人偽作古人畫,總還是比較容易被人看出,但要是古人的偽作,譬如南宋人偽作北宋時期的名畫,流傳已久就更難於鑑別了。不過南宋時代的畫本身也很有價值,真偽反而成為次要的事了。
古畫之所以真偽鑑別最難,全因它沒有一定的標準。像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假畫最多,現在所知,美國有三種,日本有兩種,台灣有一種,大陸有一種,可能全是偽作,只是臨摹的技法,有高下之別而已。但從這許多臨本中,可以看出原畫的一些規模,那末贋本也有其價值,是無可非議的。
另外,有許多古畫是沒有款字的,鑑賞家忖度其筆法及紙絹年代,假定為某家之作,流傳年代一久,此畫就被確定為某家之作了。如香港某名收藏家所藏之北宋劉道士「湖山清曉圖」即屬一例。最近張大千先生所得五代關潼「岸曲醉吟圖」,亦無作者款字,僅有元初趙孟頫題跋,稱為關潼之作。視其佈局筆法,絕非所謂劉道士之「湖山清曉圖」,安知趙孟頫之稱此畫者為關潼,豈亦如大千居士之命名無款宋畫的作者為劉道士耶?
原載於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三日《星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