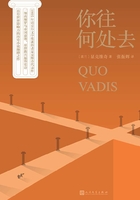
第二章
舅甥二人吃的这顿饭名为早餐,可是他们在饭桌边坐下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裴特罗纽斯建议饭后去休息一下,因为现在出门访友为时尚早。他见到过有的人太阳刚刚升起就出去访友,还说这是罗马的老规矩,但他认为这是一种不文明的习惯,下午出去会亲访友才是最合适的,而且要等到太阳照过卡比托尔朱庇特[1]神庙,开始向集市广场倾斜的时候。秋天虽然到了,天气依然很热,人都爱在饭后休憩一下。这时候,倾听庭院里喷泉的沙沙细语,或者在饭后规定的一千步的散步之后,在透过半开半合的紫色天棚射进来的红色阳光下闭目养神,倒也十分惬意。
维尼茨尤斯觉得他的建议不错,便和他一起出去散了一会儿步,随便谈了一些帕拉丁宫和城里的情况,还就人生问题发表了许多议论。裴特罗纽斯随后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里,但他只睡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他吩咐把马鞭草香料拿来,闻了闻它的香气,把它擦在自己的手上和太阳穴上,说:
“你不知道这东西是多么提神醒脑。我已经准备好啦!”
一乘轿子早就在等候着他们,二人上轿后,便命奴仆把他们抬到位于帕特里丘斯街的阿卢斯·普劳茨尤斯的府邸去。裴特罗纽斯的住宅坐落在帕拉丁宫南边的山坡上,距卡雷纳不远,走集市广场下面去本来最近,可是他想顺便去看望一下珠宝商伊多门,就让轿子走阿波林尼斯街和集市广场,先到斯策列拉杜斯街去。他们来到斯策列拉杜斯街口后,看见这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货摊。
抬轿子的是几个身材魁梧的黑人,还有一些“家丁”在前面开路。裴特罗纽斯一直没有说话,他这时把他那散发着马鞭草香气的手掌抬了起来,摸着他的鼻子,好像在想什么事情,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道:
“我有时以为,你的那位森林女神既然不是奴隶,她就可以离开普劳茨尤斯夫妇,住到你家里去。到那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全部爱心倾注在她身上,让她和你共享荣华富贵,就像我对我的那位圣洁的赫雷佐泰米斯一样。可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之间都感到有些厌腻了,你们也会这样。”
维尼茨尤斯摇了摇头。
“不会这样?”裴特罗纽斯问道,“当然,就是遇到最坏的情况,你还可以得到皇帝的恩赐,红胡子看在我的面上也会成全你的,这你可以放心。”
“你不了解莉吉亚。”维尼茨尤斯回答说。
“我倒要问你,你了解她吗?你除了和她见过一面之外,还有什么呢?你和她说过话吗?向她求过爱吗?”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喷水池旁,后来我又见过她两次。你要知道,我在普劳茨尤斯家里做客时,是住在一所专为接待客人用的别墅里,我的手臂当时又受了伤,不能和他们一同进餐,所以一直到我离开他们家的头天吃晚饭时才见到了她。但我又没法和她单独在一起谈话,因为我不得不听普劳茨尤斯没完没了地讲他那些在大不列颠打了胜仗的故事。他还说什么虽然利策纽斯·斯托罗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未能挽回意大利的那些地主遭到破产的命运。我不知道他还要说些什么,反正你别想从他的那些故事中绕出来,除非你要他讲今天人们失掉了男子汉气的事情还差不多。他们家的鸡笼里养了许多野鸡,但他们却不肯杀了吃,因为他们有一种看法:每吃掉一只野鸡,就会使罗马帝国早灭亡一天。我第二次遇见她,是在花园里的池塘边,当时她手里拿着一根苇秆,用秆的一头去塘里沾水,浇洒着周围盛开的鸢尾花。你就看看我这两个膝盖吧!凭赫拉克勒斯的盾牌起誓,当一群黑压压的安息人大喊大叫地向我们的小队冲过来时,我这两个膝盖都没有发抖,可它们在这两个水塘边却颤抖起来。我真的像一个脖子上挂着垂花的少年那么腼腆,只会用眼光去乞求怜悯,很久说不出话来。”
裴特罗纽斯以羡慕的眼光望着他说:
“一个多么幸福的人啊!即使人世间和我们的生活都变得最坏,也还有一样东西永远是美好的,那就是青春。”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道:
“你和她说过话没有?”
“说过,我的脑子稍微清醒了点后,就对她说,我是从亚细亚回国的,我在城外摔伤了胳膊,痛得很厉害。可是当我要离开这所好客的房子时,我就感到在这里熬过的痛苦比在别处享受的欢乐要宝贵得多,我在这里生病也比在别的地方健康的时候要好得多。她听了我的话后,难为情地低下了头,用苇秆在脚边的沙地上画了些什么。随后她看了一下她画的那些符号,又看了我一下,好像有什么要问我似的,可是她又突然跑掉了,仿佛树仙遇到笨头笨脑的畜牧神,她不喜欢我似的。”
“她一定有双迷人的眼睛。”
“像大海一样迷人,我像淹没在大海里一样淹没在她的眼睛里了。请相信我,她的眼睛比岛屿密布的大海都显得更蓝,过了一阵,普劳茨尤斯的小儿子跑来问我一件事,我竟然什么也没有听懂。”
“啊!雅典娜[2]!”裴特罗纽斯叫道,“请你把埃罗斯绑在这个青年眼睛上的遮巾摘下来吧!否则他在维纳斯的神庙里,会在圆柱上碰破脑袋的。”
接着他对维尼茨尤斯说:
“你是生命之树上春天的蓓蕾,葡萄藤上新绿的嫩芽,我要把你送到盖罗茨尤斯的家里去,而不是送到普劳茨尤斯的家里去。盖罗茨尤斯家里有一所专为涉世不深的青年开办的学校。”
“你到底要干什么?”
“她在沙土上画的是什么?是爱神的名字,还是她那颗被射中的心?或者有关萨迪尔[3]在这位女神耳边悄悄说过的那些人生的秘密?你怎么不仔细地看一看那些符号呢?”
“你别小看人,我穿上长袍的时间比你料想的要早得多。”维尼茨尤斯说,“在小普劳茨尤斯来到之前,我就已经把那些符号看清楚了。我知道,在希腊和罗马,姑娘们羞于用嘴表达的爱情,往往写在沙子上……你猜猜,她画的是什么?”
“如果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我就猜不出了。”
“一条鱼。”
“你说什么?”
“我是说,一条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血管里流的是冰冷的血?你既然说我是生命之树上春天的蓓蕾,那你肯定知道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咯?”
“亲爱的,这种事你还是去问问普利纽斯吧!他最懂得鱼。如果老阿彼茨尤斯在世,他也会告诉你,他一生吃过的鱼比那不勒斯海湾的鱼还要多。”
他们乘坐的轿子已经来到了热闹的大街上,这里喧腾的人声使他们再也谈不下去了。过了阿波林尼斯街后,他们便拐进了罗马的集市广场。每当天气晴和,在日落前总有一些闲散的居民到这里来游玩:有的在圆柱间散散步,有的打听和谈论着各种新闻,有的爱看那些坐在大轿里的名声显赫的达官贵人。可是舅甥俩还要去参观卡比托尔[4]对面市场上的那些珠宝商店、书店、钱庄、绸缎铺、铜器店和别的商店。集市广场有一半处在城堡岩石的下方,被岩石的影子遮住了。神庙的圆柱所处的位置要高一些,阳光和蓝天交相辉映,使周围呈现一片金碧辉煌。位置较低的圆柱把一道道长长的影子投在大理石地板上。一眼望去,这些圆柱简直数不胜数,就像一片森林,望不到尽头。可是看起来,它们又好像和房屋连在一起,形成参差不齐的层次,向左右两边延伸,然后爬上山丘,贴着城堡的墙壁,或者相互之间紧紧地挨着,仿佛一排排树干,大小粗细交叉,红白两色相间。有的在楣下种植着老鸦花,有的卷着爱奥尼亚式的棱角,有的还在顶端造成一个简单的多利亚式的正方形。城里的神庙很多,在一大片宛如森林的建筑物上,闪耀着五颜六色的三垅板。山墙上耸立着诸神的雕像,屋顶上有许多飞马驾着的马车,那些飞马都展开了金色的翅膀,似要腾空而起,飞向静静高悬在罗马城上的蔚蓝色的苍穹。市场的中心和周围,人群川流不息,有的从尤利乌斯·恺撒[5]大殿的拱门下走过,有的坐在卡斯托尔和波卢克斯[6]神庙前的阶梯上,有的在维斯塔[7]的神庙前晃悠,就像一大群五颜六色的蝴蝶和甲虫,闪动在一块巨大的大理石上。新的人群又从“至高无上的朱庇特”神庙的上方,沿着一些巨大的阶梯拥过来了。讲台四周的人群都在倾听着演说家们偶尔到此发表的演说。到处都可听到人群的喧叫声,有卖水果、葡萄酒或无花果汁的小贩,有卖神药的江湖骗子,有算命先生,有能测出宝物藏地的卜人,还有详梦的人,他们自卖自夸的叫喊常常和远处或近处演奏的竖琴、埃及桑布基或者希腊风笛的乐声混在一起。还有一些病人、虔诚的信徒或者在人世间饱经忧虑的人在给神庙供祭品,祈求诸神的保佑。不时飞来一大群鸽子,在石板地上贪婪地啄食着人们给它们撒下的谷粒。不一会儿它们又扑着翅膀啪达啪达地向空中飞去,然后落在人群离散了的空地上,好似一群流动着的五颜六色的斑点。如果偶尔来了一乘轿子,人们还会给它让出一条道来,这样他们便可看到轿子里露出来的一位贵妇人的俏丽的面孔或者元老或骑士的头,可是这些贵人神色呆板,仿佛饱受过痛苦的折磨。观看者于是以不同的语言不断地叫唤着他们的名字和绰号,对他们说几句讽刺或者恭维的话。士兵和维持治安的巡警队都迈着整齐的步伐,在这些散乱的人群中来回地走着。人们在这里除了讲拉丁语外,也常常说一些希腊话。
维尼茨尤斯很久不在罗马了,因此乍一看到那些喧闹的人群和罗马的集市广场,他感到十分新奇,感到它既掌握着那许多人群的命运,又好像被人群淹没了似的。裴特罗纽斯猜出了他的心思,便把这座广场称为“没有克维雷特人[8]的克维雷特人的巢穴”。的确,罗马的风俗习惯在这些汇集着所有民族的人群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这里除了罗马人外,还有埃塞俄比亚人,有身材高大、长着浅色头发从远处来的北方人,有不列颠人、高卢人和日耳曼人,有斜眼睛的塞利库姆人,有来自幼发拉底河畔的人和胡须染成了砖色的印度人,有来自奥隆捷斯河畔、长着一双柔顺的黑眼睛的叙利亚人,有骨瘦如柴的阿拉伯沙漠的居民和胸脯陷了下去的犹太人,有老是露着一副无所谓的笑脸的埃及人,有基米提人和阿非利加人,还有来自赫拉斯[9],来自爱琴海上的岛屿,来自小亚细亚、埃及、意大利和纳尔波高卢的希腊人。他们能够和罗马人并驾齐驱地统治这座城市,凭的是他们的知识、艺术和智慧,还有他们善于行骗的本领。还有一些游手好闲的自由民混杂在那些耳上穿了洞的奴隶中间,皇帝供给他们衣食,以他们取乐。还有一些人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觉得这里容易找到职业,实现他们发财的梦想。此外还有许多小商小贩、手里拿着棕榈树枝的塞拉庇斯[10]僧侣和伊西斯[11]僧侣——伊西斯的神坛上的供品比卡比托尔朱庇特神庙里的供品还要多——手捧金黄色稻穗的库柏勒[12]僧侣和信奉巡游诸神的僧侣。还有头带鲜艳头饰的东方舞女和卖护身符的人,玩蛇的人和迦勒底的魔术师,还有许多无业流民。这些流民每周都到第伯河畔的粮库里去领取救济粮,为了抢到几张竞技场上的彩票便大打出手,晚上就在第伯河区一些破旧的房子里栖身。天热的时候,他们便到地下圣堂的柱廊里来乘凉,或者在苏布拉区的一些肮脏的酒馆里喝酒,或者在密尔维尤斯桥上闲逛,在大户人家的门前等着里面不时扔出奴隶吃剩的菜饭。
广场上的人都认识裴特罗纽斯,他们不断地呼叫着“这就是他”,因为他们都很爱他为人慷慨,特别是他在皇帝面前反对过对佩达纽斯·塞昆德总督一家奴仆的死刑判决,消息传开之后,他的声望就更高了。事情是这样的,塞昆德总督家里有个奴隶,因为不堪主人的虐待而把他杀了。罗马的法庭后来竟将他家所有的奴仆,不分男女老少都判处了死刑。裴特罗纽斯看到这个判决不公,表示了反对。他曾一再地说过,判不判死刑对他来说本来没有什么关系,他对皇帝也只是非正式地表示了一个态度,但他认为这种只有斯吉提人[13]而不是罗马人能采取的野蛮行动败坏了他作为一个“风雅裁判官”的雅兴。由于他的这种表示,一些对死刑判决感到愤慨的人们就更加爱戴他了。
可是裴特罗纽斯对这却不十分关心。他记得人民所热爱的布雷塔尼克[14]后来反被皇帝毒死了,人民所尊敬的阿格丽披娜[15]也被皇帝杀害了。还有奥克塔维亚[16],她被割开了动脉,后来被闷死在潘达塔里亚的蒸气浴池里。鲁贝留斯·普拉乌特[17]也遭到了放逐,特拉泽阿斯不知哪天也会被处死的。因此他认为人民的爱戴乃是一种不祥之兆。裴特罗纽斯疑心很重,而且还迷信。作为一个性行高雅的贵族,他也看不起人民群众,那些怀里揣着炒豆,身上散发着豆香的人,那些在街口或柱廊下声嘶力竭地叫嚷,不要命地进行赌博的下流汉,在他看来根本不算是人。
不管周围的人群怎么对他欢呼,或者向他飞吻,他都不理睬,只是一心一意地给维尼茨尤斯讲佩达纽斯·塞昆德的那桩事情。他还耻笑那些乌合之众的反复无常,因为他们本来反对那次不公正的死刑判决,但在死刑执行后的第二天,当尼禄前往朱庇特神庙时,他们又在路上向他表示热烈的欢呼。舅甥俩的轿子现在来到了阿维鲁努斯书店的门口,裴特罗纽斯于是吩咐停轿。他下轿后,马上去书店买了一本装帧得很漂亮的手抄书,把它送给了维尼茨尤斯。
“这是我给你的礼品。”他说。
“谢谢!”维尼茨尤斯看了一下书名,问道:“《萨蒂利孔》?是新书?谁写的?”
“我写的。可是我不学鲁菲努斯的样,他的事儿我以后会告诉你。我也不做法布雷茨尤斯·维延特那样的蠢事,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我是这本书的作者,你也不要告诉别人。”
“你刚才说你不写诗。”维尼茨尤斯说着翻开了一页,“可是这本书里却有许多诗呀!”
“你读的时候,要注意其中写特雷马奇奥宴会的那一段。说到写诗,自从我看了尼禄的史诗之后,就对这感到厌倦了。你看,维泰留斯要清洗他的肠胃,就把象牙筷子插在自己的喉咙里。有的人用火烈鸟羽毛沾上一点橄榄油或者百里香汁,放到嘴里后,也能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我呢?我只要朗读一下尼禄的诗,就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因此我要感谢他,要对他的诗歌大加赞美一番,这种感谢虽然不是出自我纯洁的良心,但至少是出自干净的肠胃。”
他说完后又叫奴仆把轿子在珠宝商伊多门的店门前停下,等到办完了这里的事情,才让他们一直抬到普劳茨尤斯的家里去。
“路上我要给你讲讲鲁菲努斯的事情,因为他的事情可以说明一个作者的自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可是他还没有开始讲,他的轿子拐过帕特里丘斯街后,很快就来到了普劳茨尤斯的家门口。一个年轻的体格健壮的看门人给他们打开了通往穿堂的大门,他们马上看见门上挂着一个鸟笼,笼子里有一只喜鹊嘁嘁喳喳地叫着,好像在对他们表示欢迎。
在从穿堂走向客厅的时候,维尼茨尤斯对裴特罗纽斯说:
“你注意到了没有,这里的看门人身上没有戴锁链。”
“真是一个奇怪的家庭。”裴特罗纽斯低声回答说,“你一定知道,有人怀疑蓬波尼亚·格列齐娜信一种东方的迷信,崇拜一个叫基督的人,这是克雷斯披尼娜说出来的,她看不惯蓬波尼亚一生只嫁一个男人——不事二夫!今天,在罗马要找到她这样的女人比找半碗诺里库姆的蘑菇还难,为了这个,她还受到过家庭法庭的审讯……”
“你说得对,这是一个很怪的家庭。以后我要把我在这里听到和见到的都告诉你。”
这时他们来到了客厅里。这里管事的奴隶叫总管,这个总管见到他们后,马上派了专事接待的奴隶去向主人禀报了客人的光临,随后他又派了一些奴隶给他们摆好了椅子和踏脚凳。裴特罗纽斯从来没有到过这里,在他的想象中,这个严厉的家庭一定是充满了悲戚的。可是他环顾四周,这个客厅给他的印象却是很不错的,这不仅使他感到奇怪,而且使他感到有点失望。一束明亮的阳光通过屋顶上的巨大天窗直泻而下,照在客厅中间一个小蓄水池的喷泉上,于是化成了千千万万的光点。天阴下雨的时候,这个正方形的蓄水池还可用来盛接天窗上面落下的雨水。水池周围摆满了白头翁和一丛丛盛开着的百合花,有白的,也有红的,可以看出这一家人特别喜爱这种花。此外还有番红色的鸢尾花,它娇嫩的花瓣洒上喷泉的水沫之后,就像镀上了一层闪闪发亮的白银。还有一些种在盆里的百合花被藏放在潮湿的青苔中间,透过它们的枝叶又可看到一些小孩和水鸟的铜像。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头铜铸的水鹿,把它那因受潮侵蚀而绿痕斑斑的头伸到了水边,似要喝水。客厅里拼铺着木质地板,四周的墙壁一部分嵌上了红色的大理石,另一部分用木板钉成,上面画着鱼、鸟和狮身鹰嘴的怪物,缤纷鲜艳的色彩令人赏心悦目。两边侧房的门上都装点着贝壳或象牙。在两扇门间的那道墙前,排立着普劳茨尤斯家祖宗的神像。到处都显示着这个家庭的祥和和富裕,但是又不奢华,使人感到主人的高贵和充满自信。
裴特罗纽斯虽然住惯了他那更加豪华和雅致的官邸,可是他在这里也不感到有伤他的雅兴。当他正要把这个印象告诉维尼茨尤斯时,一个奴隶拉开了隔着客厅和后院的门帘,于是他们看见阿卢斯·普劳茨尤斯从后院深处急急忙忙地走出来。
这是一位已近耋暮之年的老者,但他腰杆挺拔,一头银发显得神采飞扬。他的脸庞虽然短小一些,却像鹫鸟一样威严逼人。他看到来访的人是尼禄的朋友、伙伴和谋臣,感到十分意外,因而脸上露出了惊讶、甚至忐忑不安的神色。
裴特罗纽斯是一个饱经世态、机敏过人的人,当然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在初见的几句寒暄之后,他便以他的全部口才和洒脱说明了他到这里来,是为了感谢普劳茨尤斯对他外甥的照顾,这就是他,作为主人的老朋友之所以贸然来访的目的。
普劳茨尤斯表示热烈欢迎贵客的光临,如果说到感谢,要感谢的倒是他自己。可是裴特罗纽斯却不知道普劳茨尤斯要感谢他什么。
裴特罗纽斯的确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抬起他的那双榛子形的眼睛,力图回想起他为普劳茨尤斯或者其他的人是否效过什么劳,哪怕最最微不足道的效劳。可是他这种回忆是徒劳的,因为他什么也想不起来,除了他专程到此给维尼茨尤斯帮的这个忙之外。如果说他真的为普劳茨尤斯效过劳的话,那一定是无意的。
“我很尊敬和喜爱韦斯巴芗[18],一次,他在聆听皇帝的御诗时,倒霉地睡着了,你当时可救了他的命啊!”普劳茨尤斯说。
“他没有听见这些诗倒是他走运。可是我认为,这件事也可能最终导致不幸的结局,因为红胡子本来要派一个百夫长,奉旨到他家里去,好言悦色地叫他割开自己的动脉。”
“可是裴特罗纽斯!你笑话过他的这个打算。”
“是的,但也不完全是这样。我对他说,如果奥尔菲斯[19]的歌声能使猛兽入睡的话,那么陛下的诗也给韦斯巴芗起了催眠的作用,陛下和奥尔菲斯一样,都成功了。要责备红胡子只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就是在小骂中掺上一大堆吹捧。我们敬爱的皇后波贝亚就很懂得这一点。”
“很遗憾,如今的世道就是这样。”普劳茨尤斯回答说,“我少两颗门牙,是被一个不列颠人的石头砸掉的,所以我说起话来有杂音。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也是在不列颠度过的。”
“因为你在那里打了胜仗。”维尼茨尤斯插进来说。
裴特罗纽斯怔了一下,他怕这位军队的老统帅听了后开始没完没了地讲起他的战争经历来,因此马上把话题一转,说有个叫科达的人告诉他:有个农民在帕拉内斯特附近发现了一只双头小狼的尸体。在前天的那一场暴风雪中,雷电又劈掉了路娜[20]神庙上的一个屋角。现在已是深秋,还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科达还说,神庙的祭司预言,这意味着罗马城将要毁灭,或者至少一个大的家族将要灭亡,只有供奉别的祭品才能挽救这个危局。
普劳茨尤斯听了裴特罗纽斯的这些话,也觉得这些征兆不可忽视,如果积恶太多,就会激怒诸神,这是不奇怪的。只有及早献上供品,恳求神明的宽恕,才是最妥善的办法。
裴特罗纽斯又说:
“普劳茨尤斯,府上不很宽敞,可是住着像你这样的大人物,它当然是太小了。舍下和府上差不多大,因为住着像我这样的平庸之辈,它又显得太大了。如果像皇宫那么宏伟的建筑物真的要变成废墟的话,那么你我为了拯救它,该不该都献上一点贵重的祭品呢?”
普劳茨尤斯一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是裴特罗纽斯对于他的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却感到有点不快,因为裴特罗纽斯认为他自己虽然有时分不清是非,但他从来不告密,和他谈话是大可放心的。不过他随后还是改变了话题,开始对普劳茨尤斯的住宅和这一家人的高雅情趣大加赞美起来。普劳茨尤斯听了后也说:
“这是一幢古老的宅院,由我继承之后,这里什么都没有改变。”
当奴仆把客厅和后院之间的门帘拉开后,这座府邸的内景就什么都可以看见了:后院往下有一道长廊通往内厅,从内厅一直可以望到花园里。这个花园远看就像装在深色的镜框里的一幅色彩明丽的图画,从那里传来了孩子们一阵阵欢快的笑声。
“啊!统帅!能否让我们去那里听听这种天真的笑声?今天能够听到这样的笑声是很难得的。”裴特罗纽斯说。
普劳茨尤斯起身回答说:
“好的!这是小儿在和莉吉亚玩球。如果说到笑,裴特罗纽斯,我想你的全部生活都是充满了笑的。”
“人生本来就很可笑嘛!所以我要笑。可是这里的笑声却不一样。”裴特罗纽斯答道。
“舅父白天从来不笑,晚上却要笑一整晚。”维尼茨尤斯又插了一句。
说到这里,他们穿过了整个住宅,来到了后花园里。小普劳茨尤斯正在那里和莉吉亚玩球,几个专门侍候这种球戏的人叫作捡球的奴隶,把球从地上一个个地捡起来递给他们。裴特罗纽斯马上冲莉吉亚瞥了一眼,小普劳茨尤斯看见是维尼茨尤斯便迎了上来。但维尼茨尤斯却一直走到了那个美丽的姑娘面前,向她鞠了一躬。莉吉亚手里拿着一个球,她的头发有点散乱,呼吸有点急促,脸上泛着红晕。
蓬波尼亚·格列齐娜坐在花园的餐室里。这里有许多高悬着的常春藤、葡萄和羊踯躅花枝叶,都是用来遮阳的。他们上前和女主人见了礼。裴特罗纽斯虽然没有到过普劳茨尤斯的家里,但他认识蓬波尼亚,因为他早先在鲁贝留斯·普拉乌特的女儿安迪斯第亚家里见过她一面,后来在塞内加的家里和波利约恩家里又见过两次。蓬波尼亚面带忧郁而又安详的神色,她那高雅的仪表和谈吐,落落大方的举止都使得裴特罗纽斯情不自禁地为之赞叹,因而也完全否定了他对女人的看法,使他这个自认为无可救药、可又无比自信的人不仅对她肃然起敬,而且也失去了他的自信。现在,当他向蓬波尼亚对维尼茨尤斯的照顾表示感谢的时候,便不假思索地称她为“夫人”了,这是他过去和卡尔维亚·克雷斯披尼娜、斯克雷波尼亚、瓦列利亚、索莉娜以及其他上流社会的女人谈话时从来没有过的。可是他在向她表示问候和致谢之后,又颇有怪罪地说,由于她在公共场所很少露面,大家在竞技场和剧院里都见不到她。蓬波尼亚于是把手放在她丈夫的手掌里,心平气和地回答说:
“我们两个人都越来越老了,所以爱在家过点清闲的日子。”

裴特罗纽斯对这本要表示一点不同的看法,可是普劳茨尤斯又用他那带杂音的口齿接着说了下去:
“我们对那些用希腊名字称呼我们罗马诸神的人,都感到越来越隔阂了。”
“其实长期以来,人们只在他们的演讲中才把那些神明称呼一下。可是自从希腊人教会了我们演说,连我自己也觉得,叫‘赫拉’比叫‘朱诺’[21]容易。”裴特罗纽斯毫不在意地答道。
他说完后,便把眼光投向蓬波尼亚,好像他要表明在她面前他是想不起任何别的神的。后来他又对她关于年老的看法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人的确老得很快,可是有些人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他们就不一样。还有一些人连死神是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裴特罗纽斯的这些话说得很坦率,因为他看到蓬波尼亚·格列齐娜虽已年过半百,却保持着异乎寻常的雅嫩隽秀。她虽然身穿深色的裙衣,面带严肃和忧郁的表情,但她有一个俊俏的额头,一张姣小的面孔,依然使人感到真像一个漂亮的少妇。维尼茨尤斯上次住在这里养伤时,就和小普劳茨尤斯交上了朋友,因此小普劳茨尤斯前来邀他去打球。莉吉亚也跟在他们后面走进了餐室,站在常春藤的天棚下。那频频闪烁的阳光这时照在她的脸上,使裴特罗纽斯觉得她比他刚才第一眼看去时还要漂亮,简直是一位仙女,可他直到现在还没有和她说话呢!因此他马上站了起来,向她鞠了一躬,用一句奥德修斯在迎接瑙西卡娅时朗诵的诗代替了平常的问候:
我不知道你是女神还是凡间的少女,
如果你是凡人所生的姑娘,
那么你的父母和兄弟,
定要受到加倍的祝福。
这位社交名士的儒雅礼数首先给蓬波尼亚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莉吉亚听到这些话后,一下子便羞得满脸通红,连眼睛都抬不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她的嘴边露出了一丝调皮的微笑,她的脸上也表露出了少女羞怯和意欲表达的矛盾心情。这种表达的欲望终于占了上风,因此她对裴特罗纽斯望了一眼,也用瑙西卡娅的话来回答他,而且她在引用这些话时,就像背诵功课一样,一口气就说完了:
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脑袋。
说完她又转身回到了她原先站立的地方,然后又跑掉了,仿佛一只受了惊的小鸟似的。裴特罗纽斯感到非常吃惊,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维尼茨尤斯说的蛮族出身的姑娘的口中能够说出荷马的诗句。因此他向蓬波尼亚投去了探问的目光,但是蓬波尼亚没法表示回答,因为她这时候正在笑容可掬地望着她丈夫脸上露出的自豪的神色。
老普劳茨尤斯之所以感到自豪,首先是因为他对莉吉亚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地疼爱;再者,虽然他出于罗马人的许多古老的成见反对希腊语,不让它在人民中普及,但他还是认为,会说希腊话乃是社交文明的最高级的表现。他曾经为自己没有学会这种语言而暗自懊恼,怕裴特罗纽斯把他们一家看成是野蛮人。所以他一看见他的家里有人能在这位高贵的绅士和显赫的文人面前用荷马的语言和诗句来答话,真是高兴极了,便即刻转身对裴特罗纽斯说:
“我们家里请了一位希腊语教师。他除了教我的儿子之外,也让姑娘前来听课。这是一只鸟,一只可爱的小鸟,我们夫妇俩都和她处得很好。”
裴特罗纽斯通过常春藤和羊踯躅花枝叶间的空隙,看见了对面的花园和在那里玩球的三个人:维尼茨尤斯脱去了宽袍,只穿一件衬衫,把球高高地抛起。莉吉亚站在他对面,高举着双臂,力图把球接住。第一眼望去,这个姑娘给裴特罗纽斯的印象并不很深,而且他还觉得她的身子太瘦小,可是当他在餐室里走近前来一看,便觉得她简直是一颗明丽的晨星。作为一个鉴赏家,他在她的身上已经发现了某种极不平常的东西。他自上而下地打量着她的全身,要对那里的一切做出正确的评价:她那玫瑰色的、明净如洗的面孔和清新雅嫩的嘴唇像是专为亲吻而生的。她的一双明媚的眼睛就像湛蓝的大海,她的前额白净得像雪花石膏一样。在那一头浓密和盘曲着的黑发丛中,闪烁着琥珀和科林斯铜饰的光辉。她的轻柔秀美的脖颈,仙女般的肩背,窈窕俊逸的体态都焕发着五月的青春,比刚从蓓蕾里绽放出来的鲜花都显得更美。而这一切在他那里也唤起了一个艺术家、一个美的鉴赏者的雅兴,使他感到在这个姑娘的塑像下面,可以写上“春天”二字。这时他还突然想起了赫雷佐泰米斯,虽然她的发上撒着金粉,眉上描着黑黛,但她却显得形容憔悴,就像一枝枯黄凋落的玫瑰,而罗马城里还有许多人非常羡慕她呢!接着他又想起了波贝亚,在他看来,久负盛名的波贝亚不过是一尊没有灵魂的蜡像。只有这个塔拉格利[22]的瓷形姑娘不一样,她不仅散发着春天的气息,而且有一个光彩照人的“灵魂”。这个灵魂的光芒是透过她的玫瑰色的肉体照射出来的,就像火光透过灯罩一样。
裴特罗纽斯暗自想道:
“维尼茨尤斯的眼力不错呀!我的赫雷佐泰米斯确实老了,老了……像特洛亚一样地老了!”
然后他把手指着花园,转过身来对蓬波尼亚·格列齐娜说:
“我现在才明白,夫人!你们二位为什么宁愿待在家里,而不去帕拉丁宫参加宴会,或者观看竞技场上的表演了。”
“是的!”她望着小普劳茨尤斯和莉吉亚那边回答说。
这时候,老统帅开始讲起了姑娘的身世和那些住在茫茫北国的莉吉亚民族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他许多年前在阿泰留斯·希斯泰尔那里听到的。
花园里的三个人打完球后,便在沙地上散步,他们由于身后衬着深色的桃金娘和柏树,看起来就像三尊白皙的雕像。后来莉吉亚拉着小普劳茨尤斯的手,又来回地踱了一阵,便在花园中间鱼池旁的一条板凳上坐下。过了一会儿,小普劳茨尤斯忽又站了起来,原来他要去逗吓那些在清冽的池水中翔游的小鱼。维尼茨尤斯仍在说着他们在踱步时已经开始说的话,他说话的声音很低,还有点颤抖:
“是的!我一脱下童装就到亚细亚军团里去了。我对罗马并不熟悉,既不了解这里的生活,也不知道什么叫爱情。我虽然会背诵一点阿纳克瑞翁[23]和贺拉斯[24]的诗句,可是当我惊慌得说不出话来,或者找不到适当的言辞来表达的时候,我就不会驾轻就熟地引用那些古诗了,而裴特罗纽斯却是做得到的。我小时候在莫佐纽斯办的学校里读过书,老师对我们说,一个人的幸福就是把诸神的要求当作自己的要求,只是看他有没有这种意愿和决心。但我认为幸福不是这样,它更伟大也更宝贵,它和意志无关,幸福是爱情创造的。这种幸福就是天神也十分向往,所以我也是很向往的。莉吉亚!我虽然至今还没有感受过爱情,但我要学天神的榜样,找到那种能够给我幸福的爱情……”
维尼茨尤斯说到这里便停了下来,只听见小普劳茨尤斯为了惊吓小鱼,将石子扔到池里激起轻微的水声。
随后他又开始用一种更加轻柔、更加细小的声音说:
“你知道韦斯巴芗的儿子蒂杜斯吗?有人说他刚刚成年就如痴如狂地爱上了贝列尼卡,还差点害相思病死了……啊,莉吉亚!我也会这么痴情的……财产、荣誉、权势不过是过眼烟云,富人有凌驾于他的更加富豪的人,显赫者在显赫于他的人面前会变得渺小,强权也会被强权征服的。但一个人,即便一个最最普通的人,他在他的怀中如能触到恋人跳动着的胸脯,或者能够亲吻她的嘴唇,那么他所感受的幸福和快乐,就连皇帝陛下或者天神也是感受不到的……所以爱情使我们和天神平等了,啊!莉吉亚!……”
莉吉亚听到他的这些话既感到惊讶和不安,又好像听到了希腊笛子和竖琴演奏的一首欢乐动人的乐曲似的。她还以为维尼茨尤斯在对她唱一支神奇的歌,这歌声在她的耳边回响,使她热血沸腾,也使她的心里充满了忧郁、惶恐和无可言状的快乐。她觉得他说出了以前就在她的心上可她却不知道如何表达出来的东西,而且他也唤醒了她身上一直沉睡着的东西。因此就在这个时刻,她的朦胧的梦境变得愈来愈清晰,愈来愈令人心醉了。
太阳早已越过了第伯河,渐渐沉落在雅尼库尔的山陵上,在一动不动的柏树上撒下了万道霞光,使整个天空都变得红通通的了。莉吉亚抬起她那宛如梦中苏醒的蓝莹莹的眼睛,向维尼茨尤斯投去了一瞥。维尼茨尤斯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把身子躬了下来,眼里透出了恳求的神色,使莉吉亚突然感到他比她在神庙祭坛上看到的那些希腊和罗马的神像都漂亮得多。于是他用手指轻轻地拉着她的手臂,问道:
“莉吉亚,你明白我对你说的这些话的意思吗?”
“不明白。”她的声音是那么细小,使他几乎都听不见了。
维尼茨尤斯不相信她的回答,而且他还使劲地把她的手拉到自己身边。如果不是老普劳茨尤斯正从两边种着桃金娘的羊肠小道朝他们走过来,他就要把这双俊美的小手放在他那像被槌子击打而怦怦跳动着的胸脯上。因为这位貌若天仙的姑娘已在他心上激起了强烈的欲望,他要向她倾诉炽热的衷肠。但这时候,普劳茨尤斯已经来到了他们跟前,对他们说:
“日头落山了!小心夜里着凉,和利比蒂娜[25]是开不得玩笑的。”
“我不冷。我没有穿外衣,并不觉得冷。”
“你们看,日头在山那边只剩下半个圆盘了。”老普劳茨尤斯说,“要说气候,只有西西里才是真正暖和的,那里的人在黄昏的时候都聚集在集市广场上,他们一起唱着歌,要和正待离去的福波斯[26]告别。”
普劳茨尤斯因为讲起了西西里的情况,便把刚才说过要警惕死神的话给忘了。他说那里有他的领地和他心爱的大农场,他曾不止一次地打算搬到那里去住,他的一生熬过了无数的寒冬霜雪,现在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要在那里安度晚年。趁现在树叶还没有脱落,晴朗的天空在对罗马表示友好的微笑,不可失去这个美好的时机。一旦葡萄叶儿变得枯黄,阿尔班山上降下了大雪,诸神在坎帕尼亚平原上刮起了刺骨的寒风,到那时候,谁知道,他的全家也许就得搬到乡下那座寂寞的庄园里去了。
“你要离开罗马,普劳茨尤斯先生?”维尼茨尤斯听到他的话后,突然感到不安,问道。
“我早就有这个打算,因为西西里岛比这里清静,也比这里安全。”普劳茨尤斯回答说。
接着他又夸耀他的花园、他的牲畜和那幢被绿荫遮掩的房子,还有那片长满了麝香草和薄荷的山丘,花草丛中飞着一群群蜜蜂。可是维尼茨尤斯根本没有心思去听他的这支田园牧歌式的曲子,他怕他会失去莉吉亚,他凝视着裴特罗纽斯,好像只有他的这个舅舅才能够救他。
坐在蓬波尼亚旁边的裴特罗纽斯正在如痴如醉地欣赏着那红日西沉的美景,目不转睛地望着对面的花园和肃立于水池旁边的人影。这些人影的背后衬托着黑黝黝的桃金娘,他们身上的白衣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辉。天空中的红霞逐渐染上了一层紫色或堇色,最后变成了一块白色的宝石,整个天空都呈现出了百合花的颜色。柏树黑色的姿体比白天显得更加清晰可见,在人和树之间,在整个花园里都充满了黄昏的宁静。
裴特罗纽斯对于这种宁静,尤其是对这里的人们感触很深。他在蓬波尼亚、老普劳茨尤斯的脸上,在他们的孩子和莉吉亚的脸上,都看到了一种在他每天,不,在他每天每夜都接触到的人们的脸上所看不到的东西。那是一种光明,一种恬静,一种在他们生活中直接表露出来的从容不迫。他惊异地发现,虽然他的一生都在追求美和欢乐,可是这里的美和欢乐却是他从来没有感受过的。裴特罗纽斯这时候也无法隐瞒他的这种想法,于是转过身来对蓬波尼亚说:
“我觉得,你们这个世界和我们的尼禄统治的那个世界真的不一样啊!”
蓬波尼亚抬起她那姣小的面孔,两眼凝视着晚霞,憨直地回答说:
“统治世界的不是尼禄,而是上帝。”
随后大家都沉默了。这时在餐室近旁可以听到老统帅、维尼茨尤斯、莉吉亚和小普劳茨尤斯走在林荫道上的脚步声。裴特罗纽斯在他们来到之前又问:
“那么你信仰诸神吗?蓬波尼亚!”
“我只信上帝,上帝只有一个,他是公正的,也是万能的。”蓬波尼亚回答说。
[1] 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卡比托尔朱庇特神庙是古罗马的主要神庙。
[2] 雅典娜,希腊神话中护佑和平、劳动和科学的女神,司丰产和智慧的女神。
[3] 萨迪尔,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形状的森林男神,具有懒惰、好色、酗酒的性习。
[4] 卡比托尔,罗马城中的七个山丘之一,有著名的卡比托尔朱庇特神庙。
[5] 尤利乌斯·恺撒 (公元前100—公元前44),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和作家,曾建立独裁统治,制定历法。著有《高卢战记》《内战记》等。
[6] 卡斯托尔和波卢克斯是宙斯的两个儿子,一对孪生兄弟。
[7] 维斯塔,罗马神话中的灶神和火神。
[8] 克维雷特人,古罗马有公民权的居民。
[9] 赫拉斯,地名,在希腊中部,后来将古希腊人居住的地方称为赫拉斯。
[10] 塞拉庇斯,古希腊和埃及共尊的一位神祇,能使植物死而复生。
[11] 伊西斯,古埃及最重要的女神,司生命和健康,庇护丰产、生育和繁殖的女神。她丈夫奥西里斯是古埃及自然界死而复生之神。奥西里斯为恶煞塞特杀害,尸体被剁成碎块,抛向全世界,伊西斯悲恸欲绝,到处寻找丈夫的尸体,后来她把丈夫的碎尸块收到了一起,奥西里斯因此死而复活,成为冥王。
[12] 库柏勒,古小亚细亚崇拜的女神,称为“太阳母”,是诸神以及地上一切生物的母亲,她使自然死而复活,并赐予丰收。
[13] 斯吉提人,古希腊罗马时代居住在黑海一带的一个民族。
[14] 布雷塔尼克,克劳迪乌斯皇帝的儿子,尼禄的异父兄弟。
[15] 阿格丽披娜,克劳迪乌斯的妻子,尼禄的母亲。她为了让尼禄当皇帝,毒死了丈夫,但她后来又被尼禄杀害。
[16] 奥克塔维亚,尼禄的结发妻子。
[17] 鲁贝留斯·普拉乌特,蒂贝留斯的曾孙。
[18] 韦斯巴芗(9—79),古罗马皇帝,弗拉维王朝(69—79)的创立者。本为尼禄的将军,尼禄死后,在68至69年的内战中被军队拥立为帝,在位时整顿财政,加强集权统治,重建卡比托尔王朝,还建立了罗马大斗兽场、凯旋门等。
[19] 奥尔菲斯,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传说他发明了音乐和作诗法,他的歌声能使树木弯枝,顽石移步,野兽俯首。
[20] 路娜,古罗马的月亮女神。
[21] 朱诺,罗马神话中主神朱庇特的妻子。
[22] 古希腊地名,这里以产瓷器闻名。
[23] 阿纳克瑞翁(约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抒情诗人。他的作品大都歌颂酒宴和爱情。
[24] 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前8),古罗马诗人。他的作品有《讽刺诗集》《长短句集》《歌集》等。
[25] 利比蒂娜,古罗马的大地女神。大地是万物生长之处,又是万物归宿之地,因此她专司丰产和死亡。
[26] 福波斯,意为“光明”或“光辉灿烂”,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