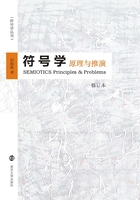
3.共时性
系统性连带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所谓“共时性”,在索绪尔理论的四个二元对立(能指/所指,语言/言语,共时/历时,组合/聚合)中,这条似乎最容易理解,实际上还挺复杂。共时性问题,是索绪尔为语言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索绪尔之前的语言学,主要在语言的演变上下工夫,而索绪尔的系统观,注重的是一个系统内部各种元素之间的关系,因此要求从一个“共时角度”来观察,系统才能运作。系统各因素之间,不是历时性的联系,而是在某个条件下共存的关系。
共时观念,给语言学的研究带来重大变化,也使符号学一开始就落在一个非常有效的模式之中。但共时观念还没有被真正弄清楚,就被追赶时髦的学界宣布过时,所以本书稍微多花一点功夫解释一下。首先,共时与历时不可分,每个系统都是在历时地转化为一连串的共时局面中形成的。没有一个符号系统能历时不变,我们只能谈历时性中的共时性,这一点容易理解。
关于共时与历时究竟如何区分,却一直有很多误解。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中举交响乐为例,说一首交响乐是共时与历时配合而成。某个瞬间的和声与配器,是共时性的,交响乐的演奏则是历时的。(13)巴尔特认为西餐中一道道上菜是历时的。(14)两位大师恐怕是弄错了。他们把符号系统的空间展开/时间展开,误作为共时性/历时性。有的符号文本在空间中展开(例如壁画、建筑),有的符号文本在时间中展开(例如电影、仪式)。哪怕需要在时间中展开的文本,依然可以被看成一个共时结构,只要展开的时间过程没有影响组分的相互关系和意义的变化。一本小说看上去是空间的存在,而讲故事需要时间,但一本小说和一则故事都不是历时的。当符号组合被看成一个文本,或一个系统,它们就是共时的。
列维-斯特劳斯和巴尔特关于一首交响乐或一顿餐是“历时性”的说法,颇类似钱锺书所引《优婆塞经》中的例子:“有智之人,若遇恶骂,当作是念:是骂詈字,不一时生;初字生时,后字未生,后字生已,初字复灭。若不一时,云何是骂?”钱锺书认为这种态度,可以“以资轩渠”(15)。
符号学讨论的共时,不是指符号文本的空间(非时间)展开方式,而是解释者看待这个系统的角度。对于一个系统的研究,可以有共时与历时的两种侧重。一部交响乐,一顿晚餐,哪怕不是严格的“共时发生”(空间并存),也可以被看做共时系统,即可以当做一个系统给予解释。
斯瓦西里语把周围所有的人分成“活人”、“撒哈”(sasha)、“扎马尼”(zamani)三种。活人是在世的人;撒哈是人已去世,但是在世的有与他相识的人;扎马尼是已经死去,并且所有认识他的人也都已经死去的人。(16)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系统。原先是历时的关系,在意义关系中变成了一个共时系统,三种“人”互相区别,必须用不同方式处理,谈论扎马尼已经无人对证。其他语言对历时的两种死者不加区别,是因为更多地凭借共时的书面记载谈论他们。
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只是观察解释符号系统的角度之分,并不是严格的时间问题。叶尔姆斯列夫说得一清二楚:“(共时性是)语言成分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而不是经验上的共时性,而所谓历时性也只能看成一种关系转换系列。”(17)巴尔特后来似乎也明白了这一点:“时装的共时性年年风云变化,但在一年之内它是绝对稳定的。”(18)为什么时装系统“一年之内”是稳定的?因为时装需要用四个季节展开整个系统。巴尔特对共时性的看法,在几年中前后矛盾,只能说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巴尔特知道我们至今尚在一句一句认真读《符号学原理》,他必定会郑重其事地做个自我修正吧。
既然系统必须从“共时”角度观察,索绪尔符号学就带上一种共时偏向,这一点受到不少关注社会历史的理论家抨击。既然系统只有在共时状态中观察,历史就只是系统的叠加。(19)符号系统的一系列共时状态,靠“自组性”组成一个贯穿了的演变系列,才出现系统的历时性,因此难以否认,系统观是共时性优先。虽然共时性并不否认历时性,当共时结构被特别关注时,历时关系容易被忽视。
由于索绪尔理论,至少共时性作为一种可供选用的研究角度出现,只要这种观念没有独霸学界,就不应当说是坏事。这个理论兴起之初,不少学者赞美有加。巴尔特甚至说,索绪尔提出共时性原理,“意味着起源概念的退场……个体不再相当于‘子女’,而是相当于‘同胞’;语言结构不再是一种‘贵族制’,而是一种‘民主制’”。他甚至感慨地说索绪尔的理论,与索绪尔本人的“籍贯”有关:“只有一位卢梭的同乡,住在具有数百年民主制传统的日内瓦,才能想到把语言的意义比拟为社会契约。”(20)这个赞美太政治化,也太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