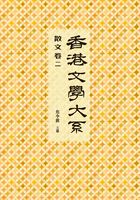
玄囿
新歲感
窗外蕭蕭瑟瑟地下着雨,這是歲暮的一個晚上。我正在挑燈夜讀之際,寒氣暗侵( )幕,畸零的旅人,對此怎能壓得住內心的惆悵!偶然想起日昨與幾個朋友於品茗時所談及「過年」之事。他們中的一位說:「近幾年來,每逢過年的時節,非窮即病。」言下似乎有不勝感慨的樣子。其實我自己又何嘗不是遭於這相似的厄運中呢——如今計算起來,離家不覺已近六載了,唐人詩云:「每逢佳節倍思親」;但是像我一樣畸零的旅人,經已過慣了飄泊的生涯,對於家的觀念,逐漸地給外部生活磨洗得淡薄下去了。
這九年來的教書生涯,天天與純潔的青年們混在一起,他們有着光和熱,也曾給我這凄清的環境渲染得很美麗。他們愛護我,幫助我,我也愛護他們,幫助他們。在彼此互助相愛之下,使我忘記了一切飄零之苦!不獨如此,並且使我有着一種非常的祈待,這不是希望我自己能夠顯達富貴,養尊處優,而利用他們;這希望還是在這一羣純潔誠摯的青年的身上。為了這,我曾下了最大的决心,把我自己的生命,完全付託在無數的孩子的身上,犧牲小我而為大我。
「過年」,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一個名詞;特別的在孩子們的頭腦中,似乎有着更美麗的想像。可是對於我,畢竟是惹起了無窮的悵惘與寂寞!當這時節的來臨,我底周圍,忽然變得更加寥落起來——孩子們趁着年假都歸去了,同事們大都有家的,也得要回去叙天倫之樂事。平日與我在一起的人們,這時候都跑光了,剩下一所廓落的校舍,給我留守;好在我性愛靜,我怕太熱鬧,所以到這時候,我還是深居簡出,閉門度歲;一天到晚,在這清幽的環境裏,踱來踱去,從頂樓行落地下,從課室轉( )課室,或讀書,或彈琴,或靜聽外面的炮竹聲,以消磨這一段日子,等到復課後,我底生活才始恢復常態。八年來如一日,過去每一次新年佳節,都是一樣地糟蹋了,任它幻滅。在我個人而論,則「窮也非病」,於八九年來的飄泊生涯之中,年年歲歲一床書,一肩行李,兩袖清風。因此對這燈紅酒綠的新年佳節,不是討厭它而是窮於酬酢,怕與勢利周旋,這是落得孤寂的因素吧!直至去年,我在上海的家庭中,度過了一年的生活,終於覺得:「懷與安,實敗名。」又〔飄〕然南返,奔向自己的前程。只幾個月的時光,而遭逢這次的變亂,刧後餘生,好在得苟存性命,再有苦可吃,這是不不幸中之幸。
「桃符萬戶更新」,舊節的新年又去了,這與我相遇合,似乎又有着另一種不可磨滅的因素,也是和從前一樣的困頓與飄零,而且是有家歸未得;而且是無前程可奔,要滯留在悲鬱的境地裏。
新歲的苦雨孤燈之夕,如何能不惹起我底惆悵呢!畸零人,我畢竟是個畸零人啊!
選自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香港《南華日報·前鋒》
夜談與散文
「談」是樂事,再加上一個「夜」字,就更加顯出此番談話的靜態美。古來無論中外的文人雅士,都很讚美「夜談」。他們喜歡夜談,是為着避免環境上的繁囂,抱着一種野心,要擁有整個靜靜的宇宙,而發表他們積累在腦際的美麗的意象,給二三知己欣賞,志在博得一般的共鳴。因此,就散文之勃興而論,這似乎與談天有着密切的關聯。林語堂謂:「我相信一個國家的真正優美的散文,是必須在談天一道已經發展到成為一項藝術的地步方能產生。這個情形,在中國和希臘散文之發展中最為顯明。」
其實一篇真正優美的散文之產生,的確要從靜靜的環境中,輕輕地淡淡地描寫出那種溫柔婉順的靜態美;要用纖妙之筆調去描寫。所以晚上的會晤,竟然在散文與詩詞的藝術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時也作了散文與詩詞上( )取現成的材料。
試想想看吧!唐詩中之「今夕復何夕,共剪燈燭光」與「何當共剪西窻燭,却話巴山夜雨時」。像這些詩篇的內容與結構,雖然是靜態之下的夜談藝術的描寫〔,〕其中隱寓着一段纏綿不盡的情緒。風雨之夕,無論在任何的一個季節裏面,都很可以引導人進入談天的世界;這時候,如果有知己會合,話談得投機則更好;一甌清茶,一碟花生米,儘可以於此而消遣無慮。不然,即使召集家人,漫談祖代之嘉言懿行與軼事,乘人之不覺,寓以家訓,亦是一種取寫意的家庭教育方法。上自歷史掌故,宮闈秘史,文人軼事;下至民間傳說,神話,談狐說鬼,以迄於螞蟻蒼蠅的瑣碎之事,皆可作為夜談的資料。
只要「眼前一笑皆知己,座上全無礙目人」,則「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曾常聞」的(金聖嘆言)。所謂「談言微中」,那就大可舒舒服服地,將凝結了的心緒,盡情放寬,使生命安排在閒息的氛圍中,其樂正無可比擬!至於談天的地點,無論日夜,最好是隨遇而安。正如林語堂說:「在十八世紀的沙龍(即書室)中可以談關於文學或哲學的閒天;但在農家木桶的旁邊,也何嘗不可以談。或在風雨之夕的航船中,對河船上的燈光微映水波,而臥聽船夫閒談當地的一個女子怎樣被選去做皇后娘娘的故事。這類談天之所以悅人者,實在於所得的樂趣,視地點時間和談者而各不相同。我們所以能牢記不忘者,有時因為談天的時候是正在桂子飄香,秋月懸空的佳景下;有時因為是正在風雨之夕,一爐柴火之前;有時因為是正在一個高亭之上遠眺河中船隻往來,而當中有一隻船忽因潮流過激而側翻的時候,或是在清晨坐在車站待車室的時候。這種眼前之景象,常和所談的天聯繫一起,因即使我們永不能忘。」那種永不能忘的景象,便可以合作詩的材料,畫的材料(如最後的晚餐圖之類),散文的材料。所謂「事在性情之際」,一個作家的「性靈」在心底流動的時候,那種永不能忘的景象再現的時候,頭腦中有如電陣一般的攪擾,覺得非將他的觀念發洩出來不能安逸,乃將它們寫在紙上而覺如釋重負,這就是文藝的產生之經過。
推而論之,在靜態之下,時常會產生出一種高超的藝術美,這種藝術美,如果發現在一個美術家或文藝家的眼底,他自然不輕易放過它,就要去欣賞它,最後那種永不能忘的景象,便與他的性靈匯合而交流,在腦際起着如電陣一般的攪擾,藝術作家要把他這一點藝術觀念發洩出來,就產生出藝術的作品。靜靜的夜,是幽雅的背景,更有着輕鬆的談話在這靜靜的夜底雰圍中輕輕地淡淡地迴蕩着,穿插着,宛如人間文藝的仙境,其中清福,並非一天忙到晚的生意人,吃了晚飯就睡覺,鼾聲如牛者所能享受得到的了。故此有人說,這些俗人,於文化决沒有幫助的。
在一個幽美的晚上,談話,當然哪,單獨一個人就永遠不能做成談話的場面的;除非是自言自語。那麼,最低限度要有兩個人或兩個人以上,有了叙會的機緣。談天然後可以開始,在這場所中,是觸發人類靈感的最好的機會。語言是表情達意的工具,靈感觸發語言之發出,表得妙,達得妙,就是語言的藝術,這些妙言妙語,筆之於文,就是文藝,所以文藝之產生是出於偶然的,並非出於當然的。一篇傑作,能垂千古而不朽,一件好的藝術作品,能烙印在人類的腦根裏永久不會幻滅。由此,夜談一道可能成為藝術的真正優美的散文的產生地,是無可置疑的了。
選自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至十七日香港《南華日報·前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