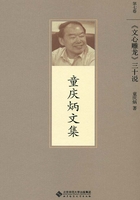
三、“奇正华实”说的理论意义
本篇的理论意义在于,刘勰在肯定楚辞推进了文学新变的前提下,借用兵家的“奇正”观念,具体论述了文学创作变化中的艺术控制和调节问题。
刘勰在给予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以很高的评价之后,给出了“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坠其实”的理论概括。这句话是本篇的点睛之笔,准确地揭示了楚辞的特色,指出楚辞的特点是在“奇正华实”之间实现了一种艺术调控。楚辞所抒发的思想感情是纯正的,但语言的表现形式则是艳丽奇特的,它一方面为中国文学开辟了新局面,树立了新传统;另一方面,又肯定了风雅、经典作为旧的传统是不可丢弃的。刘勰又从理论的角度提出一个创作中的“奇与正”、“华与实”的关系问题,在奇与正、华与实之间要保持张力,既不能过奇而失正,过华而失实;也不能为了正而失去奇、过实而失去华。总之,要在奇与正、华与实之间保持平衡,取得一个理想的折衷点,使作品产生一种微妙的艺术张力。
刘勰的理论贡献在于他把兵家的“奇正”观念转化为文学理论的观念。“奇正”观念由《孙子兵法》的《兵势篇》提出:“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2]又“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3]又:“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4]孙子兵法中的奇正指奇兵和正兵的战术运用。这里包括两层关系:一是用兵有两种,一是奇兵,一是正兵,正兵应战,但往往靠奇兵取胜;二是奇正相生,奇变为正,正变为奇,可以无限地循环变化,以获得战争的胜利。
刘勰将“奇正”的战术变化运用于文学创作的研究。在《辨骚》篇提出“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坠其实”,这主要在第一层意义上运用奇正的观念,意思是楚辞创作的成功,纯正的思想感情与奇特的夸张、想象(包括神话的运用)相互结合,即纯正的思想感情不是平板地、凡庸地展开,而是在奇特的夸张、幻化的神话世界中艺术流动,奇与正、华与实两者相互制约又相互为用。在《定势》篇刘勰又进一步提出“执正以驭奇”,“奇正虽反,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这主要是在“奇正相生”的第二层次来加以运用了。就是说文学创作中也有奇正相通和转化的问题,如奇特的、夸张的描写对作家来说是属于“奇”的成分,但写出后则可能被读者理解为“正”的成分了。刘勰把兵家“奇正”转化为文论观念,其旨意在提出艺术节制原理,即以“正”节制“奇”,不让奇诡而失去雅正;以“奇”调整“正”,不让雅正流于呆板而无生气。
刘勰认为《离骚》的成功,就在于巧妙地运用了这种艺术控制。“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坠其实。”奇与正,华与实,看似两对概念,实际上“华与实”不过是补充、加强“奇”与“正”。“正”、“实”相同,是指内容而言的,要求思想感情的雅正,合乎经义;“奇”、“华”同义,则主要是指语言表现和技巧运用的,要求语言活泼多姿,运用奇诡的幻想、夸张,使艺术形式气象万千。在奇与正、华与实之间,通过调节,掌握了一定的度,从而形成内容与形式之间富有弹性的艺术张力。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刘勰的艺术节制思想,不仅是他借用兵家的思想,同时也是继承了儒家的诗学原则,这里并不存在矛盾。《论语》:“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左传》写季札观乐,其中也有“勤而不怨”、“忧而不困”、“乐而不淫”、“怨而不言”、“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的说法。过去,对这一原则的看法多从政治和伦理的角度加以褒贬,认为孔子鼓吹“中庸”之道,让百姓只能“怨而不怒”,而不能造反。刘勰显然也对儒家这一思想有很深的理解,并认为它与兵家的奇正观念是一致的。于是他把孔子的思想当成是诗学原则来加以理解,并参照兵家思想加以改造,提出“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坠其实”的艺术节制理论。实现了伦理原则向诗学原则的转化。这种奇正相参、华实相配的艺术节制理论对后代也有很大影响,如唐代皎然《诗式》论诗:“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5]这种在句式上的雷同,说明他们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明代谢榛《四溟诗话》中论诗:“李靖曰:‘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譬诸诗:发言平易而循乎绳墨,法之正也;发言隽伟而不拘乎绳墨,法之奇也;平易而不执泥,隽伟而不险怪,此奇正参伍之法也。白乐天正而不奇;李长吉奇而不正;奇正参伍,李杜是也。”[6]此论直接承继了刘勰的“奇正华实”说,并以李杜的诗来注释“奇正参伍”,很值得注意。
推开一步来看,刘勰在《辨骚》篇中虽只就奇与正、华与实之间关系的控制提出了看法,但其理论意义是揭示了艺术的一条普遍规律——为保持艺术张力的艺术控制规律。在艺术创作中,分寸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任何艺术形象都有它的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诗意的逻辑。作家、艺术家心中的艺术形象的个性和规律一旦形成,那么,作家、艺术家就必须按其本身的个性和逻辑去把握它、理解它、描绘它,任何随意性,或者用古人的话来说,“过”与“不及”,都可能是艺术的灾难。所以,艺术的控制就成为一条不可忽视的规律。艺术控制的基本原则就是刘勰所讲的“执正以驭奇”的“驭”,用今天的话来说,作家、艺术家在抒情言志和叙述描写时,都必须有清醒的理智和强大的意志,时刻注意调整自己笔下的行为,严格按艺术形象的逻辑和个性行事,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一切都要做到恰到好处。这样作家、艺术家就不能不抑制、牺牲一些东西,以保护、促进一些东西,这就是控制。一切正常思维的人的行为都需要控制,文学艺术作为人的一种活动也需要控制。由于文学艺术具有情感性和微妙性等特征,其控制也就更多表现在情感的控制和细节的控制上面。
(1)情感控制。创作过程中作家、艺术家的感情,往往如春江涌动、骏马奔驰,势不可遏,特别是表现巨大的喜悦和巨大的悲痛时,作家、艺术家往往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感情失控,其最坏的效果就是把艺术感情还原为现实感情,完全失去审美性。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明代演员商小玲饰演《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时,在舞台上伤心而死。(“寻梦”一折,“偶然间心似缱,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实际上作家、艺术家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悖论:表现感情时作家、艺术家的感情越激动,越能真实地表现所要表现的感情;但作家的感情越激动又越可能使所要表现的感情失控。一定要处理好这个悖论,所要表现的感情才能恰如其分。所以戏剧界有的人评价周信芳的舞台艺术时指出,创作要“高度的激情,高度的放纵,高度的控制”[7]这是讲得很有道理的,没有激情就进入不了角色,没有放纵精神就不能放松,创作不能进入自由境界,但是没有控制就不能准确地把握角色的性格。必须把激情、放纵和控制结合起来,创作才能获得成功。古罗马时期学者朗吉弩斯说:“那些巨大的激烈情感,如果没有理智的控制而任其自己盲目、轻率的冲动所操纵,那就会像一只没有压仓石而飘流不定的船那样,陷入危险。它们每每需要鞭子,也需要缰绳。”[8]这里所说的以理控情的观点,与刘勰的观点十分相似。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狄德罗也说过:“凭感情去表演的演员总是好坏无常。你不能指望从他们的表演里看到什么一致性;他们的表演忽强忽弱,忽冷忽热,忽而平庸,忽而卓越,今天演得好的地方明天再演就会失败,昨天失败的地方今天再演却又成功。但是另一种演员却不如此,他表演时凭思索,凭对人性的钻研,凭经常模仿一种理想的范本,凭想象和记忆。他总是始终如一,每次表演用同一种方式,都同样完美。”[9]艺术控制与艺术的完美是密切相关的,其中要有充分的感情,也要有深刻的思考,狄德罗的这个观点也十分精彩。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悲剧诗人并不是他的情绪的奴隶而是主人,并且他能把这种对情绪的控制传达给观众们。”[10]艺术感情不是作家的自然感情,而是经过创作主体控制过的感情,控制也就是掌握、支配、调整的意思,自然的感情经过创作主体的掌握、支配和调整才有可能转化为艺术的感情,也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感人的艺术世界。
(2)细节控制。这对艺术来说是重要的。艺术的成功或失败往往在很小的细节上反映出来。稍稍差一点,就可能失败;而稍稍改进一点,就可能获得成功。列夫·托尔斯泰曾说:“……所有一切艺术都是这样:只要稍微明亮一点,稍微暗淡一点,稍微高一点,低一点,偏右一点,偏左一点(在绘画中);只要稍微减弱一点和加强一点,或者稍微提前一点,稍微延迟一点(在戏剧艺术中);只要稍微说的不够一点,稍微说得过分一点,稍微夸大一点(在诗中),那就没有感染力了。只有当艺术家找到无限小的因素时,他才可能感染别人,而且感染的程度也要看在何种程度上找到这些因素而定。”[11]列夫·托尔斯泰的话,道出了艺术控制的基本原则。
刘勰在《辨骚》篇中,在总结历代创作的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坠其实”的看法,实际上是提出了文学活动的“奇正华实”说。“奇正华实”说的主要思想是,文学要在继承前人的艺术经验的条件下求新变,但这新变又不可变成失去分寸的放纵,应注意艺术控制。创作主体应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在奇与正之间,在华与实之间,去追求具有艺术张力的折衷点,使创作从“无序”走向“有序”,以取得预期的艺术效果。“奇正华实”说可以理解为抒情言志中的艺术控制论。但把“奇正华实”说的艺术控制思想推广开来,则可以包括到文学活动的一切方面。如创作动机中功利动机与非功利动机的控制,创作过程心理状态的热与冷、松与紧的控制,艺术描写中繁略、隐显、粗细、文雅等关系的控制,艺术欣赏中入与出的控制,艺术思维中感性与理性的控制,艺术发展中通与变的控制,等等。
(1994年草, 1998年9月改)
[1]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见《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99页。
[2]《十一家注孙子校理》,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6页。
[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7页。
[4]《十一家注孙子校理》,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9~90页。
[5]《诗式校注》,李壮鹰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6]谢榛:《四溟诗话》,见《四溟诗话·姜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52~53页。
[7]秦牧:《艺海拾贝》,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172页。
[8]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
[9]狄德罗:《演员奇谈》,见《狄德罗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1~282页。
[10]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11]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