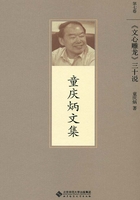
二、“原道”说与“异质同构”说比较
鲁迅说刘勰的“原道”,“其说汗漫,不可审理”,蒋祖怡、韩泉欣的文章批评刘勰“原道”理论把“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和自然现象混同起来论述”,祖先生著作中三次批评刘勰把“天文”与“人文”“混为一谈”,都表达了一个同样的意思:即自然是自然,文学是文学,两者不容混淆,因为自然是客观存在而属于物;而文学、文章则是主观意识而属于心,两者是不同质的,这中间又不讲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则刘勰似乎就直接地把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等同起来,这不是“汗漫”、不是“混同”、不是“混为一谈”吗?本文的主旨就是要在厘清刘勰的“原道”说并不是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尝试着来解释刘勰所理解的物与心之间的沟通问题或冥合问题。
无论中外,古人对外物的朴素理解,均是通过人的视、听、嗅、触、摸,以及由物而感所得出的感觉、知觉、情感反应等,来了解外在事物的。在这些心理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有了模仿、复写、影印、认知等人对物的掌握;到了现代有了哲学“反映”论,以及心理学的“移情”论和“直觉”论,心与物的沟通才得到现代科学理论的解释。但是,解释心与物的沟通是不是就只有“反映”论、“移情”论和“直觉”论呢?特别是对于刘勰的“原道”说中“物”与“心”与“文”是如何“过渡”的,我们应该怎样判断其特征呢?能不能找到新的理论来解释呢?
刘勰的“原道”说中的“道”就是他心目中的“自然”,他认为自然美丽无比,说“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踰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刘勰这段描写,充分地展现了自然之美。问题是这自然之美如何会变为文章和文学之美呢?自然是客观的,文章、文学是主观的,鲁迅批评其“汗漫,不可审理”,祖先生则质疑:“怎么能把这不同质的东西混为一谈呢?”[7]十几年前,拙作《〈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用“衍化”一词来解释,意思是自然通过人的心与言衍化为人文。现在看来,这“衍化”一词似乎也还欠清晰,“衍化”什么,怎么“衍化”,没有把道理完全说清楚。所以我认为鲁迅质疑的“汗漫,不可审理”,祖先生质疑的“怎么能把这不同质的东西混为一谈呢”是不能回避的,必须给出一个理论的解释。
在我有限的知识中,我初步觉得阿恩海姆提出的“异质同构”说似乎可以用来解释刘勰的“原道”说。鲁道夫·阿恩海姆,哈佛大学教授,著名艺术心理学家。在他出版的《艺术与视知觉》一书中,讨论“表现”问题时,提出和论证了“异质同构”理论。什么是“表现”?“表现”一词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广义的“表现”就是指“传递”,如“某某人表达了他的见解”,这种意义上的“表现”无边无际,不是阿恩海姆所用的,他所用的“表现”是狭义的,主要是指“透过某人的外貌和行为中的某些特征把握到这个人的情感、思想和动机,”[8]或者是透过某物的特征把握到人的情感、思想与动机。总的来说,表现就是通过外在的东西去把握人的内在的情感和思想。那么如何通过外在的事物的特征去把握人的内在的情感和思想呢?阿恩海姆作为格式塔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出了“异质同构”的理论。
根据阿恩海姆的评述,最初发现“异质同构”理论幼芽的,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詹姆斯,他在他的著名的《心理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身与心是否同一的问题。詹姆斯这样说:“必须指出,为这些作者们所极力强调的(外在)活动与情感之间的不等同,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绝对。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能从时间的连续中看到心理事实与物理现实之间的同一性,就是在它们的某些属性当中,比如它们的强度和响度、简单性和复杂性、流畅性和阻塞性、安静性和骚乱性中,同样也能看到它们之间的同一性。”[9]按照詹姆斯的理解,人的身体和人的心理是不同质的,前者是物质性的,后者是非物质性的,但它们之间的结构在性质上是可以等同的,这就是最早的“异质同构”理论。这种理论经过诸多格式塔心理学家如韦特海默、柯勒、卡夫卡等人的发展和验证,最终由阿恩海姆正式提出了“异质同构”理论。他的理论与詹姆斯的不同之点在于,他认为一切事物(包括自然事物)总会有一种特征,这种特征透露出一种“力的结构”,这种“力的结构”常常表现为“上升和下降、统治和服从、软弱与坚强、和谐与混乱、前进与退让等基调,实际上乃是一切存在物的基本形式。不论是在我们心灵中,还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不论是在人类社会中,还是在自然现象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些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那推动我们自己的情感活动起来的力,与那些作用于整个宇宙的普遍的力,实际上是同一种力。只有这样去看问题,我们才能意识到自身在整个宇宙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这个整体的内在统一”。阿恩海姆的“异质同构”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指出了人的心理事实与物理事实实际上具有某种同样的表现性,这就给文学艺术的创作和评论,提供了一条新的解释思路。例如,我们常常会用垂柳表达一种悲哀的情感,用屋柱压顶来表达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这应作何解释呢?阿恩海姆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一棵垂柳之所以看上去是悲哀的,并不是因为它看上去像是一个悲哀的人,而是因为垂柳枝条的形状、方向和柔软性本身传递了一种被动下垂的表现性;那种将垂柳的结构与一个悲哀的人的悲哀心理结构所进行的比较,却是在知觉到垂柳的表现性之后才进行的事情。一根神庙中的立柱,之所以看上去挺拔向上,似乎是承担着屋顶的压力,并不在于观看者设身处地地站在了立柱的位置上,而是因为那精心设计出来的立柱的位置、比例和形状中已经包含了这种表现性。”[10]这意思是说,作为植物的垂柳与人的情感的悲哀是不同质的,屋下的立柱与人所承受的压力也是不同质的,但垂柳的力的结构和人的悲哀心理的力的结构是同一的,屋顶下立柱经艺术家精心设计所透露的力的结构,与人承受压力时的力的结构是同一的,因此观看者会引起“共鸣”。更进一步的意思是,自然与人在宇宙中同处于一个整体的内在统一中,宇宙具有普遍的力,人的表现也是一种“力”,某物及形状与人的某种情感的表现倾向,在“力”的结构上可以是一致的,虽然这种“力”的结构已经是一种非心非物、亦心亦物的东西。
这种理论看起来有点神秘,实际上并不神秘。阿恩海姆指出:“表现性在人的知觉活动中所占的优势地位,在成年人当中已有所下降,这也许是过多科学教育的结果,但在儿童和原始人当中,却一直稳固地保留着。按照维尔纳(心理学家)和柯勒(心理学家)收集的资料,儿童和原始人在描述一座山岭时,往往把它说成是温和可亲的或狰狞可怕的;即使在描述一条搭在椅背上的毛巾时,也把它说成是苦恼的、悲哀的或劳累不堪的等等。”[11]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因为我们童年时期就会对周围的事物作出类似的解释。我们周围的玩具,是客观物体,是不具有思想的,但因为幼小的心灵,分不清意识与物体的关系,幼小心灵的思想还没有发展到意识产生于物体的反映论阶段,我们幼小的心灵把自己的心与客观的物“混为一谈”了,他(她)拿着一个娃娃没完没了地说话,他(她)画了一竖并不笔直的黑色的线条,以为这是他(她)竖立起来的真的柱子……这本身是一个事实,我们不能批评儿童唯心主义。
阿恩海姆进一步把这种“异质同构”理论,在解释艺术的表现性的分析中,他说:“一个艺术品的实体就是它的视觉外观形式。按照这样一个标准衡量,不仅我们心目中那些有意识的有机体具有表现性,就是那些不具意识的事物——一块陡峭的岩石、一棵垂柳、落日的余晖、墙上的裂缝、飘零的落叶、一汪清泉、甚至一条抽象的线条、一片孤立的色彩或是在银幕上起舞的抽象形状——都和人体一样,都具有表现性,在艺术家眼里,这些事物的表现价值有时候甚至超过人体。”[12]这样,阿恩海姆就把他的“异质同构”理论运用于对艺术品表现性的考察中。他的这种考察会引起我们的许多“共鸣”,在中国古典的诗词中,春风,野草,月亮,江河、山岭、各种山水花鸟等不具意识的事物,常常是诗人笔下表达情感不可缺少之景物。我想这一点大家都理解,是无须多说的。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作者似乎只写“物”和物的变动,人们就能领会作者要表现什么情感与思想了。如《论语》中记载孔子的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只写流水和上天,但我们感到的就不仅仅是流水和上天了,我们似乎在自然中领会到人的生命的脉动。徐复观在谈到刘勰的《诠赋》中“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时说:“主观的情性,与客观的自然,是不知其然而然地冥合无间的。《神思》篇把这种情形称为‘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真是言简而意赅了。”[13]看来,“异质同构”理论同样也适合于中国古代文章、文学表现性的解释。
在大体介绍了阿恩海姆的“异质同构”理论后,让我们回到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的论点,尝试进行一些比较。的确,刘勰清楚地区别了自然与人,他所说的“无识之物”与“有心之器”,就把自然与人区隔开来,这里不存在混淆;但是对于“天文”、“地文”如何衍化为“人文”,作者用“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来解释,有人认为这并没有说清楚,自然之物如何在人的知觉活动中变成情感之文,从而引起鲁迅的“汗漫”和祖保泉的“混为一谈”的质疑,但是如果我们用阿恩海姆的“异质同构”说来解释,其疑问也就自然解开了。
刘勰《原道》开篇在说了天地、日月、山川的美丽之后,指出“此盖道之文”后,接着说:“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这里的“观”,是观看天地的光辉;这里的“察”,是察看地面万物的文采,这都是人的知觉活动,所以刘勰接着说“惟人参之”。这里就把天、地、人并举,并指称其为“三才”。地、天是指物质性的宇宙,人则是具有心智的高等动物,这是不同“质”的,但刘勰把它们归为一类,即“三才”,都具有文采,这就是地、天与人“异质”而“同构”,即天地的“力的结构”与人的“力的结构”是同一的。所以这里所说的“道之文”,不仅仅是指自然天地的“文”,也指人的“文”。看来,我们理解刘勰的“原道”的“道”时,不应把它看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物,它已经在人的知觉活动中,被改造为非心非物、亦心亦物的事物了。如果用阿恩海姆的理论看,这就意识到人自身在整个宇宙中的地位,人与宇宙的不可分离,以及人与整个宇宙的内在统一性。更具体地说,自然景物属于自然界,人的情感与思想属于意识界,春天和花朵是自然物体,人的快乐和喜悦是情感意识,“异质同构”理论并不认为这种区分在谈论表现性时是合理的,而恰恰是不合理的,它主张在谈论表现性时应采用“林奈分类法”。林奈是瑞典博物学家,他对植物的分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按照科学分类植物时,有一种主张,认为人类的眼睛能够自动地创造出一种适合于所有存在物进行分类的新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打破了按照科学分类法建立起来的顺序和秩序,从而把“极不相同的事物”归并为同一类。[14]“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宋·叶绍翁),这句诗表现了春天的勃勃生机,从表现性看,就把本来属于植物一类的春天的园林、花草与人(那位访客)的喜悦和欢欣的情感归并为一类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我们顺着刘勰的《原道》篇往下读,这就是上面我们已经引过的那段“旁及万品,动植皆文”的文字,作者写“龙凤”(动物)“呈瑞”(情感),“虎豹”(动物)“凝姿”(情感),“云霞”(自然物)“雕色”(人的加工),“草木”(植物)“贲华”(人加工后的情感),在这里前者都是客观自然,后者都是人主观的情感,可前后两者合一,这就是阿恩海姆所说的“异质”而“同构”。接着刘勰自己反问:“夫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在前面的描述中了。刘勰当年自然不可能提出什么“异质同构”的话语,但其思想今天被阿恩海姆的理论“照亮”了。所以,我们今天理解刘勰的《原道》,自然也可以用阿恩海姆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充分说明了作为自然的“道”,不是孤立的,它是外在的东西,但人的心理活动,通过“异质同构”的道理,可以把外在的自然,衍化为内在的人的情感,不同质却可以同构,天文、地文就这样变成了人文。这就回应了鲁迅“汗漫”和祖保泉“混为一谈”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