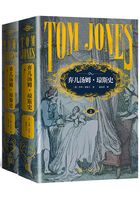
第八章
白蕊姞小姐和玳波萝阿姨的谈话,比前一章可乐者多,而有教育意义者少。
奥维资先生带着珍妮退到他的书房里去的时候,像刚才说的那样,白蕊姞小姐就带着那位精明强干的管家婆,来到前面说过的那个书房的紧隔壁,在那儿,借着一个钥匙孔的传送作用,她们把奥维资先生对珍妮发的那一番训诫之言,还有珍妮回答的话,以及,一点儿不错,前一章里所说的一切其他细情,全部醍醐灌顶,吸入双耳。
她哥哥书房门上这个钥匙孔儿,白蕊姞小姐那样深深知晓,常常利用,所以一点儿不错,就和古代细丝比对那堵著名垣墙上的孔穴 一样。这个钥匙孔儿可做许多有利的用途。因为,通过这个钥匙孔儿,白蕊姞小姐不必麻麻烦烦地有劳她哥哥重加叙说,就常常能够知道她哥哥的心意所在。固然不错,这种传送消息的办法,也有一些小小的不便,所以她有的时候,像莎士比亚里的细丝比那样,大声喊着说,“噢,可恶、可恶的垣墙啊!”
一样。这个钥匙孔儿可做许多有利的用途。因为,通过这个钥匙孔儿,白蕊姞小姐不必麻麻烦烦地有劳她哥哥重加叙说,就常常能够知道她哥哥的心意所在。固然不错,这种传送消息的办法,也有一些小小的不便,所以她有的时候,像莎士比亚里的细丝比那样,大声喊着说,“噢,可恶、可恶的垣墙啊!” 是不无其理由的。因为,奥维资先生既是治安法官,那他在侦查有关私生子一类案件的时候,就要出现一些情况,让一个处女——特别是年近四十的处女,像白蕊姞小姐——那种受不了脏话的耳朵听来,是容易感到不快的。不过,遇到这类情况,她可以开方便之门,把她脸红的情态对男子掩盖起来,而De apparentibus,et non existentibus eadem est ratio
是不无其理由的。因为,奥维资先生既是治安法官,那他在侦查有关私生子一类案件的时候,就要出现一些情况,让一个处女——特别是年近四十的处女,像白蕊姞小姐——那种受不了脏话的耳朵听来,是容易感到不快的。不过,遇到这类情况,她可以开方便之门,把她脸红的情态对男子掩盖起来,而De apparentibus,et non existentibus eadem est ratio ——用英语说,就是,一个女人脸红而无人见,那她就是绝未脸红。
——用英语说,就是,一个女人脸红而无人见,那她就是绝未脸红。
这两位贤良的女人,在奥维资先生和珍妮两个对话的全部过程中,都绝对保持静默;但是,对话刚一结束,那位绅士刚去听不见她们的地方,玳波萝阿姨就忍不住嚷嚷起来,说她主人太宽大了,特别是他不应该叫珍妮给那孩子的爸爸打掩护。她赌咒发誓地说,她要在太阳落山以前,把这人从她嘴里追问出来。
白蕊姞小姐听了这番话,微笑起来,只笑得鼻歪眼斜,(这是白蕊姞小姐不常有的)。我决不要我的读者想象,说这是一种轻浮佻 的微笑,像荷马说到维纳斯叫她是“爱笑女神”
的微笑,像荷马说到维纳斯叫她是“爱笑女神” 的时候,想要叫你想象的那样;那种笑法儿,也不是莎萝斐娜夫人
的时候,想要叫你想象的那样;那种笑法儿,也不是莎萝斐娜夫人 从舞台包厢
从舞台包厢 所发出使维纳斯诚愿舍弃她长生不老的天神资格以与之相匹的微笑。不是,都不是。那种微笑,未免太可以认为是从威仪俨然那位提西否妮
所发出使维纳斯诚愿舍弃她长生不老的天神资格以与之相匹的微笑。不是,都不是。那种微笑,未免太可以认为是从威仪俨然那位提西否妮 的酒窝儿所表现的媚态,或者她的姊妹之一的媚态。
的酒窝儿所表现的媚态,或者她的姊妹之一的媚态。
于是白蕊姞小姐就用这种微笑,还有像令人如身穿棉衣的十一月晚间那种飕飕北风 一样的悦耳之音,轻轻地责备玳波萝阿姨,说玳波萝阿姨好奇。这种坏毛病好像玳波萝阿姨沾染太甚,而白蕊姞深恶痛绝,所要厉声狠骂的;她末了添了一句说,“尽管她自己有许多毛病,但是她得感谢上帝,即便她的敌人,都不能给她加一个‘包打听’的罪名。”
一样的悦耳之音,轻轻地责备玳波萝阿姨,说玳波萝阿姨好奇。这种坏毛病好像玳波萝阿姨沾染太甚,而白蕊姞深恶痛绝,所要厉声狠骂的;她末了添了一句说,“尽管她自己有许多毛病,但是她得感谢上帝,即便她的敌人,都不能给她加一个‘包打听’的罪名。”
于是她接着夸珍妮在这件事里的所作所为,很够体面,很有胆量。她说,她不能不和她哥哥同意,认为她作的坦白那样诚实恳切,对她的情人那样忠诚正直,这都不能不说是她的可取之处;她老认为珍妮是个好孩子,她觉得没有疑问,珍妮一定是受了流氓的勾引才上了当、吃了亏;这个流氓,比她不止百倍地更加应该受到惩罚。十有八九,他还用和她结婚那类谎话或者别的欺诈手段,才把她的心说活了吧。
玳波萝阿姨一听白蕊姞小姐原来持这样的态度,不免大吃一惊。因为这位教养有素的女人,在她的主人或者主人的令妹面前,不听到他们的心意所在,向来就几乎永不开口,她的思想感情,就没有不和他们的心意东呼西应的时候。但是这回,她却一反常态,认为她抢先发动一下,可保无虞。不过,能洞察、有明鉴的读者,也许不会因为她这样,就给她安上一个没有足够先见之明的罪状,而未免要大大地欣赏她一番;因为她一看到风头不对,马上就见风使舵,掉转方向,那个快当麻利劲儿,真值得称赏。
“不错,小姐,”这位天生伶俐的妇人、真正伟大的政客说,“我一定得承认,我和小姐您一样,不能不佩服这个女孩子的胆量。再说,像小姐您说的,她要是受到了坏人的欺骗,那这个可怜的人,应该受到怜悯。再说,像小姐您说的,这孩子永远像个好心眼儿、不撒谎、不沾习气的孩子,不像这一带那些轻薄放荡的贱货那样,觉得自己的脸子值得显摆。”
“你说的不错,玳波萝,”白蕊姞小姐说,“要是这个女孩子也跟那些好显摆的贱货一样(咱们区上这样的人还真不少),那我一定要埋怨我哥哥,说他对这孩子太宽大了。前几天我看见,有两个庄稼人的闺女,在教堂里袒胸露臂,我得正颜厉色地说,她们叫我大吃一惊。要是这些丫头片子都这样搔首弄姿、献媚卖俏,那她们受了大罪,就得说她们活该。我恨透了这些丫头片子啦,我恨不得她们脸上都长了麻子,弄得坑坑洼洼的才好。但是我可得坦白地说,我从来没见过可怜的珍妮举动那样轻薄过。我敢保,一定是成心骗人的坏蛋欺骗了她,叫她上了当;不价,也许还强逼她,叫她吃了亏哪。我对这个可怜的孩子,满怀怜悯。”
玳波萝阿姨对这些思想感情,一概嘉奖。她们把丽容美貌通通臭骂了一顿,对于所有那些为人老实、无甚姿色的女孩子,叫好使坏招儿的骗子用手段欺骗了的,尽量表示了一番同情的怜悯。就这样结束了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