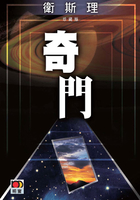
第3章 價值連城的紅寶石
有的時候,人生的際遇是很難料的,一件全然不足為奇的事,發展下去,可以變成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像“奇門”這件事就是。
在這幾個月中,新的奇事一直困擾着我,那實在是一件神秘之極的事,所以使我非將之先寫出來不可,這件事,就是現在起所記述的“奇門”。
必須要解釋的是:“奇門”兩字,和中國的“奇門遁甲”無關,它的意思,就是一扇奇怪的門而已,當然,一切奇怪的事,也都和一扇奇怪的門略有關聯。
閒言少說,言歸正傳。
整件事,是從一輛華貴的大房車開始的,不,不應該說是從那輛房車開始,而應該說,從那隻突然從街角處竄出來的那隻癩皮狗開始。
事情開始的時候,我正駕着車子,準備去探望一個朋友,那朋友是集郵狂,他說他新近找到了一張中國早期郵票中的北京老版二元宮門倒印票,非逼我去欣賞不可,我對集郵也很有興趣,自然答應了他。
但是,當我離家只不過十分鐘,車子正在疾馳中的時候,一隻癩皮狗突然自對面竄了過來,如果我不讓牠,那牠一定要被車子撞得腦漿迸裂了。
我對駕駛術十分有研究,要在那樣的情形下避開這樣的一條冒失癩皮狗,本來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當我的車頭一側,恰好避過了那頭癩皮狗時,橫街上的一輛灰白色的大房車,突然衝了出來。
我連忙煞車,可是已經遲了。
那結果是可想而知的,“蓬”地一聲響,兩車相撞,我的車子已然停了下來,但是那輛大得霸道的房車卻還未曾煞住,它向前直衝而出,撞在對街的一隻郵筒之上,將那隻郵筒,撞成了兩截。
我連忙跳下車,趕過了馬路,在大城市中,一有了什麼意外,看熱鬧的人,便會從四面八方湧了過來,當我奔到了那輛房車旁邊的時候,已經有十多個人聚集在車子的旁邊,我向其中一個看來十分斯文的人一指,道:“別看熱鬧,快去報警!”
那人呆了一呆,但立時轉身走了開去,我又推開了兩個好奇地向車中張望的人,打開車門,在司機位上坐着的,是一個穿著得十分華麗的中年婦人。
那時候,她已經昏迷了過去,額角上還有血流出,車頭玻璃裂而未碎,看來她的傷勢,也不會太重,幾分鐘之後,救傷車和警車也全都趕到了現場。
各位如果以為這件事以後的發展,和那個駕車婦人,或是那輛車子有什麼關聯的話,那就料錯了,我一開頭已寫明白,事情只不過從那輛大房車開始而已!
警車來了之後,我是應該到警局去一次的,我可能在警局耽擱不少時間,所以我先要打一個電話去通知我那位集郵狂的朋友,我和一位警官打了一個招呼,便向最近的一家雜貨舖走去,去借電話。
我還未曾走到雜貨舖,有兩三個頑童,在我的身邊奔了過去,其中一個且撞了我一下!
當那個頑童一下子撞到我身上的時候,我唯恐他跌倒,所以伸手將他扶住,可是那頑童卻將他手中的一封信,迅速地拋在我的腳下,用力一掙,逃走了!
我呆了一呆,彎身從地下拾起那封信來,那封信的信封是很厚的牛皮紙,一看便知道那是用厚牛皮紙來自製而成的,而且,整封信都相當沉重,我伸手捏了一捏,信封中好像不止是信,而且還有一些堅硬的物事。
那些堅硬的物事,看來像是一柄鑰匙。
我在才一看到那封信的時候,還不知道為什麼那頑童一被我扶住,就要將信拋掉,但是當我向信封上一看之際,我便明白了那頑童為什麼驚惶失措了。
剛才,那輛大房車在打橫直衝過馬路時,一撞在那郵筒上,將郵筒撞成了兩截,有不少信散落在地上,看熱鬧的頑童便將之拾了起來。而他們拾信的目的,也非常明顯,因為那封信上的郵票已被撕去了!
信還在郵筒之中,信封上的郵票,自然是還未蓋過印的,雖然是小數目,但在頑童的心目中,已是意外之喜了。
我當時拿了這封信在手,第一個反應,自然是想立即將之送回郵筒去,可是我卻立即改變了主意,因為那頑童撕郵票的時候,十分匆忙,所以,在將郵票撕下的時候,將信封上的牛皮紙,撕去了一層,恰好將收信人的地址,撕去了一大半。
信封上全是英文寫的,在還可以看得到的字迹上,顯示出信封是寄到一個叫作“畢列支”的地方,那地方是在地球上的哪一角落,我無法知道,因為紙已被撕去了一層。
而收信人的名字還在,那是“尊埃牧師”,而且,發信人的地址,也十分清楚,那就是離此不遠處,我一抬頭,就可以看到那條街的。在發現了那些之後,我改變了主意,將那封信,放進了我的袋中。
我當然不是準備吞沒那封信,而是因為那封信,已無法按址寄達。而那封信之所以不能寄達目的地,是由於頑童撕去了郵票時弄壞了信封,頑童之所以能得到這封信,卻是因為那輛大房車撞壞了郵筒,而大房車又是在和我相撞了之後,才撞向郵筒的,所以追根究源,全是我的關係。
我心中已打定了主意,等我在警局的手續完畢了之後,我便去訪問那位發信人,請他在信封上加上地址,那麼我就可以將信貼上郵票,再去投寄了。
我在雜貨舖中打好了電話,又駕着自己的車,和警車一齊同到了警局,在警局中,我已知道那個婦人只不過受了一點輕傷,已經出院回家了。
我在警局也沒有耽擱了多久,便已辦完了手續,我走出了警局,我的車子只不過車頭上癟進了一塊,並沒有損壞,所以,我很快就來到了那封信的發信人地址。
那是一幢十分普通的房子,坐落在一條相當幽靜的街道上,我上了三樓,按了門鈴,門打開了一道縫,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問道:“找誰啊?”
我看了那封信,才道:“我找米倫太太,她是住在這裏的,是麼?”
我自然根本不認識那個米倫太太,只不過因為那信封上寫着,發信人是“圖書路十七號三樓”的米倫太太而已。
那小姑娘一聽,立時瞪大了眼,用一種十分奇怪的神色望着我,道:“你找米倫太太?你怎麼認識她的?從來也沒有人找她的,你是中國人,是不是?”
她向我問了一連串的問題,直到她問到了我是不是中國人之際,我才發現那小姑娘雖然也是黑頭髮,黑眼睛,但是她卻並不是中國人,她可能是墨西哥人或西班牙人。
那小姑娘望着我時的那種訝異的神情,看來十分有趣,我點頭道:“是的,我是中國人,米倫太太是什麼地方人,西班牙還是墨西哥?”
那小姑娘道:“墨西哥,我們全是墨西哥人,你是米倫太太的朋友?我們從來也未曾聽說她有過中國朋友!”
我無法猜知那小姑娘和這位米倫太太的關係,而那小姑娘又像是不肯開門給我,所以我不得不道:“我可以見一見她麼?”
“見一見她?”小姑娘立時尖聲叫嚷了出來,同時,臉上更現出一種難以形容的神色來,像是我所說的,根本是不可能實現的事一樣,但是我所說的,卻是最普通的事,我只不過想見一見米倫太太而已。
或許,這位米倫太太,是一位孤獨的老太婆,或者,她是一個很怪的怪人,因為那小朋友說她是從來也沒有朋友的,但是,聽了我的話之後,反應如此之強烈,這卻多少也使我感到一點意外,不知是為了什麼。
我重複道:“是的,我想見一見她,為了一件小事。”
“可是,”那小姑娘的聲音,仍然很尖,“可是她已經死了啊!”
“死了?”我也陡地吃了一驚,這實在是我再也想不到的一件事,我本來立時想說“那不可能”的,但是,那小姑娘的神情,卻又絕沒有一點和我開玩笑之意。
“是啊,半年前已經死了。”那小姑娘補充着說。
我更加懷疑了,我道:“這不可能吧,我知道她寄過一封信,是寄給尊埃牧師的,那封信,只怕是今早投寄的,她怎可能在半年之前,已經死去?”
那小姑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這封信……是我寄的。”
我更加莫名其妙了,道:“可是,那封信卻註明發信人是米倫太太的,小妹妹,你可有弄錯麼?”
小姑娘總算將門打了開來,一面讓我走進去,一面道:“你是郵政局的人員麼?事情是這樣的,米倫太太——”
她的話還未曾講完,便聽得廚房中傳來了一個十分粗暴的女人聲音,問道:“姬娜,你和什麼人在講話?”
“媽媽!”小姑娘忙叫着,“一位先生,他是來找米倫太太的!”
那小姑娘有一個十分美麗的名字,我向廚房望去,只見一個身形十分高大的婦人,從廚房中走了出來。
我連忙準備向那婦人行禮,可是當我向那婦人一看間,我不禁大吃了一驚!
我從來也沒有看到過如此難看的女人。姬娜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小姑娘,而她竟叫那麼難看的女人為“媽媽”,這實在是令人難以想像的一件怪事!
雖然明知道這樣瞪住了人家看,是十分不禮貌的事,但是我的眼光仍然停留在那婦人的臉上,達半分鐘之久。
我絕不是有心對那婦人無禮,而是那婦人的樣子實在太可怕了,是以我在一望到了她之後,我的眼光竟然無法自她的臉上移開去,好在這時是白天,如果是黑夜的話,我一定會忍不住高聲呼叫起來的。
而且,必須明白的是,我卻不是一個膽子小的人!
我不但膽子不小,而且,足迹遍天下,見過各種各樣,奇形怪狀的事,可是就未曾見過一個那麼可怖的婦人,她頭部的形狀,好像是用斧頭隨意在樹上砍下來的一段硬木,她一隻眼睛可怕地外突着,而另一隻眼睛,則顯然是瞎的,眼皮上有許多紅色的瘰癧。
她的鼻子是挺大的,再加上她厚而外翻的上唇,就這兩部分來看,她倒像是一頭狒狒——雖然她的眼睛,比狒狒還要可怕得多,她的牙齒參差不齊。
她這時,正用圍裙在抹着濕手,而且,我還看到,在她的臉上和手上,有着許多傷痕,像是刀傷。
當我從震驚中定過神來之際,我看到那婦人可怕的臉上,已有了怒意(那是加倍的可怕)!
她那一隻幾乎突出在眼眶之外的眼睛瞪着我,啞聲道:“你是誰?你來和我的女兒說些什麼事情?”
那小姑娘——姬娜則叫道:“媽媽,這位先生是來找米倫太太的,他提及那封信,媽,你還記得麼?就是米倫太太臨死前叫我們交的信,但是我們卻忘記了,一直放了半年,到今早才找出來。”
我多少有點明白事情的真相了,米倫太太,可能是和姬娜母女一齊居住的一位老太太。而這位老太太在臨死之前,曾托她們交一封信,而她們卻忘記了,一直耽擱了半年之久,直到今天早上才找出。
而當這封信還在郵筒之中,尚未被郵差取走之時,那輛大房車便將郵筒撞斷,這封信因為十分重,所以郵票也貼得多些,是以被頑童注意,將之偷走,而又將上面的郵票撕去,因之弄得地址不清。
而也因為這一連串的關係,我才按址來到了這裏,見到了可愛的姬娜,和她那位如此可怕的母親。
我想通了一切,剛想開口道及我的來意時,那婦人已經惡聲惡氣地道:“那封信有什麼不妥了!你是誰?”
我勉強在我的臉上擠出了一個微笑來,道:“有小小的不妥,夫人。”我又取出了那封信,道:“你看,信封上的地址被撕去了,如果你記得信是寄到什麼地方去的,那麼,就請你告訴我,謝謝你。”
我已經準備結束這件事了。
因為,那婦人將地址一講出來,我寫上,貼上郵票,再將之投入郵筒,那不就完了麼?
我心中在想,總不會巧成那樣,又有一個冒失鬼,再將郵筒撞斷的!
那婦人笑了起來,她的笑聲,其實十足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嚨時所發出來的喘息聲,她道:“信是寄到什麼地方去的?米倫太太還有什麼寄信的地方?那當然是墨西哥了,你快走吧,別打擾我們了!”
她雖然下了逐客令,但是我還是不能不多留一會兒。
我又道:“那麼,請問是墨西哥什麼地方?因為信上的地址,全被撕去了,只有‘畢列支’一個字,那可能是什麼橋吧?”
那婦人瞪着她那隻突出的單眼,道:“墨西哥什麼地方?我不知道,姬娜你可知道麼?嗯?”
姬娜搖着頭,她那一頭可愛的黑髮,左右搖晃着,道:“我不知道,媽媽,我從來也沒有注意過。”
那婦人攤開了手,道:“你看,我們不知道,你走吧!”
在那一剎間,我也真的以為事情沒有希望了,而且,我已知道那封信是被積壓了半年之久的,就算有什麼急事,那也早已成為過去的事情了。所以,我已準備躬身退出。
可是,就在那婦人一攤手之間,我卻陡地呆了一呆。我在那一瞬間,看到那婦人的手上,戴着一隻鑲有紅得令人心頭震驚的紅寶石戒指!
那是極品的紅寶石(我對珠寶有着極度的愛好和相當深刻的研究),這種紅寶石的價格,遠在同樣體積大小的上等鑽石之上,那婦人戴這枚戒指的方式也十分特別,她不是將鑲有寶石的一面向外,而是將那一面向裏,所以,只有她攤開手來時,我才看得見。
這樣的一枚紅寶石戒指,和這樣的一個婦人,是無論如何不相稱的!
而我的震驚神態,也顯然立時引起了對方的注意,她連忙縮回手去,並且將手緊緊地握住,那樣,那塊極品紅寶石,就變成藏在她的掌心之中了。
我在那片刻間,心中生出了極度的疑惑來:這樣可怕的婦人是什麼人?何以她住在那樣普通的地方,又要親自操作家務,但是她卻戴着一隻那樣驚人的紅寶石戒指。這一隻戒指,照我的估計,價值是極駭人的。
而且,上好的紅寶石,世上數量極少,並不是有錢一定能買得到的東西。
一樣東西,到了有錢也買不到的時候,那麼它的價值自然更加驚人了!
我在那剎間,改變了我立即離開她們的主意。老實說,我突然改變主意,並不為了什麼,我只是好奇而已。
我原是一個好奇心十分強烈的人,我真想弄清楚那可怕的婦人的來歷和那枚紅寶石戒指的由來。
我故意不提起那枚戒指,我咳嗽了一聲,道:“你看,這封信中,好像還附有什麼東西,可能這是一封十分重要的信——”
那婦人突然打斷了我的話頭,道:“我們已經說過,不知道米倫太太要將信寄到什麼地方去的。”
我陪着笑,道:“那麼,米倫太太可有什麼遺物麼?”
那婦人立時張大了口,看她的樣子,分明是想一口回絕我了,但是小姑娘姬娜卻搶着道:“媽媽,米倫太太不是有一口箱子留下來麼?那隻紅色的大箱子。”
那婦人立時又道:“那不干這位先生的事,別多嘴!”
我仍然在我的臉上擠出笑容來,道:“夫人,你看,這封信是寄給尊埃牧師的,或許,在米倫太太的遺物之中,有着尊埃牧師的地址。她已死了,她死前想寄出這封信,你總不希望死者的願望不能實現吧?”
我知道,墨西哥人是十分迷信,而且相當尊敬死人的,這一點,和中國人倒是十分相似的。
果然,我最後的一句話生了效,那婦人遲疑了一下,道:“好,你不妨來看看,但你最好儘快離去,我的丈夫是一個醉鬼,當他看到屋中有一個陌生男人的話——”
我聽到這裏,實在忍不住笑,我要緊緊地咬住了唇,才不致於笑出聲來。一個男人有了這樣的一個妻子,而居然還要擔心的話,那麼他必然是醉鬼無疑了!
我低着頭,直到可以控制自己不再笑了,我才敢抬起頭來,跟着她,走進了一間房間,姬娜也跟了進來。那間房間十分小,房間中只有一張單人牀,在單人牀之旁的,則是一隻暗紅色的木頭箱子。
那箱子也不是很大,這時正被豎起來放着,當作牀頭几用。在箱子的上面,則放着一個神像。
那個神像好像是銅製的,年代一定已然十分久遠了,因為它泛着一種十分黝黯的青黑色。我第一眼看到它,便被它吸引住了,因為我竟無法認出那是什麼神來,這個神像有一張十分奇怪的臉,戴着一頂有角的頭盔,手中好像持着火炬,他的腳部十分大。
而那隻箱子上,則刻着十分精緻的圖案,刻工十分細膩,絕不可能出於現代的工匠之手!
這兩件東西,和那張單人牀,也是絕不相配稱的。
那婦人道:“這就是米倫太太的房間,和她在生之前一樣,這箱子就是她的。”
從那箱子,那神像,我忽然聯想到了那婦人手中,那枚非比尋常的紅寶石戒指。我的心中突然有了一個概念,那枚紅寶石戒指,一定也是米倫太太的!
我伸手拿起了那神像(那神像十分沉重,重得遠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放平了那隻箱子,箱子有一柄鎖鎖着。
同時,我順口道:“夫人,你也是墨西哥人,是不是?米倫太太只是一個人在這裏,她何以會一個人在這裏的?她的丈夫,是做什麼事情的?”
那婦人立時提高了警惕,道:“先生,你問那麼多,是為了什麼?”
我笑了一笑,沒有再問下去,並沒有費了多久,我就弄開了鎖,將那隻箱子打了開來。
令我大失所望的是,那箱子幾乎是空的,只有一疊織錦,和幾塊上面刻有浮雕、銀元大小般的銅片。
我並沒有完全抖開那疊織錦來,雖然它色彩繽紛,極其美麗,我只是用極快的手法,將五六片那樣的圓銅片,藏起了一片來。
我先將之握在掌心之中,然後站起身來,一伸手臂,將它滑進了我的衣袖之中。
就我的行為而言,我是偷了一件屬於米倫太太的東西!
我當然不致於淪為竊賊的,但這時,我卻無法控制我自己不那樣做。因為這裏的一切,實在太奇特了,奇特得使我下定決心,非要弄明它的來歷不可。
當我將那圓形的有浮雕的銅片,藏進我的衣袖之中的時候,我不知道那是什麽,我只是準備回去慢慢地研究,或者向我的幾位考古有癖、學識豐富的朋友去請教一下,我當時的心中只是想,那位米倫太太,一定是十分有來歷的人,絕不是普通人物。
我的“偷竊手法”,十分乾淨俐落,姬娜和那婦人並沒有發覺,我關上箱子,又將鎖扣上,道:“很抱歉,麻煩了你們許久,這封信我會另外再去想辦法的。”
我一面講,一面向門口走去,到了門口,我向那婦人道別,又拍了拍姬娜的頭,隨口問道:“那封信中好像還有一樣東西,你們知道那是什麼?”
我只是隨口問問的,也絕沒有真的要得到回答,可是姬娜卻立即道:“那是一柄鑰匙!一柄長着翅膀的鑰匙,米倫太太生平最喜愛的一件東西。”
我呆了一呆,道:“長着翅膀的鑰匙?什麼意思?”
“鑰匙上有兩個翅膀,是裝飾的,”姬娜解釋:“米倫太太有兩件東西最喜歡,一件是這柄鑰匙,另一件是她的一枚戒指,那戒指真美,她臨死之際送給了媽媽,媽媽答應她死時,也送給我。”
姬娜講到這裏,停了一停,然後又補充道:“我不想媽媽早死,但是我卻想早一點得到那戒指,它真美麗!”
姬娜不住地說那枚戒指真美麗,而我不必她說明,也可以知道她說的戒指,一定就是她媽媽戴在手中的那一枚。
我不再急於去開門,並轉過身來,道:“夫人,那枚戒指,的確很美麗,可以讓我細看一看麼?”
那婦人猶豫了一下,也許是因為我的態度,始終如此溫文有禮,所以她點了點頭,將那枚戒指自她的手指上取了下來,放在我的掌心。
我能夠細看那枚戒指了,姬娜也湊過頭來。唉,那實在是美麗得驚心動魄的東西,古今中外的人,如此熱愛寶石,絕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天然的寶石那種美麗,簡直可以令人面對着它們時,感到窒息!
這一點,絕不是任何人工的製品,所能夠比擬的。
天然的寶石,似乎有一種特殊的魔力,如今我眼前的那塊寶石,便是那樣,它只不過一公分平方,不會有超過三公厘厚,可是凝神望去,卻使你覺得不像是在望着一塊小小的紅色的寶石,而像是在望着半透明的,紅色的海洋,或是紅色的天空!
我望了半晌,才將之交還了那婦人,然後,我才道:“夫人,恕我冒昧問一句,你可知道這一枚戒指的確實價值麼?”
那婦人一面戴回戒指,一面道:“不知道啊,它很美麗,是不是?它很值錢麼?值多少?五百?嗯?”
我並沒有回答她的問題,我只是含糊說了一句,道:“也許。”
我並不是不想回答她的問題,而是我怕我的答案講出來,會使她不知所措,昏過去的,這樣的一塊上佳的紅寶石,拿到國際珠寶市場去,它的價格應該是在“三百”或“五百”之下,加上一個“萬”字!而且還是以世上最高的幣值來計算!
這枚戒指原來的主人是米倫太太,那麼,米倫太太難道也不知道這枚戒指的價值麼?想來是不可能的,而她將那枚戒指送了人,卻將那鑰匙寄回墨西哥去!
我的心中充滿了疑惑,當我告辭而出,來到了我車子旁邊的時候,我又抬頭向我剛才出來的地方,看了一眼,剛才那不到半小時的經歷,實在是我一生中最奇怪的一樁事了。
我心中不住地問自己,那米倫太太,究竟是什麼人呢?
我上了車子,坐了下來,竭力使我思緒靜一靜,我要到什麼地方去呢?我決定去找那幾位對於古物特別有興趣,也特別有研究的朋友。
我知道他們常在的一個地方,那是他們組成的一個俱樂部。這個俱樂部的會員,只有七個人,而要加入這個俱樂部之困難,還是你立定心機去發動一場政變,自任總統來得容易了,要成為這個俱樂部的會員,必須認出七個老會員拿出來的任何古董的來歷。
我曾申請加入這個俱樂部,我認出了一隻商鼎,一方楚鏡,一片殘舊的文件(十字軍東征時的遺物),和一隻銀製的,屬於瑪麗皇后的香水瓶。
但是我卻在一塊幽黑的爛木頭前碰壁了,後來,據那個取出這塊爛木頭的人說,這是成吉思汗的矛柄。我心中暗罵了一聲“見你的鬼”,我未能成為會員。
但是,我因為認出四件古董,那是很多年來未曾發生過的事情,是以蒙他們“恩准”,可以隨時前往他們的會所“行走”。這個“殊恩”,倒有點像清朝的時候,“欽賜御書房行走”的味道。
我一直將車子開到了這個俱樂部會所之外,那其實是他們七個會員中一位的物業,司閽人是認識我的,他由得我逕自走進去,一位僕人替我打開了客廳的門。
他們之中,只有五個人在。正在相互傳觀着一隻顏色黯淡的銅瓶。千萬別以為他們七個人全是食古不化的老古董,他們只不過是喜歡老古董罷了。
這時,手中不拿花瓶的一個人,就自一隻水晶玻璃瓶中,斟出上佳的白蘭地來。而他們之中,有三個人是在大學執教的,有五個人,是世界著名大學的博士。
他們看到了我,笑着和我打招呼,其中一個用指扣着那銅瓶,道:“喂,要看看巴比倫時代的絕世古物麼?”
我搖了搖頭,道:“不要看,但是我有一樣東西,請你們鑒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