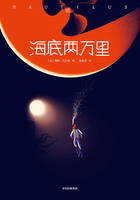
四 尼德·兰
法拉格舰长是一位优秀的海员,配得上他指挥的这艘战舰。船与他融为一体,他是船的灵魂。关于那头鲸鱼,他的心中没有任何疑问,他不许在船上讨论这只动物是否存在的问题。他相信它的存在,就像许多善良的妇人相信有利维坦 一样,是出于信仰,而非理智使然。这怪物是现实存在的,他发誓要把它从海上清除出去。他就像罗德岛的骑士,像戈松岛的迪厄多内去迎击骚扰他海岛的巨蟒。不是法拉格舰长杀死独角鲸,就是独角鲸要了法拉格舰长的命,没有什么折中的出路。
一样,是出于信仰,而非理智使然。这怪物是现实存在的,他发誓要把它从海上清除出去。他就像罗德岛的骑士,像戈松岛的迪厄多内去迎击骚扰他海岛的巨蟒。不是法拉格舰长杀死独角鲸,就是独角鲸要了法拉格舰长的命,没有什么折中的出路。
船上的军官们都赞同长官的意见。他们闲谈着,讨论着,争辩着,设想着碰见怪物的各种机会,不断侦察着辽阔的海面。不止一个人抢着要到顶桅的横木上去值班,要是换了另一种情形,他肯定对这种差事叫苦连天。只要太阳没落下,船桅边总是挤满了水手,全然不顾滚烫的甲板炙烤着脚掌,让他们几乎站不住脚!其实,林肯号的船头这时还没有沾上太平洋的边呢。
至于船上的工作人员,大家一心盼望着遇上海麒麟,用鱼叉刺死它,把它拖上船,大卸八块。他们小心翼翼地侦察着大海。何况,法拉格舰长说过,不论学徒或者水手,大副还是军官,谁先发现海麒麟,都可以得两千美元的奖金。不用我说,诸位也不难想象,林肯号上的眼睛是有多忙碌。
至于我,自然也不甘落后,每日的观察活动我从不让别人代劳。如果这艘船的名字叫作“阿尔戈斯 号”,那才贴切呢。所有人当中,唯有康塞尔对于令我们痴狂的问题表示很冷淡,与船上大家的热情格格不入。
号”,那才贴切呢。所有人当中,唯有康塞尔对于令我们痴狂的问题表示很冷淡,与船上大家的热情格格不入。
我说过,法拉格舰长很细心地为他的战舰配备了抓捕巨鲸用的各种专用装备。就是一只捕鲸船也不会有比它更多的装备。我们船上的武器应有尽有,从手投的鱼叉,一直到长满倒刺的鱼叉枪和装满火药的猎枪。在前甲板上装有一门先进的火炮,后膛装弹,炮身厚实,炮口很窄。这种炮的模型曾在一八六七年的万国博览会中展览过。这门美国制造的宝贵大炮可以轻而易举发出重四公斤的锥形炮弹,平均射程是十六公里。
可以说,林肯号的歼灭性武器真是应有尽有。但更妙的是,船上还有号称“鱼叉手之王”的尼德·兰。
尼德·兰是加拿大人,他的身手矫捷非凡,在这种危险的叉鱼职业中,无人能出其右。他灵敏又冷静,大胆而狡黠,本领十分高强,如非聪明过人的长须鲸,或是特别狡猾的抹香鲸,普通鱼类难逃他的鱼叉之劫。
尼德·兰大约四十岁。他身材魁梧,有六英尺多高,体格健壮,神色庄严。他不大爱说话,有时很暴躁,遇上有人抬杠会大发雷霆。他这人特别引人注意,尤其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使他的面貌更加特别。
我认为法拉格舰长把这人招募到船上来是很明智的。他眼光敏锐,手臂强壮,单单一人就抵得上全体船员。我找不出再好的比喻了,只能说他是一架高倍望远镜,同时又是一门随时准备发射的大炮。
说是加拿大人,就差不多是法国人了。尽管尼德·兰平日寡言少语,但我应当承认,他对我却有一种特别的好感。大约是我的国籍吸引了他。对他来说,正好有机会可以说说话,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听听这种加拿大某些省份现在还通行的拉伯雷时代的古老法语。这位鱼叉手的老家是在魁北克。这座城市还属于法国的时候,他家里就已经出了一批勇敢的鱼叉手了。
慢慢地,尼德·兰有了谈话的兴致,我很爱听他讲在极地海洋上的冒险故事。他用绘声绘色、充满诗意的语言讲述他打鱼和搏斗的故事。他的故事具有史诗的色彩,我听他讲,好像是在听一位加拿大的荷马在朗诵着北极的《伊利亚特》。
现在,我要把这位勇敢的伙伴如实地描绘出来。这是因为,在患难中产生并得到巩固的友谊把我们连在了一起,让我们成了老朋友!啊!勇敢的尼德·兰!但愿我再活一百年,可以长长久久地想念你!
那么,尼德·兰对于海怪问题是怎样看的呢?我得承认,他并不相信有什么海麒麟,船上的人里只有他不同意大家的看法。他甚至对这个话题刻意回避,但我想总有一天会使他谈到这件事的。
七月三十日,即我们出发之后三个星期,船在黄昏的时候到达离帕塔哥尼亚海岸三十海里处,跟布朗角处于同一纬度。那时我们已经越过了南回归线,南面不到七百海里处就是麦哲伦海峡。用不了八天,林肯号便将行驶在太平洋的波涛上了。
尼德·兰跟我一同坐在艉楼上东扯西谈,一边看着这神秘的大海。海洋深处至今仍然是人类目光不可及的地方。这时候,我很自然地把话题转到巨型海麒麟上面,又谈到我们这次远征成功或失败的各种可能。然后,我看见尼德·兰闷声不响地由着我说,就直截了当地催促他表态。
“怎么,尼德?”我问他,“您怎么能怀疑我们追捕的这头鲸鱼不存在呢?您这样怀疑,有什么特别理由吗?”
鱼叉手在回答之前看了我一会儿,习惯性地拿手拍拍他宽大的前额,闭起眼睛,若有所思。他说:
“也许是的,阿罗纳克斯先生。”
“尼德,您是一位职业的捕鲸行家,您很熟悉海中的巨型哺乳动物,您应当很容易就接受这个巨鲸的假设,这种情况下您应该是最不会持怀疑态度的人!”
“这您就错了,教授先生。”尼德说,“普通人相信天上会扫过奇特的彗星,相信地底下住着太古时代的怪兽,那还说得过去;但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就不会承认这类荒唐古怪的东西。捕鲸手也一样。我追逐过许多鲸鱼,我用鱼叉叉过很多,也杀死过好几条,可是它们再力大无穷,神勇生猛,它们的尾巴和长牙都没法弄坏一艘汽船的钢板。”
“可是,尼德,独角鲸的牙齿把船底钻通的传说也有不少吧。”
“木头船是可能的,”加拿大人回答,“不过,就是这种事,我也从没有亲眼见过。所以,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我不认为长须鲸、抹香鲸或独角鲸可以干出这种事。”
“尼德,您听我说……”
“不,教授先生,不。什么都可以听您的,这个除外。也许,是一条巨大的章鱼?……”
“那更不可能了,尼德。章鱼是软体动物,这个名字本身就表明,它的肌肉一点也不强硬。就算章鱼有五百英尺长,它也不属于脊椎动物门,它对于斯科蒂亚号或林肯号这类船只,无法构成威胁。所以要说这事儿是克拉肯或此类怪物的杰作,那都是无稽之谈。”
“那么,博物学家先生,”尼德用略带讥诮的口气说,“您坚持认为有一头巨型的鲸鱼喽……”
“是的,尼德,我再说一遍,我很确定,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我相信有一种哺乳类动物存在,它身形强壮,像长须鲸、座头鲸或海豚一样属于脊椎动物,并且长着一个角质的长牙,钻穿力十分强大。”
“唔!”鱼叉手哼了一声,摇摇头,一副不能信服的样子。
“请注意,我诚实的加拿大朋友,”我继续说道,“假设有这样的一种动物,它生活在大洋深处,主要在离水面几海里深的水层活动,那它必然会有坚强无比的躯体。”
“为什么要这么坚强的身躯呢?”尼德问。
“因为要在深水中生活并抵抗水的压力,那就必须有一种巨大无比的力量。”
“真的吗?”尼德眨眨眼睛,看看我。
“是的,有一些数据可以证明。”
“啊!数据!”尼德回击道,“数据爱怎么说都可以!”
“尼德,这是实际数据,而不是数学推算。听我说,我们都知道,一个大气压力相当于三十二英尺高的水柱压力。实际上,这水柱的高度会更小一点,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海水,海水的密度比淡水要大。好吧,当您潜到水里,尼德,在您上面有多少倍三十二英尺的水,您的身体就要承受多少倍数大气压的压力,也就是说,每平方厘米面积上要承受同等倍数公斤的压力。照这样推算,在三百二十英尺深处的压力是十个大气压,在三千二百英尺深处是一百个大气压,三万二千英尺深,就是说,大约两点五古海里深处,是一千个大气压。这就等于说,如果您潜入大洋到这样的深度,您身上每平方厘米就要受到一吨的压力。可是,我勇敢的尼德,您知道自己体表有多少平方厘米吗?”
“相当多吧,阿罗纳克斯先生。”
“大约有一万七千平方厘米。”
“有这么多?”
“实际上,一个大气压比每平方厘米一公斤的重量还要略大一些,您身上一万七千平方厘米的面积此时就顶着一万七千五百六十八公斤的压力。”
“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
“您一点不觉得。您没有被这样大的压力压扁,那是因为进入您身体的空气也有同等的压力。于是,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能够达到完美的平衡,相互抵消了,所以您可以承受着这样的压力而不觉得辛苦。但在水中就是另一回事了。”
“好,我明白了。”尼德答道,他的样子更专注了,“因为水在我周围,并没有进入我身体。”
“对,尼德。所以说,在水下三十二英尺,您要受到一万七千五百六十八公斤的压力;在水下三百二十英尺,压力还要大上十倍,即十七万五千六百八十公斤;在水下三千二百英尺,压力要大上百倍,即一百七十五万六千八百公斤;最后,在水下三万二千英尺,压力要大上千倍,即一千七百五十六万八千公斤;就是说,您会被压扁,就像从水压机的铁板下拉出来一样!”
“好家伙!”尼德叫出声来。
“好,我诚实的鱼叉手,如果有些脊椎动物,身长数百米,体量巨大,住在这样的海底深处,那么,它们的身体表面积有数百万平方厘米,它们所受到的压力就要以十亿公斤来计算了。现在您来算一算,要顶住这样大的压力,它们的骨架该有多坚固,躯体该有多强壮吧!”
“它们的身体得要用八英寸厚的钢板造成,”尼德回答,“就跟铁甲战舰那样。”
“正是。尼德,现在您想想,这样一个巨大的物体,以快速列车的速度撞在一艘船上,可能产生怎样的破坏力。”
“是……确实……也许。”加拿大人回答,这些数字令他受到了震动,但他还不愿意认输。
“那么,我说服您了没有?”
“您使我相信了一件事,博物学家先生。就是说,如果海底下有这样的动物,那它们必然像您所说的那样强壮。”
“可如果海底下没有这样的动物,固执的鱼叉手,您怎样解释斯科蒂亚号的遭遇呢?”
“这也许……”尼德迟疑了。
“请继续说!”
“是因为……这不是真的!”加拿大人答道,情急之下无意中吐出阿拉戈 的这句名言。
的这句名言。
但这个回答除了证明鱼叉手的固执之外并不能说明什么。这一天,我不再追问他。斯科蒂亚号的事故是不可否认的。船底上的洞真真切切,非得堵住才会消失,当然我并不认为有一个洞就能说明什么。可是这洞绝不是无缘无故就有的,那么既然它不是暗礁或海底机器撞的,那必然是某种动物的尖利武器钻的了。
那么,根据前面的种种推理,我认为这个动物属于脊椎动物门,哺乳动物纲,鱼形目,鲸鱼目。它应属于长须鲸、座头鲸或海豚的那一科。至于它是什么属,什么种,那就有待将来才能弄清楚。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剖这个神秘的怪物;要解剖它,就得捉住它;要捉住它,就得叉住它,这是尼德·兰的事;要叉住它,就得找见它,这是全体船员的事;要找见它,就得碰上它,这就得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