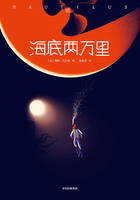
十 海洋人
说话的正是船长。
听到这些话,尼德·兰立即站了起来。侍者被掐得半死,看见主人一个手势,便蹒跚地走出去了,没有流露半点对加拿大人的愤恨,这说明船长在船上有很高的威信。康塞尔不禁有些奇怪,我也看呆了,我们默默等待,静观事情如何发展。
船长倚着桌子的一角,交叉着两手,仔细地观察我们。他在犹豫着什么,不肯说话吗?他后悔刚才用法语开口说话了吗?相信应该是这样。
沉默持续着,没有人想要打破。过了一会儿,他才用镇定而富穿透力的声调说道:
“先生们,我会说法语、英语、德语和拉丁语。我本来可以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就跟你们交谈的,不过我想先认识你们,然后再考虑。你们把事情复述了四遍,内容完全相同,这使我肯定了你们的身份。我现在知道,机缘巧合使得我碰见了负有出国做科学考察使命的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教授皮埃尔·阿罗纳克斯先生,他的仆人康塞尔以及美利坚合众国海军战舰林肯号上的鱼叉手、加拿大人尼德·兰。”
我欠身表示同意。船长并非向我提问,所以我无须回答。这人的法语说得十分流畅,没有任何口音。他遣词造句清晰准确,表意十分自如。可是我总“感觉”不出他是我的法国同胞。
他继续说下去:
“先生,我过了这么久才再一次来探访你们,你们一定觉得我耽搁得太久了。这是因为知道你们的身份以后,我想仔细考虑一下应该如何对待你们。我犹豫了很久。我已经和人类断绝了联系,现在又遇到了你们,真是令人为难。你们打乱了我的生活……”
“我们无意冒犯。”我说。
“不是故意的吗?”此人稍稍提高了嗓音,“林肯号在海面上对我围追堵截,难道是无意的吗?你们登上那艘战舰,难道不是故意的吗?你们的炮弹打到我的船上,难道不是故意的吗?尼德·兰师傅用鱼叉打我的船,难道也不是故意的吗?”
我看得出在这些话里面隐含着愤怒。但对于他提出的这些指责,我有个很合理的回答,我就说:
“先生,您一定不知道您在美洲和欧洲所引起的争论。您不知道由于您的潜水艇引起的撞船事故,对两个大陆的舆论产生了多大的冲击。人们为解释神秘现象做了无数假设,而其中的奥妙唯有您才知道,具体种种我就不一一赘述了。但您要知道,林肯号一直追逐您到太平洋北部海面,仍然认为是在追击一头力大无穷的海怪,想不惜代价把它从海洋中清除掉呢。”
船长的唇上浮现出一丝微笑,他的语气柔和起来:
“阿罗纳克斯先生,您敢肯定你们的战舰不会像追击海怪那样去追击一艘潜水艇吗?”
这个问题使我很为难,因为法拉格舰长肯定不会迟疑。他一定相信,消灭这类潜水艇和打击巨型独角鲸同样是他的职责。
“先生,您要知道,”他又说道,“我有权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
我故意不回答。因为理论碰到强权的时候,讨论这类话题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犹豫了很久,”船长又说,“我没有义务接待你们。如果我要撇下你们,我就不会再有兴趣来看你们了。我会把你们重新放在你们曾经避过难的艇顶平台上,只管自顾自潜入海中,就当你们没有存在一样。难道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吗?”
“这也许是野蛮人的权利,”我答,“而不是文明人的权利。”
“教授先生,”船长激动地反驳,“我不是你们所说的文明人!为了我个人才有权评判的理由,我跟整个人类社会断绝了关系,所以我不服从人类社会的法规。我奉劝您以后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这些了!”
这话说得十分干脆。这人眼中闪出愤怒和轻蔑的光芒,我隐隐感觉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定有过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他不但把自己置于人类的法律之外,而且使自己绝对地独立自主,不受任何约束!既然在海面上和他交手都被他打败了,谁还敢到海底去追赶他呢?什么船能承得住他这艘潜水艇的冲击呢?不管铁甲舰的钢板多么厚,哪一艘能吃得消它的冲角的撞击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对他所做的事提出质问。如果他相信上帝,如果他还有良心,那么只有上帝,只有良心,才是唯一可以对他进行评判的了。
以上的这些感想在我心中一闪而过。其间,这个怪人默不作声,仿佛在潜心思索什么。我既害怕又好奇地注视着他,就像俄狄浦斯在注视着斯芬克斯一样。
经过长久的沉默以后,船长又开口了:
“因此,我迟疑不决,”他说道,“但是我认为,我的利益是能够与人类天生的那种同情心达成一致的。既然命运把你们送到这里来,你们就留在我的船上吧。你们在船上是自由的,但这是相对的自由,作为交换条件,我要你们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们只要口头上答应就可以了。”
“先生,您说吧,”我答,“我想这一定是一个正派人士可以接受的条件吧?”
“是的,先生,条件是这样。可能因为某种意想不到的事件,我不得不把你们关在舱房里,关上几小时,或是关上几天,视情况而定。我决不愿使用暴力,我希望你们在这种情况下,比任何其他情况更要绝对服从。这样做,一切都由我负责,与你们毫无关联,因为我不能让你们看见不应该被看见的东西。你们能接受这条件吗?”
如此看来,船上一定有些离奇古怪的事,是遵循社会法律的人不应该看的!那么,在我将来可能碰到的奇异事件当中,眼前这件事给我的诧异应该不是最小的。
“我们接受,”我答,“但是,先生,请您允许我向您提一个问题,就一个。”
“说吧,先生。”
“您刚才说我们在船上可以自由行动,是不是?”
“完全自由。”
“我想问您,您所说的是怎样的自由?”
“就是自由走动,自由观看,甚至可以自由观察船上发生的一切的自由——某些特殊情况除外,总之,跟我们——我的同伴和我,享有同样的自由。”
显然,我们彼此都没有领会对方的意思。
“请原谅,先生,”我于是又说,“这种自由不过是囚犯在监狱中走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对我们来说并不够。”
“可是,对此你们应当感到满足了。”
“什么!我们将永不能再见我们的祖国、朋友和亲人吗?”
“是的,先生。但这不过是使您摆脱世俗的束缚。人们还当这种束缚是自由,抛弃它,不至于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难受吧!”
“还有这种事!”尼德·兰喊道,“我可不能保证以后不会想法子逃走!”
“尼德·兰师傅,我并没有要您保证什么。”船长冷淡地回答。
“先生,”我愤恨难耐地说道,“您这是仗势欺人!蛮不讲理!”
“不,先生,这不是蛮横,这是仁慈!你们是我的俘虏!我只要说一句话就能把你们扔到海底里去,但我留下了你们!你们攻击过我!你们撞见了世上任何人都不应该知道的秘密,关乎我生死存亡的秘密!您以为我会把你们送回那再不应该看见我的陆地上去吗?不可能!我把你们留在这儿,并不是为了你们,而是为我自己!”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船长主意已定,任何理由都改变不了他。
“先生,”我又说,“这样看来,您只是让我们在生死之间做个选择罢了。”
“正是。”
“我的朋友们,”我说,“对于这样的问题,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但我们对于这艘船的主人也没有任何承诺。”
“没有任何承诺。”这个神秘的男人答道。
随后,他用比较温和的口气说:
“现在,请允许我说完。阿罗纳克斯先生,我了解您。您和您的同伴不一样,您也许并没有那么抱怨机缘巧合,把你们跟我的命运联结在了一起吧!在我用于研究的我所喜爱的书籍中,您可以找到您发表的那部关于海底的著作。我时常拜读这本书。这部著作已经达到了陆地上的学问可以使您达到的极致。但您还不是什么都懂,还不是什么都看见过。教授,让我告诉您吧,您决不会懊悔您在我的船上度过的时光。您将领略各种旖旎盛景。震惊、错愕将成为您的精神常态。奇异的景象琳琅满目,使您应接不暇。我在下一次周游海底世界的时候——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谁知道呢?我将又一次看到在海底下曾经无数次研究过的一切事物,那时您将成为我科学研究的同伴。从这一天起,您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您将看见世界上任何人——我和我的同伴已经不在这之内了,任何人都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拜我所赐,我们的星球将把它最后的秘密呈现给您。”
我不能否认船长的这些话对我产生了很大的震撼。他戳中了我的心事,我一时竟忘记了,观赏这些奇光异景并不能抵偿我们失去的自由。我甚至于想搁下这个严肃的问题,留待以后再作打算。所以我只是这样回答他:
“先生,您虽然跟人类世界断绝了往来,但我想您还没有抛弃人的情感。我们是被您好心收留在船上的海难幸存者,您的大恩大德我们不会忘记。至于我,如果科学的兴趣可超越自由的渴望,那我不否认,我们的相遇将给我带来巨大的补偿。”
我以为船长会来跟我握手,借此表示我们达成了协议。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我真替他惋惜。
“最后一个问题。”当这个难以琢磨的人物正要离去的时候,我对他说道。
“教授先生,请讲。”
“我该如何称呼您?”
“先生,”船长回答,“对您来说,我只不过是尼莫 船长,对我来说,您和您的同伴不过是鹦鹉螺号上的乘客。”
船长,对我来说,您和您的同伴不过是鹦鹉螺号上的乘客。”
尼莫船长喊人进来,一个侍者应声出现。船长用我听不懂的那种外语吩咐了几句。然后他转身对加拿大人和康塞尔说:
“饭菜在你们的舱房里。请跟着这个人去吧。”
“那就不客气了!”鱼叉手回答。
于是康塞尔和他终于走出了这间关了他们三十多小时的房间。
“阿罗纳克斯先生,我们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了,请允许我给您引路。”
“恭敬不如从命,船长。”
我跟在船长后面,一出房门,便走上一条有电光照明的走廊,像是船上的过道。约走了十多米以后,第二道门在我们面前打开。
我于是走进了餐厅。餐厅内的装饰和家具肃穆典雅。两端分别立着镶嵌乌木花饰的高大橡木餐橱。在波浪形的隔板上,无价的陶器、瓷器和玻璃器皿熠熠生辉。光线从明亮的天花板倾泻而下,将平底餐具照耀得光彩夺目。天花板上绘有精美的图画,使光线更加柔和悦目。
餐厅的中间摆着一桌丰盛的饭菜。尼莫船长指了指我的座位。
“请坐,”他对我说道,“您已经饿了好久了吧,请不要客气。”
午餐有好几道菜,皆是海产,其中有几道荤菜,我既不知为何物,也不知从何而来。我得说,这些菜都很好吃,却有一种特殊的风味,不过我很快就习惯了。它们看起来都富含磷质,我想一定来自于大海。
尼莫船长看着我。我并没有问他,但他猜到了我的心事,就主动地回答了我急于要向他提出的问题。
“这些菜大部分您以前都没见过。”他说道,“但您可以放心大胆地吃。这些菜很卫生,也富有营养。很久以前,我就不吃陆地上的食物了,我的身体也并不见得差。我的船员个个身强力壮,他们吃的东西和我一样。”
“那么,”我说,“这些食物都是海产吗?”
“是的,教授,大海满足我一切的需求。有时我抛下拖网,等网满得都要断了就把它拉上来。有时我到人迹全无的海域去打猎,追逐那些居住在我的海底森林中的野味。我的牲畜们,就像海神的牛羊一样,无忧无虑地在那广阔的海底牧场上吃草。我在海底有一笔巨大的产业,由我自己开垦。造物主在那里亲手播种下万物。”
我有点惊异,看着尼莫船长,答道:
“先生,我完全相信您的渔网提供了这一桌丰盛的鱼类,但我不太明白您如何在您的海底森林中打猎,我最不明白的是,在您的菜单上,如何能有肉类,尽管并不很多?”
“先生,”尼莫船长回答,“我从来不吃陆上动物的肉。”
“那这是什么呢?”我手指着一个盘子里还剩下的几块肉说。
“教授,您以为这是肉吗?其实它是海龟里脊。这盘是海豚的肝,您大概以为是炖猪肉吧。我的厨师手艺精湛,他善于贮藏海中各种不同的产物。您尝一尝这些菜。这是一盘罐头海参,就是马来人也会称赞它的举世无双。这是奶油,所用的奶取自鲸类,糖是从北极海中的一种大海藻里提炼出来的。最后我请您尝尝这罐海葵酱,它的味道并不亚于最可口的水果酱。”
我一一尝了尝,与其说是由于贪食,不如说是由于好奇。同时,尼莫船长讲着他那不可思议的故事,听得我心醉神迷。
“阿罗纳克斯先生,”他说,“大海是奇妙的、取之不尽的生命泉源,不仅给我吃的,还给我穿的。您身上穿的衣料是由一种贝壳类的足丝织成的,染上老荔枝螺的绛红色,再调配上我从地中海海兔螺中提取出的紫色;您在舱房梳洗台上看到的香料,是从海洋植物提炼出来的;您睡的床是海中最柔软的大叶海藻做的;您用的笔是鲸鱼的触须,墨水是墨鱼或乌贼分泌的汁液。大海给我一切,总有一天,一切都要归还给它!”
“船长,您很爱大海吧?”
“是的,我爱大海!大海包罗万象,它占地球面积的十分之七。海洋的气息清新纯洁。在这汪洋的大海中,人类不是孤独的,他们能感到周围处处都有生命的悸动。大海只是超自然的神奇生物的一个载体;它是运动的,它充满了爱;正像你们的一位诗人所说,它是无限的生命。的确,教授,自然在海中也同样有矿物、植物、动物三类。动物在海中大量地繁衍,主要有四类腔肠动物,三个纲的节肢动物,五个纲的软体动物,三个纲的脊椎动物:即哺乳类、爬行类和无数的鱼类。鱼类这一目的种类多到无穷无尽……共有一万三千多种,其中只有十分之一生活在淡水中。海洋是大自然的巨大宝库。可以说,地球是从海洋开始的,谁知道将来它是不是在海里结束呢!海中有无比和平的环境。海不属于压迫者。在海面上,他们还可以使用暴力,在那里互相厮杀,互相吞噬,把陆地上的各种恐怖手段都搬到那里。但在海平面三十英尺以下,他们的权力便终止了,他们的气焰熄灭了,他们的势力消失了!啊!先生,生活到大海里来吧!只有在海里才有独立!在海里我不用俯首称臣!在海中我是自由的!”
尼莫船长正说得兴高采烈,忽然停住不作声了。他超出了惯常的沉默,忘乎所以了?是说得过多了?一时间,他踱来踱去,情绪很激动。过了一会儿,他的心神平静下来,脸上又现出惯常的冷淡神气,他转身对我说:
“现在,教授先生,如果您想参观鹦鹉螺号,我愿意效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