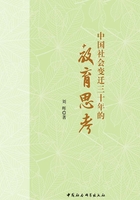
二 教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传播
以上我们从传播角度透视整体教育活动的发生、发展及其过程,得出了传播是教育的根本特征,没有传播就无所谓教育的结论。显然,教育理论工作者应该正视这一事实,考虑从传播出发构筑教育学理论的逻辑体系。
科学巨匠爱因斯坦认为:在理论研究中唯一事关紧要的是基础的逻辑简单性。任何一门科学理论都应在分析其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明确它的逻辑起点,并以此展开逻辑论证体系。爱因斯坦正是从“四维时空的相对关系”出发创立了“相对论”;马克思则以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根本特征——商品——为逻辑起点,建树了科学理论——《资本论》。我们认为修正目前教育理论科学性不强、结构松散、功能紊乱弊端的一条有效途径是变“多头起点”为一个科学的“逻辑起点”,这个起点是传播。以贯穿整个教育活动的简单的逻辑轴心——传播——为起点,有助于建立科学的教育理论大厦。
首先,从“传播”出发,有利于教育理论的科学抽象。
理论所以能够对实践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是因为它对研究现象的科学抽象,这种抽象不是模棱两可的思辨,而是从一定的逻辑起点出发,透过现象对事物本质联系的分层次的升华。这样才能使理性思维与指导实践成为可能。
如前所述,目前的教育理论要么囿于高层次的思辨(如教育本质问题、影响人发展的因素问题),要么流于经验的简单汇集(如一些教学原则,对学生学习的分析、评价等)。这说明理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支点,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坐标,对教育现象进行科学的抽象,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实践进行整体的而不是片面的,连贯的而不是割裂的指导。
以“传播”为坐标有利于教育现象的深入认识、科学抽象。自人类有教育活动以来,教育的形式、规模、内容、方法、对象和教育者等经历了巨变,但教育的传播形式只有三种,即自我传播、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任何教育培养的任何人都是通过这三种传播来完成的。教育的作用就是使三种传播协调统一,使受教育者获取知识、形成能力、树立世界观,从一个“生物人”成为“社会人”。所以教育理论的最高层次抽象应从整体入手,对教育中的自我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有个概括的认识。这有助于人们树立科学的、总体的时空观念。顺着这个坐标,可以进行第二层次的抽象。教育中的三种传播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在学校、家庭、社会范围中对受教育者实施影响的。教育理论应阐明学校教育传播、家庭教育传播、社会教育传播现象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律,研究它们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对人产生影响。第三层的抽象,可以看成是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各自内部教育传播的认识。例如,在学校教育中,有人际传播(教师授课、教育者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团体之间的交流等)、大众传播教育(教育卫星及闭路电视教学、电脑教学等)和自我传播教育(学生接受上两种传播而引起的自我认识的提高、自身知识结构、道德观的变化过程)。第四层的抽象是更进一步对微观教育传播的认识。如学校人际传播教育、自我传播教育等问题。对这些单因素进行分析抽象,建立具体指导教育、教学的理论。
以上是从传播出发对教育活动的整体过程进行的纵深的四个层次的抽象。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传播的内容、功能进行平行的横向认识。教育传播包括知识的传播、价值观的传播、对美的鉴赏的传播等,即德、智、体、美、技。这些不同内容的传播,既是综合的整体,又各自有其特点、规律,有必要抽出研究。
为便于理解,这里不妨以影响人发展的教育因素为例,进行直观分析。

可见,以“传播”为红线对教育进行贯穿始终的研究,可以理出清晰的、逻辑严谨的脉络,对教育活动的不同层次进行概括、抽象,建立一套层次分明、阐述精确的教育理论,提高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效能。
其次,从“传播”出发,有利于建立科学的教育理论模式。
传播学家赛弗林认为:“模式的运用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了起来,清晰的模式就是一种测定,这种测定可能仅表明排列次序,也可能是完全的比率。”事实表明,“模式研究”(Model Study)已成为与“语言研究”(定性研究)和“数学研究”(定量研究)并驾齐驱的三大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之一。
模式(Model)也称作模型,是系统或过程的一种简化、抽象和类比的表示。它不再包括原系统或过程的全部特征。美国比较政治学家比尔认为:“模式是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性的、简化的形式……它的特点在于能够体现出各种关系”。有的学者简明扼要地归纳说:“模式形象地反映现实,代表一种有效的推理研究方法”。虽然人们对模式的表述不同,但可以从中抽象出其主要特性——约简性,即模式把现实简化为基本的要素,通过剖析纷纭复杂的客体现象,理出其基本特征,并以此出发,对诸要素进行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最后在总体上认识事物。
以“传播”为出发点进行研究,有助于确定教育的各种图像即模式。从上面论述不难看出,教育传播的特点与建立模式的特性是吻合的。第一,从因素分析角度看。以传播为标准可以把教育中的因素十分明晰地展现出来。例如学校教育,可以从人际传播分出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之间、教师之间等诸种传播因素,而分析存在的因素数是建立模式的基本条件。第二,从因素取舍看。教育中的诸因素对整体的意义并非等量齐观的,有的是主要的,必须考虑的;有的是次要的,或者是可忽略的。从传播角度可以把握、提升主要因素。建立模式必须将教育中的因素分为不重要的、局外的和局内的三部分。这样才能科学详细地说明变量因素间的相互关系,避免事无巨细的笼统分析。第三,模式研究的种类很多。根据其研究对象和解决问题的不同,可以分为宏观模式、微观模式和混合模式。前面提到,从传播出发有利于教育理论的不同层次的抽象。这种抽象过程也就是建立一套从宏观到微观的模式过程,因为模式是一种简化的理论。例如,研究影响人发展的“人际大众传播模式”“全面发展教育的混合传播模式”“课堂传播模式”等,这些模式都是对一定范围的教育过程之间各要素关系的清晰表示。模式关系明确,就可以对各要素进行分析,实施控制,直至用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这是建立教育研究模式的最高目标。
在此,我们拟用一个“学校人际传播模式”为例来具体说明问题。

图1 学校人际传播模式
E—学校环境 T—学校教育工作者 S—某受教育者 C—学生小团体 B—学习材料 X—传播影响(德、智、体、美、技……) fST—学生的反馈
这是一个在某学校范围内,对某学生施以教育影响的“学校人际传播模式”。
从这一模式中,教育工作者可以明了学校环境中影响学生发展的诸种人际传播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以便在分析每种传播因素的基础上,找到其传播的有效途径,并站在系统观的高度,调节各种人际传播达到指向教育目标的“合力”,对学校人际传播实施最优化控制。这体现了模式这一简化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这其中的每一种传播(如S—T传播)又可以继续细化,建立低层模式。可以说每一次分层,都使模式趋于现实化、精确化。最后,达到建立因素分析、控制的数学模型。如果每一因素可以精确定量,操作控制,那么层层上行,整体的学校人际传播也就可以控制了。学校出现了问题,可以通过调节一个(或几个)传播因素予以解决,这样可以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避免以往学校中常出现的“工作重点转移”——一会儿强调知识传授,一会儿重视能力培养,一会儿校风不好又忙于加强德育……
学校教育的最优化远不是一个人际传播模式可以解决问题的,这需要一个以人际——大众——自我“整体传播模式”为首的“模式群”。值得强调的是:从传播出发考虑建立教育理论模式,是教育理论科学化的方向。
最后,从“传播”出发,有利于吸收各门学科的成果,丰富教育理论。
教育理论应呈现出开放系统的“耗散结构”特征,不断与其他学科进行各种交流,在交流中生存、发展、壮大。但交流、引进要防止生搬硬套、“兼收并蓄”,应科学建立自己的基点、方法、体系的基础上,“合理吸收”。各种新成果、新方法进入教育理论的“殿堂”,要有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应当是以传播为基点建立的模式。举例说,目前“三论”对教育研究的渗透已成为大趋势。而传播与“三论”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信息论是申农在研究通讯理论的基层上产生的。他在《传播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基于传播的统计学概念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传播模式。这对教育领域的传播现象的认识和模式的建立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传播中必然存在控制、反馈问题,而传播的层次分层本身就需要系统论的指导。无疑,以传播为逻辑起点展开的教育理论,十分便于现代横向科学的引入、指导。传播直接涉及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义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所关心的问题,这必然要求教育科学吸取其精华来丰富、充实自己。
总之,确立传播为教育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有利于各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教育理论框架中找到其合适的位置。
(原载《教育理论与实践》1987年第1期;与王箭合作完成;《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1987年第3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