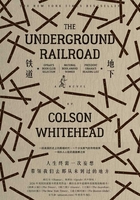
第4章 佐治亚(2)
科拉想讨回别人欠母亲的几笔债务,她知道的那几笔。他们一口回绝。比如那个叫博的女裁缝,有一次发烧,是梅布尔照料她恢复了健康。梅布尔把自己那份晚饭给了她,还用青菜根混着青菜汁,一勺勺喂进她不停打战的嘴巴,直到她再一次睁开眼睛。博说,债她已经还过了,而且还多还了呢。她还告诉科拉滚,滚回伶仃屋去。科拉记得,那次有些农具不见了,是梅布尔为卡尔文打掩护,提供了不在场的证明。康奈利在用九尾鞭抽人方面颇有心得,倘若不是梅布尔为卡尔文捏造说辞,他脊背上的肉非得叫康奈利一条条地打飞不可。如果康奈利发现梅布尔撒谎,她的下场肯定也一样。晚饭后,科拉悄悄找到卡尔文:我需要帮助。他叫她走开。梅布尔说过,她从来没发现他拿那些工具要派什么用场。
没过多久,布莱克的意图便人人周知了。有天早上,科拉一醒来,侵犯的事便临了头。她离开伶仃屋去察看菜园。那是个凉飕飕的清晨。一缕缕白色的雾气在地表盘旋。她在那儿看到了——那是她第一拨卷心菜的遗骸。藤蔓纠结,已经枯干,堆积在布莱克木屋的台阶旁边。地已经叫人翻过了,踏平了,变成了为杂种狗的房子修造的上佳的场院,狗屋坐落在她那块地的中央,仿佛种植园心脏地带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宅。
狗从门里探出头,好像知道这原本是科拉的地盘,所以刻意表现得无动于衷。
布莱克走出木屋,抱起双臂。他一口啐在地上。
人们聚集到科拉视野里的各个角落:一个个黑不溜秋的影子,满嘴的流言和责骂。瞧她,她妈跑了,她被赶进了贱人屋,谁也不上前帮帮她。现在这男人,一个身量三倍于她的彪形大汉,把她的地夺走了。
科拉一直在琢磨对策。要是再过些年,她可能会求助于伶仃屋那些女人或小可爱,可这是当时呀。外婆曾经警告,谁敢在她的地盘上胡来,她一准给那家伙开瓢儿。这种做法似乎超出了科拉的能力。过了一阵儿,她走回伶仃屋,从墙上摘了一把斧头,她睡不着觉的时候老盯着看的那把斧头。从前的住户留下来的,那些人一个个走到了悲惨的结局,要么是肺痨,要么被鞭子活活地剥了皮,要么就是五脏六腑拉了一地。
此时消息已不胫而走,看热闹的在木屋外徘徊,歪着脑袋,充满期待。科拉从他们身边大步走过,弓着背,好像逆风而行。没人出手阻拦,因为这一幕实在过于离奇。她第一斧砸掉了狗舍的屋顶,狗儿发出一声尖叫,尾巴差一点被劈成两截。它哧溜一下躲进了主人的木屋。她第二斧重创了狗舍的左墙,最后一击终结了小房的苦难。
她站在那儿,喘息不停。双手握着斧头。斧在空中舞动,置身于和幽灵的决战,但这小丫头没有退缩。
布莱克攥起双拳,一步步逼近科拉。小厮们跟在身后,个个绷得紧紧的。然后他停住了。此时此刻,在这二位——壮硕的大小伙子和纤细的小女孩之间发生的事,就成了谁能占得上风的问题。据木屋周围第一排观众所见,布莱克的脸因为惊讶和焦虑而扭曲了,活像某个一头撞进了大黄蜂领地的人的脸。那些站在新木屋旁边的人看到,科拉的目光左奔右突,仿佛在掂量一彪来犯的人马,而不只是一个男人。一支她无论如何也要迎战的大军。不管场面如何,重要的是一个人通过体态和表情传达给另一个人,并且被另一个人解读的信息:你可以打败我,但你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
他们对峙了一会儿,直到艾丽斯摇响早饭的铃铛。谁也不想放弃自己那口糊糊。趁着大伙从地里进屋的当儿,科拉清理了地块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她把槭木块翻过来,这原本是某个建筑活儿丢弃的废料,现在成了她空闲时的栖木。
如果说在阿娃暗地里使坏之前,科拉跟伶仃屋还不般配的话,现在她般配了。它最声名狼藉的住户,也是年头最长的一个。劳作终于毁灭了跛脚的——历来如此——那些神志处在失常状态的不是被便宜卖掉,就是拿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空缺是短暂的。科拉依旧。伶仃屋是她的家了。
她拿狗屋当了柴火。这让她和伶仃屋其他的人暖和了一夜,但狗屋的传奇从此给她打上了烙印,在她留在兰德尔种植园的日子里一直与她相随。布莱克和他那帮狐朋狗友开始搬弄是非。布莱克声称他在马厩后面小睡醒来,发现科拉拿着斧头站在那儿,冲他哭个没完。他是个天生的模仿者,用手舞足蹈给这故事增添了不少卖相。一旦科拉胸前开始萌芽,布莱克那一伙里最不要脸的爱德华便开始吹牛,说科拉冲他撩裙子,做出淫荡的暗示,他拒绝之后,她便威胁剥掉他的头皮。年轻的女人们窃窃私语,说瞅见她趁着满月,悄悄从木屋一带溜走,跑到树林子里,跟驴子和公羊通奸。有人发现后面这个故事不太可信,但还是认可了它的用途,它把那个怪异的女孩挡在了受人尊敬的圈子之外。
科拉初潮而花开的事为人所知后没过多久,爱德华、泡特和南半区的两个工人便把她拖到了熏肉房后。要是有谁看见或听见,他们也没干涉。伶仃屋的女人们给她做了缝合。此时布莱克已经跑掉了。也许是因为那一天见识过她的面孔,他早就告诫自己的弟兄小心遭到报复:你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可是他跑了。在她砸烂狗屋三年后,他跑掉了,在沼泽里藏了好几个星期。是他那条杂种狗的吠叫,给巡逻队指明了方位。如果不是因为他受的惩罚让科拉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她一定会说,狗对他可真孝顺啊。
他们已经从伙房抬出了大饭桌,摆上了为乔基的寿宴准备的食物。这一头,有个下套捕猎的把他捉来的浣熊挨个剥皮;另一头,弗洛伦丝刮掉一堆番薯上面的泥土。火在大锅底下噼啪作响,呼啸有声。汤在黑锅里翻腾,小块的卷心菜围着忽上忽下的猪头互相追逐,一只猪眼在灰白的浮沫里游走不定。小切斯特跑过来,想抓一把豇豆,但艾丽斯拿长柄勺把他打跑了。
“今天什么都没有,科拉?”艾丽斯问。
“太早了。”科拉说。
艾丽斯简单地表示了一下失望,便接着去弄晚饭了。
谎话大抵就是这个样子吧,科拉想,然后把它暗暗记下。只是她的菜园不肯就范罢了。上一次乔基过生日,她贡献了两颗卷心菜,艾丽斯予以笑纳。但科拉犯了个错误,她离开伙房后又转身回去,正好瞅见艾丽斯把她的菜丢进泔水桶。她脚步蹒跚,走到阳光底下。难道这女人认为她的食物很脏吗?难道艾丽斯就是这样,把科拉五年来贡献的每样东西统统扔掉,就是这样对待每一颗芜菁疙瘩、每一串青果的吗?这是从科拉开始的,还是梅布尔或外婆?和这女人对抗无济于事。艾丽斯过去是老兰德尔的宠儿,现在受宠于詹姆斯·兰德尔,他是吃着她的百果馅饼长大的。苦难也有次序,苦难里填塞着苦难,你得随时留神。
再说兰德尔兄弟。打从詹姆斯还是小孩的时候起,艾丽斯厨房的款待就能让他得到抚慰,番荔枝可以缩短发作的时间,还能败火。他弟弟特伦斯有着不同的性格。厨娘一只耳朵旁边仍然有个节,那是特伦斯少爷对她的肉汤表达不悦时留下的印记。他那年十岁。从他刚学会走路时起,就有了这种征兆,等他猛然间长大成人并开始履职,他性格里种种更加令人反感的部分便结出了累累的果实。詹姆斯有着鹦鹉螺般的性情,埋首于个人嗜好;特伦斯却把每一种转瞬即逝的和根深蒂固的幻想都强行灌注到他的权力中去了。他有权如此。
在科拉周围,盆盆罐罐叮当作响,小黑崽子们吱哇乱叫,眼瞅着桩桩乐事就要登场。南半区那边呢?什么都没有。兰德尔兄弟几年前通过掷硬币,决定了两片种植园管理权的归属,如此一来,这一天才成为可能。在特伦斯的领地,这样的宴会就不会发生,因为弟弟在奴隶的娱乐活动上颇为吝啬。兰德尔家的两个儿子按照各自的性情管理所属的遗产。詹姆斯满足于当前时髦的作物提供的安全保障,以及缓慢而必然的财产积累。土地和侍弄土地的黑鬼提供了任何一家银行力所不及的担保。特伦斯更积极地寻找机会,总是千万百计增加发往新奥尔良的运量。他要榨干每一块钱的潜力。当黑色的血就是金钱,这个精明的商人知道怎样把血管切开。
男孩切斯特和朋友们捉住科拉,吓她一跳。但这只不过是孩子。赛跑的时间到了。科拉总是把小孩安排在起跑线上,让他们的脚对齐,让好动的保持安静,视乎需要挑一些出来,放进大孩子的比赛。今年她就把切斯特往上提了一个级别。和她一样,切斯特也是个无家可归的,他的父母在他没学会走路时就被卖掉了。科拉照看他。毛刺脑袋,红眼睛。过去半年他噌噌地往高里长,棉田在他轻盈的身体内部唤醒了某些东西。康奈利说,他有条件成为一流的采摘工,而他是很少夸人的。
“你得往快里跑。”科拉说。
他抱起双臂,脑袋一翘:用不着你告诉我。切斯特已经成了半大男人,虽然他自己还不知道。科拉看到,明年他就没法子参加比赛了,只能懒洋洋地斜靠在场外,跟朋友开开玩笑,搞搞恶作剧。
年轻的奴隶和年老的奴隶聚集到了马道两旁。没了孩子的女人们一点一点移开,用种种的可能和种种的绝不可能克制着自己。男人们挤作一团,交换着装苹果酒的罐子,感觉自己的耻辱慢慢消散。伶仃屋的女人很少参加宴会,但奈格能帮上忙,她跑前跑后,把溜号的小家伙们赶到一起。
小可爱站在终点当裁判。除了小孩子,人人都知道,只要能上手,她总是要对获胜者示爱。乔基也在终点坐镇,屁股底下的槭木扶手椅已经快要散架,大凡夜晚,他都会坐在这把椅子上看星星。一到生日,他就在小路上把椅子拖过来,拉过去,对以他的名义举办的各种娱乐活动给予适度的关切。赛跑者完成比赛就去找乔基,他拿一块姜饼放到他们掌心,而完全不看名次。
切斯特双手撑住膝盖,喘着粗气。他在快到终点的时候被人超过了。
“差一点儿就赢了。”科拉说。
男孩回答:“差一点儿。”说完,他便去拿自己那份姜饼了。
比赛全部结束以后,科拉拍了拍老头的胳膊。你根本说不清他那双混浊的眼睛到底看见了多少。“您高寿了,乔基?”
“噢,我得想想。”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她记得很清楚,乔基上次做寿时说他一百零一岁。他其实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但这依然意味着在兰德尔家的两处种植园里,他是所有人见过的最老的奴隶。一旦你活到这个岁数,跟九十八或一百零八还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能拿给这世界看的,只是残虐恶行的最后一块活化石罢了。
十六七岁。这就是科拉对自己年龄的估算。康奈利命令她找个丈夫已有一年。泡特一伙让她开始成熟也已两年。他们没有再次施暴,那天以后,便没有体面的男人拿正眼瞧过她,因为她称之为家的那座木屋,还因为关于她神志错乱的那些故事。她母亲离开已经六年了。
乔基有个很好的生日计划,科拉想。指不定哪个出其不意的星期天,乔基一醒,便宣布他要庆祝,事就这样成了。有时这日子正逢连绵的春雨,其他时间则在秋收以后。有些年他跳过去了,或忘记了,或是心里怀着些个人的愤懑,认为这种植园不配庆祝。没有人介意他的反复无常。有这两样就够了:他是大伙平生所见最老的有色人;他熬过了大大小小的白人策划和施加的一切折磨。他两只眼睛雾蒙蒙的,他一条腿是瘸的,他一只废掉的手永久地蜷缩着,仿佛仍然紧握着铁锹,但他是个活人。
白人现在不管他了。兰德尔老爷子对他的生日什么都没说,詹姆斯接手以后也没过问。监工康奈利每逢星期天都难得一见,因为这时候他肯定召了哪个奴隶姑娘,指定她做当月的老婆呢。白人默不作声。他们好像已经放弃,或认定一点小小的自由是最毒的惩罚,可以将真正自由的丰盛表现为饮鸩止渴的慰藉。
总有一天,乔基能选中自己正确的生日。只要他活得足够长久。如果这是真的,如果科拉也间或给自己选个生日,那么她兴许也能碰对自己的那一天。其实呢,说不定今天就是她的生日。可是知道你生在白人世界的日子又能怎么样呢?这好像不是什么有必要记住的事。最好还是忘掉。
“科拉。”
北半区的大部分人到伙房来是找吃的,但西泽只是为了消磨时间。眼前就是他。自从这男人来到种植园,她一直没机会跟他讲话。新来的奴隶很快就会得到警告,别招惹伶仃屋的女人。省事儿。
“我能和你谈谈吗?”他问。
一年半前的热病造成多人死亡以后,詹姆斯·兰德尔从一个游商手里买下了西泽和另外三个奴隶。两个女人在洗衣房干活,西泽和普林斯下地帮工。科拉见过他削木头,用一套弯曲的刻刀在松木块上挖弄。他没有和种植园里更让人讨厌的那伙人厮混,但她知道,他有时跟一个名叫弗朗西丝的女仆搞在一起。他们还在同寝吗?小可爱肯定知道。别看她还是女孩,却对男女之事和行将发生的配对保持着密切关注。
科拉感觉要端庄一些。“你有什么事吗,西泽?”
他不担心隔墙有耳。他知道没人,因为他都计划好了。“我要回北方去。”他说,“很快。逃跑。我想要你也来。”
科拉很想知道是谁打发他来搞这种恶作剧的。“你去你的北边,我要顾着我的嘴边。”她说。
西泽抓住她一条胳膊,温和而急切。像他这个年纪所有下地干活的工人一样,他的身体瘦长而强壮,但他只是轻微地用了些力。他的脸圆圆的,鼻子扁平——她马上想起来他笑的时候有酒窝。她脑子里为什么保留着这样的记忆?